再论《金瓶梅》作者“大名士”说——从《金瓶梅》中李贺的一首引诗说起
2016-01-31杨彬
杨 彬
(东华大学,上海 201620)
再论《金瓶梅》作者“大名士”说——从《金瓶梅》中李贺的一首引诗说起
杨彬
(东华大学,上海 201620)
E-mail:bang2002@163.com
摘要:《金瓶梅》是一部以仿拟其他文艺作品为创作特色的伟大小说,但是它在仿拟、引用“雅文学”如诗词等素材的时候,却并不是根据第一手的材料,而是根据引述这些诗词的其他通俗文艺作品而进行仿拟、引用。第十一回中对于李贺诗歌《将进酒》的引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金瓶梅》的作者对于正统诗词等“雅文学”(以及真正的上层社会)的陌生,和他对于通俗文艺作品(包括中低层市民生活)的熟悉,使我们有理由质疑:这样的作者尽管不是持“集体创作说”者所称的说书人群体,但恐怕也并非长期以来流传的所谓“大名士”。
关键词:金瓶梅;李贺诗;雅文学;大名士;引用
自从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提到《金瓶梅》的时候(《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为《金瓶梅》,只在强调词话本的时候才使用《金瓶梅词话》),说他“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引来了后世无穷的猜测,而此前此后“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杮录》)“巨公”(《金瓶梅》廿公跋)甚至直点其名怀疑为“明朝闲儒生卢楠”(见《金瓶梅》满文本序言)等等的说法,也都似乎在佐证、加强沈氏的猜测。持《金瓶梅词话》乃“集体创作说”者虽然并不认可此说,但坚信“个人创作说”的“金学”研究者们却都从文献资料等外证,到经由文本细读而得到的内证,力求坐实沈德符们的猜测。可惜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这已经多达八十数人,几乎都是明代知名文人的备选作者名单上的人名,始终处于加长的状态。即使在最近的金瓶梅会议上,新材料的发现使得金学界为之振奋,乐观其成者认为距离认定作者只有一步之遥,但其实问题仍然多多。因为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金瓶梅》文本内部,有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使“大名士”说依然面临着不小解惑的困难。总体而言,《金瓶梅》的作者是“大名士”或者有较高文学修养的高阶层文人的说法还不宜被轻易认定。
一
《金瓶梅》第十一回,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在其家留连饮酒,小说写道,有诗为证:
瑠璃锺,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幙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莫虚度,银釭掩映娇娥语,酒不到刘伶坟上去。
此诗出自于李贺的《将进酒》。原诗作: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与原诗对比,除了我们引诗时并未统一的繁简字体或者皆可通用的字如“瑠璃锺”和“琉璃钟”、“真珠”和“珍珠”、“幙”与“幕”等不论,显然有几个明显的异辞。这些异辞集中出现在原诗最后四句,准确地说,是从“青春”开始,四句全异,《金瓶梅》甚至比之原作少了一句“劝君终日酩酊醉”,只剩三句。而最后一句,《金瓶梅》把原诗的“土”,改为了“去”。一望而知是形近而讹(或许还值得一提的是,崇祯本《金瓶梅》此处甚至连“酒”字也省掉了),而另外两句,“况是青春莫虚度,银釭掩映娇娥语”,考其句意,则原诗那种佳日无多,红颜凋敝,故劝君更进一杯酒之意,几乎就被改成了青春励志之辞——还不要说这似是而非的句子明显有欠通顺。显然,《金瓶梅词话》此处所引,应非李贺原诗。那么,这段文字出在何处?
初步的考察表明,《金瓶梅》里的许多此类诗词,都是间接引用(我们把它称为间接仿拟)。也就是说,它不是引用的第一手材料,而是引用的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更等而下之辗转抄引的材料当中引得,并且几乎都是来自其他通俗文艺作品的引用。在查证此段间接引用文字时,同样引用了此诗的《宣和遗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后者记徽宗私访李师师家,显露身份重开筵席后,有如下一段描写:
师师进酒,别唱新词。天子甚喜,畅怀而饮。正是:
瑠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很显然,《宣和遗事》中的文字与李贺的原诗更加接近,而《金瓶梅》的引用,却改动了最后四句,而所做改动也并没有更加贴切其情节,融入其自身当中,甚至还出现了从句法到诗意的可笑的错误。这让我们十分困惑。不过,当我们翻开上引标称“重刊宋本”的“士礼居丛书”本的《宣和遗事》时,似乎找到了答案,一下子豁然开朗。
原来,《宣和遗事》中在“青春”的“春”字开始处换页,将“青”与“春”字以下隔在了两页(图1、2)。需要说明的是:士礼居丛书的刊刻年代固然是在清代,但刊刻者黄丕烈完全遵从着宋刊本的版式,事实上,他所藏的宋刊本原貌正是如此,上述引文也一字不差。所以附图关于《宣和遗事》版面的描述对宋刊本同样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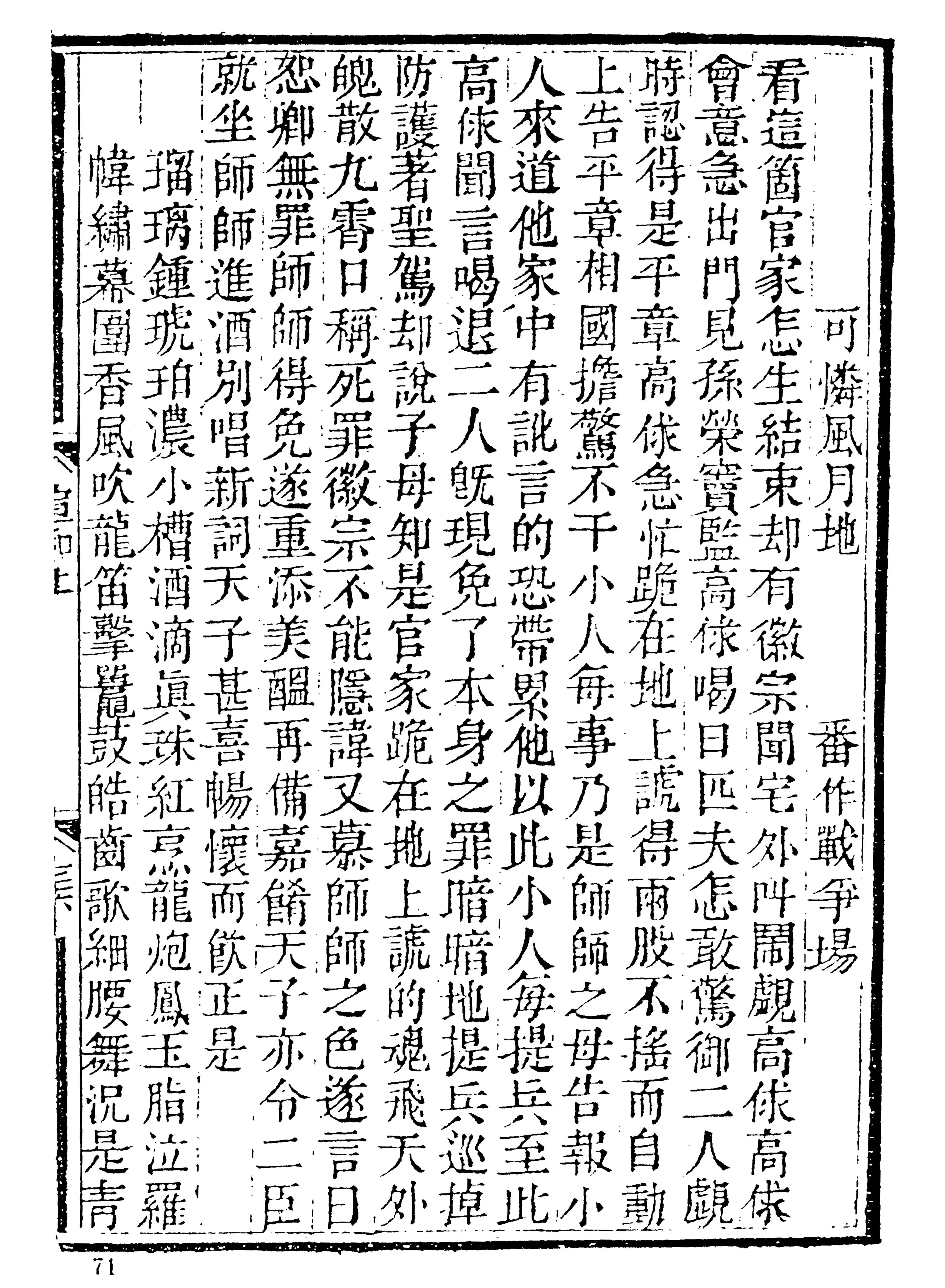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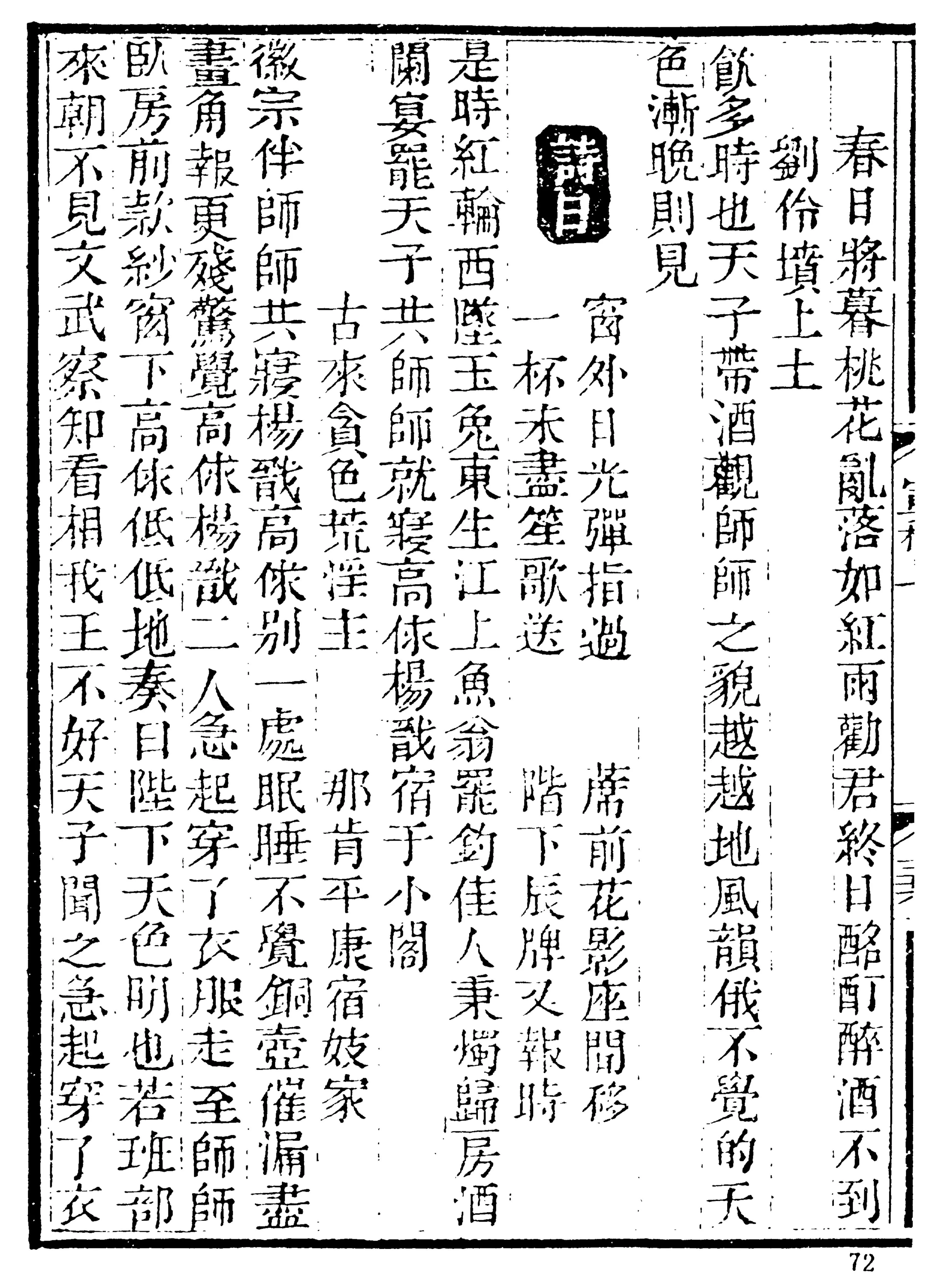
图2
一个合理的推测,应该是《金瓶梅》所抄引的李贺诗,乃正是抄自《宣和遗事》,而由于换页,“春”以下的文字或因原书版残缺,或因“春”以下漫漶不清,总之本行仅剩下了最后一句“酒不到刘伶坟上土”,故《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只得自行补足。而这一补,就现出了与原作的差异——不仅是文字修养上的差异,句意几乎已经与原作相反。这与“大名士”“巨公”们的手笔差距可真不是一点点大。经过细心的查找,我们发现这两句的句意与《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李铭、王柱应西门庆要求所唱的一段“东风料峭”《好事近》的〔尾聲〕部分颇为相近:“醉教酩酊眠芳草,高把银灯花下烧。韶光易老,休把春光虚度了。”(崇祯本《金瓶梅》按照它一贯的修编原则,并没有引用此段曲词)退一步说,即使《金瓶梅词话》的抄引错误并非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平心而论,“土”字误为“去”字更有可能是手民之误或者其他的原因),但看上去对李贺原诗一无所知,而仅通过二手材料引用,还将原诗的四句省减了一句且改动后的诗意正相反,无论如何不会是“大名士”“巨公”甚至“老儒”的做派。
在普遍缺乏可信的文献资料的前提下,我们从内部考察出来这样的文本差异,给基本上是从外证入手而认定的所谓“大名士”创作了《金瓶梅》观点,制造了不少论证上的困难。
类似上述的文本内证远非一例。在历代学人的考述下,《金瓶梅》各回所引诗词曲赋等的来源,正在逐一被挖掘出来。这其中,周钧韬先生的《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逐回详细考证其素材来源,让我们得以窥见《金瓶梅》以仿拟、改造素材而成书的写作方式,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立论的材料。其对《金瓶梅》第一回卷首词的考辨,就让我们对于作者的身份问题再次产生了疑问。
《金瓶梅词话》卷首词“丈夫只手把吴钩”,据考证是宋人卓田的《眼儿媚·题吴小楼》。而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的考索则说明,《金瓶梅》是“抄于《清平山堂话本》卷三《刎颈鸳鸯会》”而非后者所引卓田原词。他论证说:“1. 《金》引词与卓田原词有六字之差,而与《刎》引词只二字之差;2. 卓原词用词准确,如‘尝观项籍与刘季’,表示追忆甚恰,而《刎》改为‘君看’近似,而与‘尝观’,差之甚;3. 卓词‘一怒世人愁’,表示项刘乃盖世英雄,甚恰,而《刎》改为‘一以使人愁’,原意失且文理不通。《金》改为‘一拟使人愁’,承袭《刎》篇之迹十分明显。由此可见,《金》抄《刎》而非抄卓原词。甚至可以推断,《金》作者根本未见卓原词,否则不会错得如此离奇。此还可见出,《金》作者于诗词之道,并不十分精通,书中不少诗作很不高明,可证笔者推断之不误。”[1]3
这与上述引用李贺诗词的情形一样,都不是直接引用原诗词,而是引用了原诗词的其他通俗小说,并且根本不知原诗(词),对其原意也远未真正理解,只能囫囵吞枣,似是而非。此外,周钧韬书在对《金瓶梅》的第六回所引《水浒传》诗词之改动也发表同样意见。在那里,一首被《金瓶梅》辗转从《水浒传》引来的《鹧鸪天》,居然不辨词、诗,改为七律而仍沿用其词牌名[1]42-43。这同样“可证笔者推断之不误”。
“大名士”当不至于粗疏不学如此吧。
二
《金瓶梅》是一部以仿拟其他文艺作品为特征的小说。这里所谓的仿拟,在其他研究者那里也常用“镶嵌”“抄袭”“摹仿”“引用”等等不同的理论术语来表述,大致都是指《金瓶梅词话》从其他文艺作品中撷取部分现成诗句、唱词或者整段的情节、故事入于自己故事、情节架构中的做法,不过在本文看来,这些表述都各有其不同的侧重,限于论题,此处不予深究,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仿拟”和“引用”的界定则略有异:前者是指在适应小说自身情节构架的前提下,对前代或当代文艺作品中的相关对象——包括诗词歌赋、语言表达、情节段落、人物形象等——加以变形、改造,以产生新的情节构架,甚至新的文本意义;后者则仅是对一篇特定文艺产品(如诗词、小曲)等的照抄使用,如同叙述语言中的“直接引语”,它经常与情节无关。
衡以此标准,则《金瓶梅》仿拟、引用其他文艺作品的现象当然不局限于上述几回,其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但就其仿拟、引用的对象而论,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所仿拟、引用的对象,基本都是通俗文艺作品。这从弁于卷首的《欣欣子序》里罗列的“前代骚人”及其作品的名单即可见一斑:“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徽(微)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当然,在这样一部几乎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全景图像的大书而言,既有“奴佁之稽唇淬语”,也免不了“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谢肇淛语)的官场语言,作者要如实刻画这些场面,尤其是接待蔡状元、廷参朱太尉等情境中,自然也少不了对于“雅文学”的仿拟和引用。众所周知,《金瓶梅》从内容到叙述语言,都是典型的通俗文学。其大量使用的山东方言(即使有论者力辩其中含有、甚至主要是吴语或其他方言,终究也还是地方土白,与书面语雅俗有别)、俚语等白话口语,正是它被人啧啧称奇之处。但在这些白话之中,却也偶尔会有文绉绉的以雅言——文言诗词或者雅词丽句——为主体的叙述语言掺入其中。只是细观其文,却又会令人忍俊不禁,因为这些“雅言”,几乎无一例外是仿拟、引用其他通俗文艺作品,并且生硬地插入其自身文本中,颇让人有“水土不服”的感觉。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金莲大闹葡萄架”的一段淫秽描写,被普遍认为乃是仿拟《如意君传》武后与薛敖曹在室外挹香亭的一段交合情节而来。在不厌其详地记述了同在室外上演的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狂暴性爱活动之后,一向满口俚语村言(尽管这些语言是那么的生动活泼,又富于生活情趣)的潘金莲居然对西门庆如此告诫并抱怨说:“今后再不可这般所为,不是耍处,我如今头目森森然,莫知所之矣。”在这里,《金瓶梅》完整保留了《如意君传》的语言——武后“乃视曹低语曰:‘且勿动!我头目森森然,莫知所之。’”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在全篇泼辣生动的白话体的人物语言中,金莲口中残留的文言显得十分刺目。
第五十九回,西门庆初会郑爱月,作者极尽刻画郑爱月的房内陈设:
但见瑶窗素纱罩,淡月半浸;绣幕以夜明悬,伴光高灿。正面黑漆镂金床,床上帐悬?锦,褥隐华裀;旁设褆红小几,博山小篆霭沉檀;楼鼻壁上,文锦囊象窑瓶,插紫笋其中。床前设两张绣甸矮椅,旁边放对鲛绡锦帨。云母屏,摹写淡浓之笔;鸳鸯榻,高阁古今之书。西门庆坐下,但觉异香袭人,极其清雅,真所谓神仙洞府,人迹不可到者也。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房间恐怕只有崔莺莺等相府小姐们才适合居住吧,而《金瓶梅》里,在“这人迹不可到者”的房间里住着的却偏偏是一个以“弃旧迎新为本,趋炎附势为强”的“院里”的妓女!用这样的丽辞(虽然也摆脱不了通俗的身份)来形容郑爱月这样的一个“女娘”,谈不上“唐突佳人”,反倒一不小心就唐突丽句了。
上述充斥着套语和卖弄的文辞雅言,与全篇俚俗而生动的风格似乎格格不入,其来历也颇可令人生疑。梅节先生的考述表明,原来其出处就是出现在明代中前期、在欣欣子序里被称为卢梅湖所做的《怀春雅集》,而在仿拟上述作品的时候,《金瓶梅》中还出现了不少的异文。这段文字,连同第七十七回,西门庆踏雪访爱月的时候,在爱月房中墙上看到的那幅《爱月美人图》,上面赫然题写着三泉先生的题词——“有美人兮迥出群”的七言诗,也都是自《怀春雅集》中仿拟得来。只是,相对于原作中才子佳人的怀春情事,较之恶俗得多的嫖客与妓女之间的肮脏生意,与这样的雅言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金瓶梅》中偶见的“雅”,当然更多还是对于诗词的仿拟和引用。晏几道的词《鹧鸪天》“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在梦中”,在《金瓶梅》中被窜改使用于西门庆和李瓶儿偷情的不堪之事:“情浓胸紧凑,款洽臂轻笼。剩把银釭照,犹疑是梦中。”简直像是粪里插花,不伦不类。对于上述这部《怀春雅集》,《金瓶梅》也没有放过充斥其间的那些并不高明的诗词,但并不忠实的引用和与自身情节系统并不契合的仿拟,让《金瓶梅》并没能真正有向“雅”的提升,反倒是留下了更多的把柄,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仿拟者——《金瓶梅》作者的文化底子。
梅节先生对于《金瓶梅词话》仿拟的《怀春雅集》的全部二十一首诗都做了认真的校勘,并且从“生硬代入 比拟不伦” “不解原书 随意窜改”“其他引诗 过失相同”“腹笥不丰 随意引用”等几个方面数说了《金瓶梅》在仿拟、引用这些诗词时的粗疏鄙陋、不伦不类之处,对作者的身份也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这种连续引用同一作品的现象,反映词话作者对雅文学即正统文学,似乎腹笥不丰,未能博览广采,择最贴切的引用,而是逮着南瓜吃南瓜,逮着茄子吃茄子。”[2]71《怀春雅集》《钟情丽集》等文言小说是否可称为“雅文学”,概念上尚需要进一步讨论——事实上,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就鄙称它“不为庄人所取”,显然在当时就不被视为“雅文学”。但即使对这些接近于“通俗”的文言小说,《金瓶梅》的作者都显得“腹笥不广”,那么即使我们并不认同梅先生视《金瓶梅》作者为“‘打谈的’(说书人)”,也怀疑梅先生能否仅凭《金瓶梅词话》大量“袭用、窜改《怀春雅集》的诗文”,就能达到“证明词话作者不可能是钜公大名士”[2]74的目的,但《金瓶梅》作者那难以确指的“大名士”的身份,至少可以再次受到合理的质疑了。
三
与《金瓶梅》仿拟、引用“雅文学”的情形恰成对照的是,小说在引述通俗文艺作品的时候,却是显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固然,在对诸如《雍熙乐府》《词林摘艳》里所记载的散套、小令的引用,《金瓶梅》也时有讹误,时见异文,但对于情节发展、人物形象刻画、叙述语言等等,都不构成不和谐的影响,并不像它对雅文学的引用所造成的结果那样。而它在仿拟或引用这些通俗文体时的使用范围也是极广:有的以之抒情(像充斥其中的回前诗词等等);有的以之反讽(如第八十回,应伯爵等一干“兄弟”请水秀才为西门庆所做的祭文,全篇以西门庆之阳物为祭奠对象,明显是对传统祭文的“戏拟”);有的严肃而痛心(如李瓶儿痛失官哥后所唱的《山坡羊》);有些却意在调节气氛,如同戏曲作品中的“蒜酪”,甚至不惜破坏全书那种悲剧气息(如赵太医、接生婆蔡老娘等的出场白,比较准确地仿拟自李开先《宝剑记》,完全是插科打诨的闹剧风格);还有的只是“以曲代言”,如同戏曲作品那样,以曲词代替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大量出现于后二十回中,如第八十二回金莲与经济苟合之后二人互唱小曲,第八十九回吴月娘与孟玉楼给西门庆上坟时之哭诉,以及第九十三回陈经济在冷铺中对众花子自述身世时所唱的《粉蝶儿》套曲等等皆是)。而全书中最精彩的引述,莫过于第五十二回因应伯爵不断插科打诨而变异了的李桂姐演唱的那段曲词:
笑了一回,桂姐慢慢才拿起琵琶,横担膝上,启朱唇,露皓齿,唱了个《伊州三台令》:
思量你好辜恩,便忘了誓盟,遇花朝月夕良辰,好交我虚度了青春。闷恹恹,把栏杆凭倚,凝望他怎生全无个音信?几回自将,多应是我薄缘轻。
〔黄莺儿〕
谁想有这一种,(伯爵道:“阳沟里翻了船,后十年也不知道。”)减香肌,憔瘦损;(伯爵道:“爱好贪他,闪在人水里。”)镜鸾尘锁,无心整。脂粉轻匀,花枝又懒簪;空教黛眉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记得说,接客千个,情在一人,无言对镜长吁气,半是思君半恨君。你两个当初好,如今就为他耽些惊怕儿也罢,不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说!”)最难禁,(伯爵道:“你难禁,别人却怎样禁的?”)谯楼上画角,吹彻了断肠声!(伯爵道:“肠子倒没断,这一回来,提你的断了线,你两个休提了。”被桂姐尽力打了一下,骂道:“贼们攘的,今日汗歪了你,只鬼混人的!”)
〔集贤宾〕
幽窗静悄月又明,恨独倚帏屏。蓦听的孤鸿只在楼外鸣,把万愁又还题醒。更长漏永,早不觉灯昏香尽眠未成,他那里睡得安稳?(伯爵道:“傻小淫妇儿,他怎的睡不安稳?又没拿了他去,落合的在家里睡觉儿里。你便在人家躲着,逐日怀着羊皮儿,直等东京人来,一块石头方落地。”桂姐被他说急了,便道:“爹,你看应花子来!不知怎的,只发讪缠我!”伯爵道:“你这回才认得爹了?”桂姐不理他,弹着琵琶又唱)
〔双声韵〕
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伯爵道:“揉着你那痒痒处,不由你不上心。”)无人处,无人处,泪珠儿暗倾。”(伯爵道:“一个人惯溺床,那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铺在灵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进来看见褥子湿,问:‘怎的来?’那人没的回答,只说:‘你不知,我夜间眼泪打肚里流出来了。’就和你一般,为他声说不的,只好背地哭罢了。”桂姐道:“没羞的孩儿,你看见来?汗邪了你哩!”)“我怨他,我怨他,说他不尽;(伯爵道:“我又一件说,你怎的不怨天,赤道得了他多少钱?见今日躲在人家,把买卖都悮了!说他不尽,是左门神白脸子,极古来子。不知道甚么儿的,好哄他。”)谁知道这里先走滚。(伯爵道:“可知拿着到手中,还飞了哩!”)自恨我当初,不合地认真!(伯爵道:“傻小淫妇儿,如今年程在这里,小岁小孩儿出来,也哄不过,何况风月中子弟,你和他认真?你且住了,等我唱个《南枝儿》你听:‘风月事,我说与你听,如今年程,论不得假真,个个人古怪精灵,个个人久惯老诚。倒将计活埋,他瞎缸暗顶。老虔婆只要图财,小淫妇儿少不得拽着脖子往前挣!苦似投河,愁如觅声。几时得把业罐子填完,就变驴变马也不干这个营生!’”当下把桂姐说得哭起来了。被西门庆向伯爵头打了一扇子,笑骂道:“你这断了肠子的狗材,生生儿吃你把人就欧杀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谢希大道:“应二哥,你好没趣,今日左来右去,只欺负我这干女儿!你再言语,口上生个大疔疮!”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
人都道他志诚,(伯爵才待言语,被希大把口按了,说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李桂姐又唱道。)却原来厮勾引,眼睁睁,心口不相应。(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说:“相应倒好了,弄不出此事来了。心口里不相应,如今虎口里倒相应。不多,也只两三炷儿。”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见来?”伯爵道:”“我没看见?在乐星堂儿里不是?”连西门庆,众人都笑起来了。)山盟海誓,说假道真,险些儿不为他错害了相思病!(伯爵道:“好保虫儿,只有错买了的,没有错卖了的。你院中人,肯把病儿错害了?”)负人心,看伊家做作,如何交我有前程?(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个招宣袭了罢!”)
〔琥珀猫儿〕
日疏日远,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宁耐等。(伯爵道:“等到几日?到明日东京了毕事,再回炉也是不迟。”)想巫山云雨梦难成,薄情,猛拚今生,和你凤拆鸾,凤拆鸾!
〔尾声〕
冤家下得忒薄幸,割捨的將人孤另,那世里恩情,番成做话饼!
括号中都是应伯爵等人在演唱过程中的插话。李桂姐所唱的这首《伊州三台令》,本是抄自于明代曲选集《词林摘艳》,但作者却一改其他段落里对现成曲词大段抄录的习惯(其中异文也自不少),而是抓住人物形象与心理,对曲词本身及演唱过程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把这段唱词及其演唱过程融入了故事情节的进展中,成为作者构思情节的一个有效方式。且使原本不到400字的散曲,由于应伯爵的插科打诨,竟然衍生为1 500多字,当然也把演唱时间拖长了几倍,增加了情节的延展性,更生动地表现出应伯爵的帮闲天赋——他如“肚里蛔虫”一般知晓西门庆对桂姐瞒着他接客王三官深怀不满,才会如此谰言。结合唱者听者的不同反映,小说同时刻画出了几个人物的形象,并深探到他们各自的内心世界。而从整段情节的发展来看,作者写来也是极尽变化,不呆不板。应伯爵接着李桂姐的唱词打岔,有时是曲解词意,有时是讲个笑话,甚至还止住李桂姐的演唱,自己插入另一支小曲,说中了李桂姐的心事,让她不由得哭了起来。一段小小的曲词演唱,不是平铺直叙地写出,而是枝节横生,千变万化,让读者读来意趣盎然,而不会感觉单调乏味。这在大量引用、抄录诗词、散曲的中国古代小说中还不多见。虽然在《金瓶梅》中也不过仅此一见,但作者那巧妙的引用和运用仿拟材料的娴熟、高妙手法,还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出色地表现出他对于通俗文艺作品是如何熟悉且善于把握的特点——特别是在看到他引用“雅文学”的笨拙之后。
以上所论,多少有些像我们刚刚对梅节先生的论断所作出的判断,仅仅凭着《金瓶梅》的作者对“雅文学”的不精审甚至不伦不类的引述,以及对俗文学如鱼得水得心应手的运用,就断言作者绝非“钜公大名士”,多少有些草率。但反向而论,若不忽略这些问题,而试图论证作者就是某“钜公大名士”,也非易事。事实上,除此之外,《金瓶梅》的文本中还包含有许多的证据,对本文所论提供着有力的支撑,给“钜公大名士”之说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大名士”改造、创作类似的通俗文艺作品固然并不足为奇,但在运用雅俗文学时表现出来的如此鲜明的对比,没办法不让我们对于作者的身份产生怀疑。
比如,从小说对于宴会食单的描写上,似乎就可见出作者的寒酸:在西门院内,或者在如王六儿等“小户人家”的宴席上,对于酒水菜肴的描写不厌其详,举不胜举。随手摘引小说第三十四回所记的一次普通午餐:“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炸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炸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最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即化,骨刺皆香。”可谓形色兼备,不厌其详;而一旦涉及皇宫贵族的筵宴甚至写到西门庆入京之后所经的宴席,对那食单就只能是泛泛而论,与前者之细密翔实有着明显的不同。仅在第七十回写西门庆进京“庭参朱太尉”的过程中,就有翟谦、何太监、何千户三次宴请西门庆的描写,但饮食描写则简略至约等于无,像“不一时,安放桌席端正,就是大盘大碗,汤饭点心一齐拿上来,都是光禄烹炮美味,极品无加”。“桌上许多汤饭肴品,拿盏箸儿来安下”。“何千户又是预备饭食,头脑小席,大盘小碗,齐齐整整……”这哪还有一点此前描写的生动、逼真?一旦走出清河县城,涉及对于真正上层社会的摹写,就显出了作者的寒酸,似乎不知从何落笔。黄霖先生曾举《红楼梦》与《金瓶梅》关于宴会食单描写的“雅”和“俗”,力证二书品格的雅和俗,在我们看来,其根本原因乃是二书作者出身的社会阶层不同:曹雪芹出自豪门贵族,自幼鼎鸣玉食,饫甘餍肥,其所经历,自是普通大众所不能及,故其笔下食饮如螃蟹鲞不仅令刘姥姥叹为观止,一般读者读之也顿觉眼界大开;而地位远非“大名士”之高的《金瓶梅》作者则与普通大众所见相同,对真实的富豪家居生活并不甚了了,反映在小说中,其所描写仅止蜻蜓点水,浮泛简略,根因就在于他本来就不具有他要描绘的生活经验而已。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但限于论题,我们在这不便多所展开,正面的立论只能留待另文再加详释。
四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可谓中国小说史上最难最大的一桩悬案。而遍观世界文坛,类似这样在作者问题上聚讼纷纭的公案尚有不少。比如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这两部题名即昭示出作者乃是荷马的史诗——包含《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围绕着荷马之有无,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长时期的争论。而了解他们对于这一相似问题的处理,或会成为我们解释中国小说史上斯芬克斯之谜的“他山之石”。
西方文学史对于荷马之身份——像我们对于《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大名士”,还是其他——历来有两派意见:一派以荷马为不同时期的多个人,荷马史诗则是由多个不同时期形成的诗篇片段连缀而成,这被称为“分辨派”(Analysts),或者“小歌派”(Unitarians);另一派以荷马为单一天才作者的,同时认为荷马史诗出于一人之手的,史称“统一派”[3]。 不难看出,前者类似《金瓶梅》的“集体累积创作成书说”,后者则是“个人创作说”的荷马史诗版本。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米尔曼·帕里(M.Parry,1902—1935年)和他的学生和合作者艾伯特·洛德(A.B.Lord,1912—1991年),共同开创了“帕里─洛德学说”(也叫“口头程式理论”)。他们对于荷马史诗问题的讨论和结论对于类似《金瓶梅》等古代小说的形成、成书过程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朝戈金先生对这一学说的展开及其对荷马身份研究过程的描述作过如下的说明:这对师生,帕里和洛德,“通过精心设计的田野调查手段和方法,他们得出许多意味深长的结论,其核心是:史诗歌手决不是逐字逐句背诵并演演述诗作品,而是依靠程式化的主题、程式化的典型场景和程式化的故事范型来构造故事的。同理,堪称巨制的荷马史诗也就不可能是个别天才诗人灵感的产物,而是一个伟大的民间口头演述传统的产物。”他们的后继者,同为哈佛大学的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 1942—)在《荷马诸问题》(Homeric Questions)也说道:“鉴于在文本性与口头诗歌传统的某些演进模型之间已彰显出坚实的平行对应关系,我一直在坚持论述的是:荷马史诗作为文本的定型问题可以视作一个过程,而不必当作一个事件。只有当文本最终进入书面写定之际,文本定型(text-fixation)才会成为一个事件。……史诗的荷马传统为这样的文本化提供了一个例证: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演进过程中,史诗的荷马传统按其自身的再创编模式,呈现出流变性越来越弱而稳定性越来越强的特征,随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直至一个相对静止的阶段。我们可以将这一相对稳定的阶段归结为一个史诗吟诵人的时代(an era of hapsōidoí)”[4]。对《荷马史诗》这样极具文化与文学重要价值和意义的作品,洛德断言:“荷马史诗的创作者是一位口头诗人。”[5]
在我们看来,《金瓶梅》的创作和写作,与之有着相似的过程——都是演述自前代伟大的文学传统,包括口头的戏曲、说唱艺术以及书面通俗文学作品,但依照作者的独立意志进行再创编而逐渐定型、完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仿拟”)。这一过程漫长,甚至会是许多岁月。诚然,对《金瓶梅》做这样的认识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和引入更合理的论证方法,但既然洛德等人对于历来堪称伟大且署有主名的荷马史诗的作者都做出这么斩钉截铁地“口头诗人”的认定,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可以认为像《金瓶梅》这样堪称“伟大”(尽管不掩其“瑕玼”),其成书定型也经过了较长且也复杂过程的作品就一定是某“大名士”所为?
参考文献:
[1]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梅节.从套用窜改《怀春雅集》诗文看《金瓶梅词话》的作者[M]// 梅节.瓶梅闲笔砚——梅节金学文存[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3]李赋宁.欧洲文学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
[4]朝戈金.从“荷马问题”到“荷马诸问题”[N].中华读书报,2009-03-11(09).
[5]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204.
[责任编辑王晓雪]
IsTheGoldenLotusAuthored by a Great Celebrity?
Inspired by a Piece of Parodied Poem
YANG Bin
(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1620,China)
Abstract:While The Golden Lotus has earned the reputation for parodies, the works parodied (such as poems from the Tang to Ming dynasties) are not the first hand material, instead, they are from a secondary source: the light literature, as is showed in chapter 11 in which Invitation to Wine—a poem by Li He—is quoted. The author of The Golden Lotus was unfamiliar with the elegant literature, such as poetry (and even the real life of upper society), while familiar with the light literature (including the life of townspeople in the bottom society), which justifies our hypothesis: even though the novel was not authored by a storyteller group, as some scholars have believed, it could hardly be written by a so-called “great celebrity” as widely believed for long.
Key words:The Golden Lotus; poetry of Li He; elegant literature; great celebrity; parody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79(2015)04-0477-08
作者简介:杨彬(1970—),男,山东泰安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