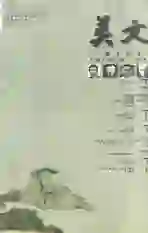锦瑟无端五十弦
2016-01-11庞永力
庞永力

一
临近中年的男人,事业、家庭、人际关系、情欲(虽非少年孟浪,但也是有所需求的)……这些聚而成火,备受煎熬。在锅底翻腾,说其虚浮,其实是焦灼。张着嘴,探出锅沿,想来一点儿冷水降降温,不料被喂一口酱油或醋,解灼热未遂,反倒咸酸复加。跌落锅底,感叹自己被烹制,同时又不得不味道鲜美。
二
一日做梦,竟是热闹风光地娶媳妇,玉缎轻裘,人拥仆簇,美娇娘红布遮面,令人怦然心动……醒来后感叹:噫!因何有此梦?想清苦少年,心高路窄,谁不艳羡温柔富贵之乡?此梦乃青春旧淤故创所致也!少年苦时不觉苦,垂老反顾泪潸然!现在就得正果了么?八十一难尚有多少应来未至?殊途同归,盖人之共愿,春风满途,而非秋雨凄凄;外表同着锦,内心异矣!将至中年有此旖梦,始知少年狂妄已逝,沉重落地,羽翼纷纷。
三
与妻遛弯儿,并肩坐在广场的长椅上,猛然有了幻觉,遥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模样:也会这样坐着,人物、情景、姿势一般无二。到那时,呛水、吞泥已够,脚都洗干净了,没有这样那样的惊喜与期待了,诸如涨工资、升官、艳遇……足够安稳了,足够平静了!等待的,只是自己与身边人的老病,乃至故去。“平静了以后/我枯萎了”,这是我十几年前写下的诗句,到如今更加凸显预言性,栩栩如生。上岸,何喜之有?
四
黄昏的时候,随意坐上一路公共汽车。这个城市是久别的,沿着一条线路剖开她的肌理,看两旁的建筑、招牌,身边的人上上下下,说着杂七杂八。公交的起点、终点大多是城郊,它一停一顿,陌生与熟悉相杂,穿过繁华渐至冷清。公交有它的好处,既能一步步走远,也能一节节踱回来。有时候,能回来,心情就大不一样。暮色渐重,渗漏在心里洇散开去,不好清除的。一个人独自也好,暮色里的寂寥也是可以享受的。
五
人一到危急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依着最熟悉的样式,做出最熟练的动作。乱石纷纷之际,就知道什么叫抱头鼠窜了,人会无师自通地抱头、猫腰,寻那安全点儿的地方去。再发达了的人,再变异了的人,离乡再久,平常想不起娘亲来,只要内心一极度悲凉,就会暗自祷告:“娘啊!”这是一个人最初的东西,也将是最后的东西。
六
梦,好的记忆、好的梦想映射进来,妙不可言,很多事在梦里得了逞;而白天里潜在的忧虑、可能的风险,也会钻渗进来,更阴森更绝望。惊骇不绝,逃脱出来,却跌至床下,摔破了嘴。梦与现实至少是堂兄弟,他们有血缘关系。
七
人很多时候会一下子回到曾经的境地,好像乞丐偶尔也能讨到半碗肉一样,发达了的人也会时不时显露原形。来路,以前怎样挣扎着、半跪半爬着走过来,过五关斩六将的辛苦与荣光,失荆州走麦城的落魄与龌龊,其实离得都不远,那些锦衣、钱帛,禁不住一阵大风。重又站在路口,逝去的只是岁月,那时青葱,如今老迈。
八
一时间很迷茫,完全不想做事,空虚之至。青春之仓促,上下求索,又常常捉襟见肘。身边碌碌者,不乏暗地里发了财的、命好做了官的、运好摘了桃花的,就算运气不逮如我者,也没有我这般深刻的醒悟与痛苦。
九
人与人相处,总有个远近亲疏的,看一个人为他人的付出,一般是时间和金钱的衡量。我倒觉得,应该看对他日常习惯的影响,越是雷打不动的习惯,越见真章。如果仍是慢条斯理、按部就班,嘴上再怎么表达也没有用。如果有人为你改变了习惯,甚至于为你形成了新的习惯,那他就是再有问题,也是可以原谅并值得你去亲近的。
十
年少时懵懂,想万千事物都美好;及长,历经挫败与打击,又“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经常悲愤无状,总能看到人生的不干净、不如意。其实很多事物,本来就是良莠并存的:譬如春天,既要感怀她的萌发也要明晰她的浪荡;譬如草原,既享受他的水草丰茂也要接受蚊蝇孳生;譬如美女,有风情万种也必将老态龙钟……而真正的成熟,是保持谨慎之余,还要重拾事物的美好;一切,要看我们心态的阴晴与切入的角度。
十一
终老的终老,应该是在一辆略微颠簸的车上。脸冲窗外看着,那轮番变幻的风景;侧过头来,身边是不老的容颜……不去管外面逝去了多少岁月,不去管别人看你我是如何的枯槁。车永远不要停,无穷的世代轮回,也占不满宇宙一个光年的内存。
十二
两个感情萌动的男女,谁先表达爱意,谁就会在日后的交往中吃亏。两个面临分手的男女,谁先说出决绝的话,谁在日后心肺互相撕咬的煎熬里沾光。事先忍不住,事后收不拢,都会成为弱者。世间之事,大多类此。
十三
伏案笔耕者,每有妙语佳句、人生醒悟便如淘金拣宝,兴奋过后又发愁如何传播,生怕不被发现、不被接受,思想与声音消散于茫茫虚空,白白来一遭。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作品的传播不要在意何种形式,付梓了、上网了,甚至口口相传,只要大致精神在,不要在意只言片语的差误。而传播不广,不单是作者的损失,也是无缘一见者的遗憾——他们错过了一个人用生命凝结而成的赤金。
十四
年少时曾失恋,五迷三道、茶饭不思,怎么也转不过那个弯儿来。曾因此向长辈吐露苦恼,他告诉我:在你这里是好东西,在别人那里不一定就是宝贝。这话很残酷,想来却有道理。同样一个物件,放在不同人那里,感觉与效果会大不一样。俩人得到的渠道不同,会有差异;情境不同也是,得到之前茶饭不思,得到以后兴趣索然。同理,你枕边冷战恶吵者,也许正是哪个傻瓜的梦中情人。
十五
与身边人笑语:生个好脸蛋儿乃爹娘所赐,乃自身固有之资源——整容不算,扶鼻挪眼,那是潜规则,更何况有的人丑到无处可整。如果先天亏缺,可以有一个好性格。性格与脸蛋儿不太一样,有天性,也有后天修养。好脸蛋儿与好性格并不冲突,只不过生个好脸蛋儿的人,一般会心高气傲,没心思去打磨性情。我们聊以自慰的是:好脸蛋儿只管一个花开青春期,而好性格是可以受用一辈子的。
十六
去买东西,柜台后的女孩可眼可心。先可眼再可心,男人就这毛病,管她什么品质,先可了眼再说。关键很多时候碰上的,既不可眼也不可心。你又不能打包票:她不可眼,但一定可心。
十七
女人四十豆腐渣,再嫩也不管用,更何况很多嫩是装的,倒是不装的让人踏实。与某女笑言:你都三十了,不用担心美貌这个问题了,人们开始用贤惠要求你了;再过几年,就是慈祥不慈祥的问题了。
十八
爱情在多年后就淡成了过日子,有时还能偶露峥嵘,浪漫地互相牵念一下子,似初恋时的感觉。岁月飞逝,很可以掐指一算了,突然发觉:自己可能早就没有被爱的自信了,也没有施爱的耐心了,两个人之间变得粗糙起来。爱也是可以回归的,放到怀里焐焐,它就可能苏醒。时间一久,会应了那句“少年夫妻老来伴”。爱在我们眼前消长、变幻,似虹,它的色彩与弧度取决于我们自己。
十九
一个灵魂在风中,一股股滚烫的、冰凉的、硬而苦的、软而酸的液体,涌过流淌,包裹着这个灵魂,它在动,它在腐化,它在变幻——如果我是一颗最终变臭了的鸡蛋,那第一个洞就是你打的,亲爱的,这就是你的罪过。
二十
坐车瞅美女。女子的美大致表现在身材(高挑、凹凸有致)、肤色(白皙、吹弹可破)、五官(精致、秀色可餐),这些令人养眼的标准具备了,就是难得一见的美女了。这样的女子会让人变得沉静,先是惊艳,继而纯粹起来。美到了极致便是沉静,同时也能顺带着注目者沉静下来,使他有一种酸痒的感觉自内心油然而生,没来由地感到亲近,甚至有一吐多年纷杂、辛酸之愿望,虽然与人家只是擦肩。
二十一
在异性的追求上,我们总是心动于“人生若只如初见”,或者擦肩的惊鸿一瞥,随即会萌发“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的浪漫期许。而真正走到了一起,修得正果,岁月磨砺后,相看两厌,互成蠢汉与黄脸婆了。其实,细细想想每一对夫妻的相处,多少次同船共车,多少次同桌举箸添汤,又有多少时日的欢愉!真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岂是前世千万年所能修得的?我们大多选择性遗忘了,蠢汉也曾挺拔,黄脸婆也曾青翠,这个过程中有过多少依偎、风情?又有着多少疏忽与痛楚?
二十二
在噩梦中哭泣的人,是走不出来,还是不甘心接受失败而不愿意醒?但早晚会结束的,认输,如果有未来可图还算幸运的。人生终究是要认输的,到头来,总有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子,绊住走过千山万水的脚。所以人至晚暮,首先要戒掉狂妄与梦想,变换底色与旋律的节拍,缓缓地落降下来。
二十三
我不知道,那些负面情绪是怎么积攒起来的,平时一个火药桶,将火药面儿慢慢地撒进去,压瓷实,然后只需不经意的一点儿火星。我只知道,好事万难不期而遇,倒霉则根本不需要邀请。一些焦虑是无法说明的,而激烈的对抗后,伤害是互相的。好像打碎一面镜子,对方怎样不说,在里面看到的,是自己那张支离破碎的脸。
二十四
人是很怪的,春风得意时会生出霸气、英气、儒雅之气,甚至祥和之气,丑者也耐看了,一是他的内心里有一股意气撑着,二是他人的“刮目”之功。而一旦落魄受困,就显得猥琐、木呆,举止土而硬,五官也不协调。没有意气撑着的脸面很劳顿,别别扭扭。环境首先改变人的心态,继而改变人的举止,最后连容貌都改变了!
二十五
人还没死,就已有故居了——应称旧居的,这样就不用死了。幸未遭到拆迁,房子还是那房子,街还是那街,只是陈旧了些。与昔人相比,这是旧居的好处:它们不大改变和转移,它们的变化在肌肤上,是痕迹的湮没,是岁月的褪色,是记忆的渐失,但它们时光的核没有变,心应依旧。
二十六
人一出生就要面临着死,相对于生的繁花锦簇,冷漠、未知的死始终是每个人心里的一道阴影。生死是一个大课题,我倒避繁就简地以为:与其惧怕死,不如想想生命萌发之前。就好像列车穿行于山谷间,从一段隧道钻出来,有光亮、空气、鲜花和水,让我们懂得欣赏从而变得贪婪,让我们心怀欲求从而痛苦不堪。然而,很快又钻入下一段漆黑了。这漆黑与上一段漆黑一模一样。或者说,正因有了光亮的比衬,我们才觉出上段与下段的漆黑,才不能忍耐漆黑。而下一段,与我们先前度过的所有的漆黑一样,是我们已然忘记了的漫长的混沌。
二十七
爹的耳朵越来越聋,都七十多岁的老头了;那些年奶奶也聋,老太太唠唠叨叨,老骂自己的儿媳们,我怀疑她的聋是有选择的,有利于她的就听见,不合她意的就茫然。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也向着岁月深处滑去,这些年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同时也躲不开活着的欲望与消磨。我也在祖辈的后面衰老着,脂肪肝、肾虚、心累——最平常生活化的,就是一打开水龙头、一刷牙,就有尿意。一个前列腺条件反射就这样,何况各种制服不住、化解不了的病菌呢!可你又能怎样呢?我经历着自己的老,我原谅也请别人原谅我的老。
二十八
舆论很多不是档案、典籍,严谨、精确、煌煌大卷,而表现为街头巷尾的闲话儿。离乡多年,却总能想起一些乡人,在街头、田间臧否他人的情景。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完全不用负责,他们也负不了责,更没有能力去帮助或惩戒。他们旁观着你的生活,却往往搞不好自己的生活。他们只是抄着手,咳嗽着、吐着痰,发表着自己的意见:你成事了,他吐一个“行”,不管你如何的不容易,只是关心你是否托大、能否从你这里沾光借力;你衰败了,他一撇嘴而已,不管你有怎样的苦衷,甚至正好清算你曾经的托大,顺便发泄没能从你这里沾光、借力的怨恨。
二十九
在某处等人,看不远处一对男女的起腻、缠磨,忽然感到熟悉,好像有一股力拉扯着靠近、加入一样。很多时候就这样:首次相见却又感到熟悉,一个人、一个路口、一座屋檐,从它们身边经过,都是直着走过去的;如果一拐,自己的人生就是另一个情境,另一个因果。
毕竟没有拐。年岁大了就容易恍惚,总想如果拐了,会怎样?无数的选择与可能,是否预示着在多个维度空间上演着多种的人生——我们只是经历了其中一种,抑或真的有着无穷地轮回——那就太值得我们深味与期待了。
三十
中国梦,窃以为就是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有担当,有发展。现实生活是硬邦邦,努力拼争,潜规则横行,赢了靠侥幸、甚至玩阴谋,败了五味杂陈,却无暇伤感。在得逞与幻灭间,渐渐清醒,不再相信什么,失去了热忱与情趣,在睡梦中都清醒无比——失却了做梦的功能,才是最大的伤害,才是最大的悲戚。
三十一
向上攀爬时,没有人嫌爬得高,捞得多,也很少有人因为明伤暗疾而驻足整饬。现在想来,在一时风光之外,身踞高处还真的问题多多;一旦问题凸显、周遭崩塌,山有多高,悬崖就有多深。先前的心机、经营,都成了晕眩、惊悚、绝望的累积;上升过程中的日积月累,却换来更多人更长时间地听到你坠落时的惨叫——这时,你也许会想:如若不那么较劲,平稳地待在平地或半山腰,也挺好。
三十二
睁眼醒来,做了一个在老家老宅的梦:昌在过道里说话儿,推开木栅栏门进院,走进屋来,我倚着被摞,跟他谈现在的事儿……老家已疏离20余年,老宅屋顶半塌,草木横生;老友白发比我多,在老家熬生活。我只是感慨:沉溺在当下,那些过去的、逝去的,无暇念及,也很少梦到——难道梦到什么,也是需要选择的么?梦何至于如此吝啬?
三十三
与人夜谈,某人至死不改辛辣腥骚的重口味,令人心有余呕。回来一想,他的想法也来自真切的经历与观感,虽偏颇但也属真情实感。只要是欲望,就不能分大小与成色的。细一想,我们何尝没有那样的觊觎之心、未逞之欲?也少不了因之心潮澎湃、耿耿难眠,只不过我们还能忍住,还能去寻求较好的路径与表达,还能欺骗自己少食人间烟火、暂避灯红酒绿,甚至——只是还能伪装得不露出马脚而已。
三十四
上海虹桥高铁站,要回了,一天间华北、华东走一遭。几个月前,一家人从这里去杭州。对一个驿站的熟悉,除了恍惚、伤感,好像就没什么了。人一变老,就不堪漂泊了。以前隔开我们的,是山川、时间及生活中的诸多借口。现代化把时空缩短了,却仍不肯相见,隔开我们的,是那不再热望、现实琐碎、难堪思念的心……
三十五
年根儿了,情感也变得浓稠。老家一帮发小喝酒,打来电话——他们总是这样,耳热酒酣之际就想起我,埋怨我回家少、聚得少,颇有“遍插茱萸少一人”之感。一帮两鬓泛白的人,唠叨的却是少年时光。又接到初中同学志刚的电话,二十年不见了,直说这些年没啥本事,就是孝敬爹娘了——足矣了!城里乡下,哪个不是辛苦奔命?能欣然做的、本分做的,其实不多。
弄新诗多年,如今变了,一咣当就往外冒五言、七字,却不愿从头去学高深、刻板的平仄技法,顺口溜出《居廊寄友》分记之:
其一:兄弟举杯总念我,当年醉卧青草窝。庆禄何言心渐远?风吹花叶终袁佐(注:袁佐,生养我的村子)。
其二:二十年来未闻音,城里乡下皆艰辛。兄言爹娘膝下孝,远胜猫狗乱吠人。
三十六
阳光漫无边际洒落时,烟雾独自扭曲吞吐信子时,我们想不到二者的关联。很多时候,我们少年不知愁滋味,抑或一头绊倒在泥泞里,想不到人生哪会有独一的境遇,乌云罩在头上,而阳光在乌云之上——只有这样的排布,苦难才丰厚而别致,希望才温暖又绚丽……
三十七
早起,闺女跟同学坐车逛北京去了,不让送,不听叮嘱。想到她终会闯荡,就不再说话。
想起1990年自己第一次远行,在北京车站写出《如果有你在异乡街头》的凄惶与相思,坐着绿皮车去西北。到亲戚家后,给家报平安不是打电话、发短信、刷微信,而是发电报。拿钱不多,没想到连地址都算钱,写完省市县乡村后,仅够一个字了,就是:到。事后大姐说:好像你下到一口深井底,就给家里一个字。
又感慨唏嘘了。与女儿就像这茶几上两个容器,外形迥异,但饮下的,都是人生啊!
三十八
这是一个不缺乏新闻的年月,屡被震惊的人们最终会习以为常。高官被查,富商破产……人在欲望中癫狂,在侥幸中奔突,一点一点累积,一次一次险胜,到头来却一次性输个精光、败得彻底。没有信仰的人不会去想来生,而很多善恶恰恰是现世报应,在死之前、在沉溺于享乐已经万难“由奢入简”之际,被打回原形。人啊,大多看不清结局,抑或不愿去看结局,在过程中得过且过,掩耳盗铃,竟想不明白:到底选择一时风光爬得高摔得重,还是阖家安好细水长流?
三十九
子夜不眠,竟发现今天是情人节,真是忽略了。中国的情人节是七夕,过得模模糊糊,争议中倒把洋节扶了正。好多事情都这样。前天看到段子说情人——于谦问郭德纲,媳妇非常蛮横不讲理,外面的情人却温顺可人,怎么办?郭答:别相信在野党,谁上台都一样。真是刁钻恶毒又一击中的。
我想:老婆与情人好像这床上的枕头与靠垫,连洼带地,功能相似,因比较而存在,作用在男人身上的力,彼此轮换,一会儿相斥、一会儿相吸。很多沉迷其中者不明白,无论老婆还是情人,笑语盈盈时都融筋化骨,恶语相向时都令人窒息胆寒。所以不是如何选择身边人的问题,而是怎样修炼自身,让身边人保持心情愉快的问题。这是男人一生的课题。完成得不好,辞旧迎新也无非苦痛的轮替;完成得好,老婆与情人,完全可以合为一体。
四十
终于,梦到逝去四年的姥姥。一个菜园,早已痴呆、卧床多日的她出现了,手里掐着一把菜,还有娘,还有很多远近亲戚;我是知道她的逝去的,却只是招呼着合影,别人总把她挡住,她也不那么配合;我努力把她放进取景框里,透过眼底泛起的泪光盯着她……
四十一
1995年,春节刚过,我从家里出来再次到保定漂,在河北大学东侧白楼,与当时的席作家聊。旁边一男一女俩打字员,男的过一会儿就问:“那个啥五笔怎么打?”女的就回头告诉他。我瞥一眼,女的留短发,穿黄外套,俩人很吵。
刚才,身边人为减腰一通乱蹦,直说:“我才长十来斤,你比那时长了80斤,岁月还不是一把杀猪刀?”我想,虽然总烦秀什么恩爱,也该纪念了,这磕磕碰碰悲悲喜喜尚一舟共楫的二十年!
四十二
采访某活动。操办人事先跟我联系,客套一番,忽说:你是十八年前在北京北海的那个庞吧?我也一直觉得他的名字熟呢,说:你是我的同事黄吧?还真是。
组织方来接。上车,后排一位,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他说:我认识一个与你同名同姓的。扭头,哎呀,二十年不见的沧州老乡,他老父亲当年对我多有提携。
还能说什么呢?有一天,有个老太太遇见我,含情脉脉:我是三百年前大明湖畔你的夏雨荷……岁月太荏苒,就像车轮下这条高速路,向前,没头没脑向前,很多东西就一闪而过了啊。
四十三
决绝的对象分为两种,彼此防备的敌手,一度无间的亲密者。决绝的方式大概也分两种:在愤怒下采取方方面面的不配合,给对方制造难度,尽可能使之尴尬、难堪;还有一种就是表面没有异样,完成固定的程序和套路,但在关键处已做出动作。后者因为不动声色却斩钉截铁,更具令人惊骇、绝望之打击效果。
四十四
春节。在所有文艺作品中重复渲染,从而投注到人们内心,挥不去的亲情感、家族感;更多是仪式上的。那些固定的探访、问候,所选定对象、情景设置、遣词造句已定型,均不用突破,也不能突破。
中国人就生活在这种谓之民俗的东西中,一代代传承,就是有所改变,也是大多数均接受了的。有此感觉者,就好像站在了高坎儿上,看低洼处的同类被一层烟雾裹着,觉出灰色、窒息来,却不能改变他们,而自己也有着习惯性的依赖,难耐高处的冷风与孤寒。但时不时地也要沉浸进去,吸上那么两口。
四十五
又喝多了。好久不这样了。刚才的睡,睡中有梦:回家,巷口修路,挖大沟;那个租的平房小院,门帘一掀,媳妇也回来了,那辆骑了好几年的自行车——她咋没看孩子?那个胖嘟嘟的小人儿……
醒了。口干舌燥,客厅喝水,找到一个老橙子,真好。想到那梦,有些伤感,又想,虽已远逝,那毕竟是曾经的生活啊!藏着脑海的犄角旮旯,虽然不好翻出来,但永远不会丢掉,只要扎进梦里,踏上那条小道,就能互相看望。这就行了。
四十六
不知为了什么?还是那个做过多次的梦,一个彻底结束、终于毁灭的通告。很多事没有做,如果做了,就有延续,但结局就如跑道尽头的那根细线,你已撞线了!惊恐、痛绝一下子,涌起一声干瘪、沙哑的哭嚎,在漆黑、寂静的房间里响起……
醒了。结束只是梦里的事,自己还在。人到中年,不同于青涩年代的幻梦与进取,内心变得静寂、澄明,一直演绎着如何防御与怎样结束,逐渐地焦灼与绝望,才有了突然登临悬崖的“连续梦”。至此,少壮已变成了惯性,已然慢慢适应错误与流逝了,失去弹性的记忆开始混乱、渐次空白——很多动作已经完成,结果却是怪异:很多任性足以灭顶,却没有警示与惩罚。
那就结束吧!却不想是曾经多少的坚持,别人一脸不屑,自己竟然也解脱。就像脱下一件衣服,已经穿旧,本以为可以一直穿下去的;脱吧,却发现它已成了皮肤的一层,撕扯、断裂地疼。
四十七
电视剧《嘿,老头》落幕。一个笑中带泪的故事,海皮与小爽最终爽在一起,无论男女,经过多年奔走、追逐,梦想都褪色、安妥了。于女人,“被一个无赖看上,是幸还是不幸”;于男人,好像自家一辆自行车,被人骑了一圈又送回来了——无论如何,在大梦与回忆之外,生活本身还在,这就值得我们举杯庆祝!
四十八
回乡,肃宁有春秋时期的武垣城,以不惑之年寻访三千载古城,残垣断壁上自拍胖脸;老娘又翻出老照片,那时的我竹竿一般,差距之大,好像她有俩儿子一样,遂顺口溜出《时光小调》:
时光不算长,二十来年前。一胖与一瘦,该笑或该叹?周身贴肥肉,一片复一片。伊在春梦里,偶入泪眼帘。
四十九
有人请饭。一个很高大上的企业,老总却很忧虑。不应该啊!像我这样前途飘摇、四十无闻的小人物才应该发愁啊!于是重温了一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抑或是五千有五千的愁、十亿有十亿的忧。由此可见,我们起早贪黑努力拼争来的地位、身家与声名,都不能成为忧愁、悲痛的豁免金牌;同理,置身深渊泥淖者,也没人挡得住他扭过头来片刻的悠闲、快乐。
人类之间自定的沉迷其中的等级与差异,完全到不了改变自然、时光、命运的程度。冥冥中总有一个巨大的辽阔无边的人低头审视着我们,因为他的无穷大所以我们看不到他,因为我们微末如尘埃,所以他无视我们的悲喜。如是,每个人都苦守着自己的高地,承受着绵延不断的变化多端的攻击,到头来却谈不上得到与失去。我曾就此向爹诉苦,希望他这个老中医给开一副疗生汤药,他拒绝了,说:这就是过日子,太正常不过了。等真正消停下来,你也就完蛋了。
五十
又是睡梦中的相见。一个妇人的身影,伏在田垄间睡着了。还有动态的,拾来一块块白薯。这是谁的母亲?用臂弯遮着脸,短暂的睡能否暂忘生活的重压?那动态也仓促、短暂,这是谁脑海里深藏的记忆得以呈现?又好似置身一个图画展,我一下子对着身边的人痛哭失声。声音暗哑,久违的湿润。醒了。一个念头急迫:回家。看垂老的爹娘。
出差中,离家仅百里,却要按定好的行程,再折返回城里。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短短百十年的印痕被渐次磨去,好像从未来过。文字会有更长一些的流传么?在血脉亲人那里,也是一组越来越模糊的影像。没有留下声光影像是遗憾,不期而遇更会心痛得不堪——人总是这样,伸手可触时懈怠,轻易就扭过头去,即将永逝之际才呼天抢地,却又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