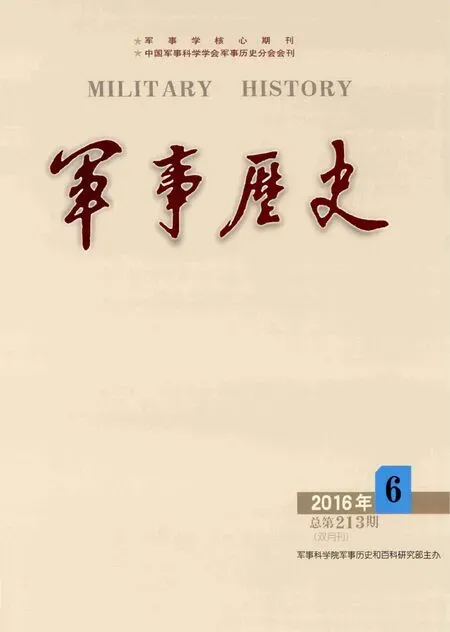《国语》战争观的两个重要特点
2016-01-06★
★
《国语》“以国分类,以语为主”,记载了上起周穆王,下至周贞定王500多年间的历史。从穆王征犬戎而国衰,到韩、赵、魏联合灭智伯,战争贯穿了《国语》的始终。因此,《国语》保留了西周中期至春秋末期大量关于军事思想的对话。这些对话集中于如何选择战争对象、看待战争目的,体现了《国语》战争观的两个重要特点,即重视对战争对象的合理选择、强调冷静准确地看待战争目的,对认识西周、春秋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重视对战争对象的合理选择
发动战争必须有合理的原因,合理选择战争对象是战争决策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国语》中涉及战争对象选择问题的对话有多处,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出自管子、子犯和富辰等人之口。他们的观点反映了选择战争对象的三个标准。
(一)以是否危害既定的利益格局作为选择标准。管子在回答齐桓公“吾欲从事于诸侯”的问题时提出了“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的观点*《国语·齐语》,卷六,管仲教桓公亲邻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管仲认为借助商人到天下各国去贩卖裘皮、丝帛以及玩赏之物的机会,可以观察各国君臣上下的喜好和追求,知晓诸侯各国的社会风气,之后选择骄奢淫逸的国家作为征伐对象。当时的战争决策者按照“周礼”的规定将破坏礼制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原因,即淫乱礼制者败坏社会规范和风气,如不加以制止,将损害西周以来既定的社会秩序,所以有必要进行军事征伐。与之近似的是仓葛的观点。周天子将阳樊赐予晋文公后,阳樊人不服,晋文公以兵围之。阳樊人仓葛说:“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国语·周语中》,卷二,阳人不服晋侯。意思是说晋军征讨的对象应该是“蛮、夷、戎、狄”中骄纵淫逸、不服王化的部分,而不是“皆天子之父兄甥舅”的阳樊人,晋文公对阳樊人使用武力的做法是“玩而顿”,不妥当。仓葛认为晋文公“若惠及之,唯官是征,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师!”因为这种看法符合周礼,所以晋文公也承认仓葛所言“是君子之言”。
郑桓公曾经向史伯请教避祸之计。史伯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得出“非亲则顽,不可入也”的结论,然后认为“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国语·郑语》,卷十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史伯对战争对象的选择判断非常准确。因为虢叔和郐仲都是骄纵奢侈、懈怠疏忽之人,再加上对财富的贪婪,一旦周王室因祸乱而衰落时必定会背叛把妻子儿女以及财富寄存到他们那里的郑桓公。到时候桓公统帅成周的军队,奉周天子的命令讨伐其“背君”之罪,就一定能够成功立国。
如果遵守既定的利益格局,就不能作为战争对象,否则会自乱章法,损害权威。为了劝阻周穆王“征犬戎”,祭公谋父首先搬出了先王规定的甸、侯、宾、要、荒等五服之制和“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的惩罚措施,然后提醒穆王犬戎一直谨守礼制,且“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国语·周语上》,卷一,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不能作为征伐对象。如果“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不仅会师出无名,而且会导致“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的严重后果。后来“荒服者不至”的事实证明了祭公谋父判断的正确,穆王的草率之举换来的是周王权威严的消解。
分析管子、仓葛、史伯、祭公谋父的论述,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军队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如果出现危害既定社会秩序的力量,比如叛乱,就要出动军队予以惩罚。对残民者、不守礼制者用兵就是以有道伐无道。春秋时期开始的争霸战争大都源自于此,所以有“尊王攘夷”的旗号。反之,对遵礼者用兵就是滥用武力,不仅会使自己陷入不义,而且肆意使用军队也会进一步破坏现有社会秩序。
(二)以是否具有争胜的精神状态作为选择标准。城濮之战前,晋军首先后退30里以避楚军。晋军军吏认为“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矣,必败。”子犯不同意这种判断,回击说:“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众莫不生气,不可谓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国语·晋语四》,卷十,文公救宋败楚于城濮。这里的“壮”与“老”反映的是部队不同的精神状态。子犯认为两军作战,理直的士气就壮,理曲的士气就衰。晋文公没有报答当年楚王的恩惠而出兵救援宋国,晋国理曲而楚国理直,所以楚国的将士没有一个不生气勃勃,不能说他们疲惫不堪。如果晋国国君退以避楚臣子玉,就算是履行当年报恩于楚王的承诺,若楚军还不撤军就会变得理曲。子犯认为如果战争对象站在正义的一方,就具有昂扬的战斗精神和发自内心的战斗积极性,此时就要主动回避,不要正面冲突,并力求使对方失去正义性以及与之相伴的作战士气。最后晋军退避三舍,甚至连楚军将士都主张应该停战撤军,但是刚而无礼的子玉却不肯,反而更加趾高气扬,结果楚军在理屈气衰、士气不高的情况下与晋军开战,导致楚军大败,子玉也落了个兵败自杀的结局。
韩原之战前,晋惠公向韩简询问秦“师少于我,斗士众”的原因,韩简答道:“以君之出也处己,入也烦己,饥食其籴,三施而无报,故来。今又击之,秦莫不愠,晋莫不怠,斗士是故众。”*《国语·晋语三》,卷九,秦侵晋止惠公于秦。秦国有三施之恩于晋国,而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以德报怨,致使秦穆公亲率大军进攻晋国。晋惠公也认可晋国对秦国“三施而无报”和秦军斗志旺盛的现实,承认晋军缺乏正义,士气衰怠。晋惠公只是考虑到“今我不击,归必狃”的尴尬处境,为顾及面子才勉强派韩简向秦军挑战,犯了用兵之大忌。可以说晋惠公兵败被俘的根本原因就是多行不义而使军队失去了旺盛的斗志。
分析子犯、韩简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战争决策者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战争的正义性与部队作战士气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确立己方在战争正义性方面的心理优势,从而激发己方的作战积极性、瓦解对手的作战意志。
(三)以战争的结果是否于己有利作为选择标准。周襄王因为郑滑之争,将郑国视作军事打击的对象,并计划“以狄伐郑”。富辰引用周文公在《诗经·小雅·棠棣》篇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句子提醒“郑在天子,兄弟也”,反对“以小怨置大德”的“伐郑”决定。因为借用狄人的军队攻击自己的兄弟之国是“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狄,不祥;以怨报德,不仁”,“不劝谏说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所以富辰劝谏周王不能一怒而失“三德”。*《国语·周语中》,卷二,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富辰主张在发动战争前要首先进行利害判断。只有当预期的战果于己有利时才可以兴师。富辰的分析建立在“阋乃内侮,而虽阋不败亲”的利害关系基础上,况且“兄弟之怨,不征于他,征于他,利乃外矣”。可是周襄王“不忍小忿而弃郑,又登叔隗以阶狄”,怒而兴师,“降狄师以伐郑”,不仅导致两败俱伤,而且引狼入室、埋下后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愚蠢之举。
伍子胥在劝谏吴王时,已经开始运用地缘政治理论分析与越国求和的弊和失,认为吴国一定要将越国作为战争对象,因为灭越有利而存越有害。当吴王夫差听信文种,允许越国求和时,伍子胥明确反对,因为“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吴江、钱塘江、浦阳江三条大江环绕着吴国和越国,民众不能迁徙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因为“陆人居陆,水人居水”,所以即使吴国进攻并且战胜了中原的诸侯国家,也不能居住在他们土地上,不能乘坐他们的兵车作战。可是“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国语·越语上》,卷二十,勾践灭吴。夫差没有听取伍子胥的建议,最终兵败、身死、国亡。
《国语》记载的上述三个标准具有内在的逻辑顺序。首先是战争对象具有挑战、危害现有秩序、利益格局的行为;其次是战争对象因失去了对战争正义性的判断,缺乏争胜的精神状态;再次是从利害判断角度看战争的最终结果一定是于己方有利。战争对象选择得当,就可以充分发挥战争的积极作用,否则就会带来负面效果。
二、强调冷静准确地看待战争目的
确定战争对象后,就必然要考虑战争目的问题。《国语》中涉及认识战争目的的对话也有多处,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出自单襄公、臧文仲和祭公谋父等人之口。他们的观点反映了认识战争目的的三个视角,如何看待战争目的,一般与如何选择战争对象有对应关系。总体来看,战争目的就是消灭或震慑破坏利益格局的战争对象、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民众利益。
(一)将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目的。晋国在鄢陵之战大胜楚国后,派郤至向周天子告捷,郤至向邵桓公等人自我夸耀“五胜以伐五败”的战前决策和“勇而有礼,反之以仁”的战场表现。郤至的看法遭到周大夫单襄公针锋相对地驳斥。就战争目的问题,单襄公说:“夫战,尽敌为上,守和同顺义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国语·周语中》,卷二,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经典地阐明了战争的直接目的,即以歼灭敌人为主要目的,如果不使用武力则要以敌人顺义降服为主要目的。针对郤至的夸耀战功,单襄公深刻地指出统帅军队要果敢刚毅,治理朝政要按序位成事,但是郤至却擅自放走郑国国君而危害了国家利益;抛弃作战的果敢刚毅而向楚国国君行礼是羞耻;背叛国家利益而去亲近仇敌是用诈伪的手段窃取仁义。郤至的上述行为都与战争目的相违背,事实上损害了晋国的利益,但他却认为这是勇、礼、仁的表现,值得夸耀。单襄公认为郤至是“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是对仁、礼、勇的亵渎。郤至有这三种耻辱的行为却“佻天之功以为己力”,想替代在他之上的正卿,执晋国国政,所以单襄公用当时的谚语“兵在其颈”形容郤至的危险境况,预测了郤至的结局。果然“郤至归,明年死难。”可见,如果将领对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认识不清,沽名钓誉,沾沾自喜于所谓“战果”,进而要求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必定会自取其祸。
(二)将巩固秩序作为战争目的。卫成公亲楚而不亲晋,不借道给晋文公讨曹伐楚,故晋文公想借周襄王之手杀掉卫成公。鲁正卿臧文仲进言劝说鲁禧公出面向周襄王、晋文公求情,以救助卫成公。他说:“刑五而已,无有隐者”,“卫君殆无罪矣”。臧文仲认为既然不能用五刑来惩罚卫成公,卫成公大概就没有罪。鲁禧公出面求情一定可以提高鲁国的政治地位。为了说明其中的道理,他解释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国语·鲁语上》,卷四,臧文仲说僖公请免卫成公。可见当时的刑罚分为“大”“中”“薄”等三类五种,大刑是用军队讨伐,其次用斧钺杀戮;中刑用刀锯截肢,其次用钻笮刺字黥面;轻刑是用鞭子笞打,目的都是为了威慑民众,维护秩序,所以用甲兵、斧钺杀人于野与用刀锯杀人于朝堂和街市,本质上都一样。在臧文仲看来,战争是刑罚的最高形式,军队是实施刑罚最重要的工具。范文子也有“夫战,刑也,刑之过也”*《国语·晋语六》,卷十二,范文子论外患与内忧。的观点,即战争的实质是一种刑罚,而且是用来刑罚过错。
祭公谋父之所以对穆王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就是因为“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国语·周语上》,卷一,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他认为先王都是彰明美德而不炫耀武力。聚集兵力只是在必要时动用,就是为了使军队一出动就显示出威力,让人畏服。随随便便地炫耀武力是一种玩弄军队权威的游戏态度,容易使军队失去震慑作用。更严重的是,劳师远征既会损害国威,又会丧失人心,导致政局不稳。所以国家不可滥用武力,治国需要以德服人。他引用《诗经·周颂·时迈》中周公歌颂武王的诗句“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希望穆王继承传统,偃武修德、敬德保民,“保世以滋大”。仓葛在指责晋文公时也说:“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国语·周语中》,卷二,阳人不服晋侯。意思是说滥用武力将会失去威严,隐藏文德将会德化不广,因为“觌武无烈”适得其反,所以“武不可觌”,不应“尚武隐文”,而应“隐武尚文”。
(三)将恤隐除害作为战争目的。祭公谋父在分析“不观兵”时并非全盘否定讲武、用兵,只是否定草率动武、穷兵黩武、滥用武力,而不反对正当用兵。他引用武王伐纣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正当用兵:“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国语·周语上》,卷一,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祭公谋父认为“恤民隐而除其害”就是正当用兵的目的。民众不能忍受纣王的残暴统治,都痛恨纣王而拥戴武王,希望武王救民于水火倒悬。武王也并不是崇尚武力,而是忧虑民众的痛苦,不得已出兵商郊牧野以除祸去患。晋文公出兵镇压阳樊恰恰不是“恤民隐而除其害”,结果激起了阳樊人的反抗。仓葛面对强大的晋军,以“德治”立论,指责晋文公恃强凌弱,不能以德服人。话说得有理、有节,最后迫使晋文公解除对阳樊的包围,让阳樊人民自择去留。
下邑之役,家臣董安于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认为有治绩该赏而未赏,因战功而赏是“以狂疾赏”,不是“必赏”,于是不接受赵简子的奖赏以示抗议。他说:“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女’,与余以狂疾赏也。”*《国语·晋语九》,卷十五,董安于辞赵简子赏。他的理由是赵简子重战功而轻治绩。如何评价董安于对战争的认识?战争一定是“狂疾”吗?赵简子与邯郸大夫赵午、午子赵稷等人的军事冲突是晋国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典型代表,视为“狂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片面性。如果将董安于的观点放在对战争的整体认识上时,这种片面性就非常明显。战争是现实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董安于站在个人角度形成的视战争为“狂疾”的消极认识毫无疑问是对战争的简单化理解,不能看作《国语》对战争“最深刻、最闪光的认识”和“先秦战争观念中最可宝贵的遗产”*刘伟,胡海香:《〈国语〉战争观初探》,载《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国语》关于战争目的的认识已经不只是着眼于军事领域的战场决胜,而是由战场决胜延伸到了政治领域的巩固秩序、恤隐除害等目标。虽然《国语》没有《战争论》对战争本质简洁深刻的分析总结,但已经认识到战争目的绝不能仅仅视为军事目的,而必须服从服务于政治目的,满足政治需要。这代表了当时战争观发展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