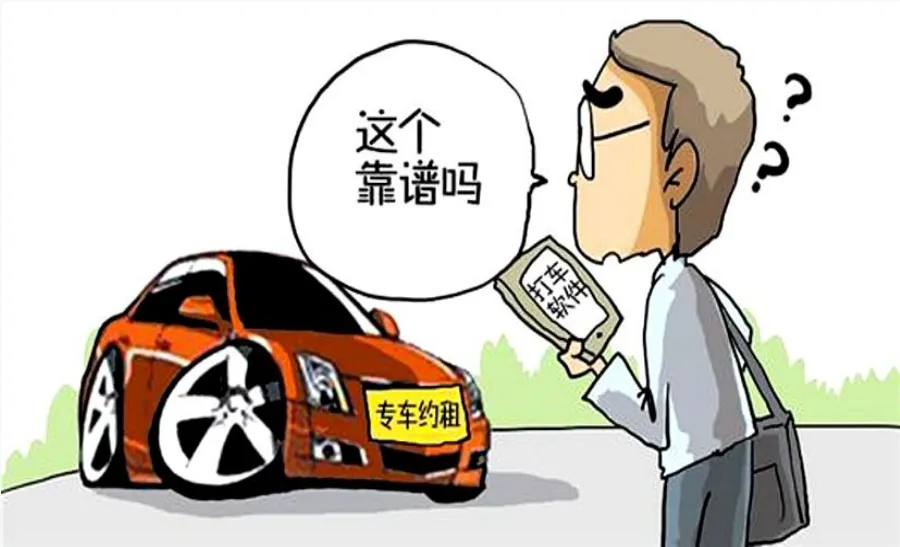“互联网+专车”叩响法律之门
2015-12-27莫岱青
■莫岱青
“互联网+专车”叩响法律之门
■莫岱青
一、事件背景
2015年1月7日,使用滴滴专车软件在济南西站送客的陈超,被市客管中心的执法人员认定为非法运营,罚款2万元。因不服处罚决定,陈超向济南市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市客管中心撤销处罚。
2015年3月30日,济南市中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此案,于4月15日开庭。这是全国首例因提供专车服务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也被称为“专车第一案”。
案件审理后,滴滴公司表示,通过媒体报道了解了济南专车第一案的相关情况,暂无法对于案件本身做任何评论,希望法律能给予公正合理的裁决。
这起案件的核心问题是滴滴软件提供的专车服务是否合法,所有关注这起诉讼的人关心都是滴滴专车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曾表态,对于专车业务,不要一棍子打死。虽然有了“互联网公司认证”这层外衣,也的确方便了不少市民的出行,但对很多城市的运管部门来说,即便套上了马甲,专车还是不合法。
二、专家观点
为了更全面剖析“互联网+专车”背后隐藏的法律问题,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特约研究员、全国知名电商律师特发表本点评,供参考。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
本案主要有四点争议:一是被告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二是处罚程序是否合法,三是做出处罚的事实证据是否充分,四是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庭审过程中围绕这四点争论很激烈。
关于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按照行政处罚法,只有行政机关才有行政处罚权,当然也有例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经过法律、法规授权也可以。被告客管中心的性质确实是事业单位,原则上来讲没有处罚权,关键看它有没有法律法规授权,被告提供了一些证据,其中一个是济南市政府办公厅的文件,其中规定了把公共客运管理职责划归济南市交通运输局,并规定把客运管理办公室改名成客运管理服务中心,也就是被告现在的名字,并负责公共客运的监管。依据这个文件基本可以认定被告是有行政处罚权限的。除了这个证据之外,被告还让济南市交通运输局提供一份材料,目的是证明客管中心得到授权,没有看到这份证据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这不是一份具体的法律法规,只是交通运输局单独出的一份证明材料的话,单靠这个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有授权。
出租汽车行业是管制行业,从事营运活动需要资质,得具备三证: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者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显然原告没有这些资质。但是,需要这三证的前提是认定原告从事了营运活动,而认定营运的关键要看两点:一是看车主和乘客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认识,要认定构成营运,一般是陌生人关系;二是看是否收取费用,是否以营利为目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主要是现场录像、现场笔录,其中证明陌生人关系主要是乘客当时的口述,但乘客口述前后不一致,刚开始不承认,而费用方面,乘客当场承认,但是现场没有支付,事后被告也没有取得这个证据。所以被告据以处罚的证据还是存在瑕疵的,关键看法院能否采信。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吴旭华律师
关于专车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成了这一电商模式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电子商务以强势的方式介入传统行业,传统行业既得利益者奋起反抗,也可以理解。只是进入听闻北京运管部门已经正式对专车进行查处并予以处罚,这一消息传来,似乎已经给专车电商模式画上了句号。
车辆挂靠运输公司,以运输公司名义和客人发生运输法律关系,并没有违反现有的法律规定,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运管部门的认可。在民事经营领域,没有明确禁止的规定即为允许,既然没有禁止,为何反对之声群起,甚至发生多地出租车司机罢工、停运、上街堵塞交通呢?
现有出租车运营模式积重难返,出租车运营证天价交易,运管部门作为既得利益部门自身监管不力,出租车司机被剥削厉害无法保证合法权益,这些都是造成强烈抵制专车运营模式的原因。
但是,市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消费者显然可以在合法的体制下选择不同的服务模式,如果只是一味迎合运管部门和既得利益者的权益,那么消费者的权益怎么获得保障?而且电子商务进入传统行业已经势不可挡,即使存在一些障碍和瑕疵,也完全可以通过协调得到解决,因噎废食那是野蛮人的做法。
专车,专业服务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肯定,法律服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麻策律师
用户围绕“车辆”这一标的物在实践中衍生了诸多商业模式,实际上可以分为“出租汽车服务”和“汽车出租服务”两类。“出租汽车服务”即类如城市出租车营运、城市公共交通,因事关民生问题和公共利益,因此需要获得行政许可并取得营运资质;“汽车出租服务”的商业模式非常之多,如租车服务和代驾服务等,该类服务是为满足特殊化个性化用户需求而定制,只需要运营主体进行工商登记即可,无须取得行政许可。
目前专车公司皆将自己定义为“信息服务”的媒介,为用户、司机、汽车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提供交易摄合。因此专车服务应当定义为一种“汽车出租服务”,只不过在互联网+的大发展趋势下,专车公司有更好的平台技术依托,能够实现用户、汽车租赁公司、劳务公司信息的“瞬间结合”。对于“专车第一案”而言,行政主管机关实际上混淆了两类商业模式背后不同的法律关系,这才是专车合法还是非法的界限症结所在。“专车第一案”中原被告双方纠结于济南客运管理中心是否具有行政处罚权,以及处罚程序和证据问题,对于专车行业正常发展的社会意义并不大。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董毅智律师
针对“专车第一案”,主要的的矛盾和焦点在于政府是否掌握合理的执法依据和尺度。
首先,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享有有关城市客运管理方面行政处罚权的是济南市交通运输局,运管中心属自收自支的处级事业单位,不具有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对非法运营的处罚权应属于交通局,运管中心并不属交通局的行政机关。
其次,非法营运是指没有依法取得营运权而实施了营运行为,即未按规定领取有关主管部门核发的营运证件和超越核定范围进行经营。按照以往的行政惯例进行裁量,合法运营需要两证,一是道路经营许可证,二是汽车营运证,二者缺一即构成非法运营。但专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裁量惯例。因为专车运营是按照四方协议模式来进行,乘客、软件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劳务公司之间达成四方协议,专车运营实际上是汽车租赁服务和劳务服务的结合,出租汽车管理的规定并不完全适用于专车运营模式。
专车作为近年来“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因为便捷性、人性化的服务特质,受到用户的好评,当然,新生事物的出现,在法律制度存在滞后性并不意外。在此案之前,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法律到底应该如何抉择?这个案件之所以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在于审判结果可能给一直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专车一个明确说法。互联网专车在法律上将如何界定?技术对于经济的推动,能否倒逼法律的完善?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王冰洁律师
目前专车主要有两种运营模式,第一种是由打车软件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赁运营车辆,并与劳务派遣机构合作寻求有资质和业务能力的司机,这种专车模式下的车辆及司机受到专车公司统一管理,由专车公司向消费公众负责;第二种模式是专车市场需求巨大,各大专车平台引入私家车车主带车加盟模式来迎合需求缺口,经营收入一般由车主与打车平台之间分成,车主拿80%,平台拿20%,车辆及人身损害等风险由车主自担。
第一种专车模式更加符合我国目前车辆运营市场的现有规定,专车运营是按照四方协议模式来进行,乘客、软件公司、汽车租赁公司、劳务公司之间达成四方协议,专车运营实际上是汽车租赁服务和劳务服务的结合,这种模式并不被法律禁止,符合民法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律精神,他解决了车辆运营资质以及司机资质问题,在乘客的人身安全性上由专车公司负责和兜底,从而更好保障消费公众安全和道路运输安全。
而私家车车主带车加盟模式,并不能被定义成“专车”,更不能与“黑车”划上等号。私家车辆为非运营车辆,非运营车辆的年检、强制报废要求很大程度上低于运营车辆,在车辆安全性、司机驾驶技能、及私家车主的道德风险在没有企业、没有政府等第三方的统一约束和设置准入标准下,仅凭车主自身的自律显然不利于专车市场及消费公众的安全。目前各大城市交通部门打击的“专车黑车服务”正是这种私家车接入专车现象。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助理分析师沈云云认为:
专车模式是一个新生事物,打车软件提供的服务是当下最时髦的“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对于面临资源和环境难题的如今社会来说,“共享经济”在各个层面上被赋予了重要的创新意义。随着消费者定制化、个性化用车需求的浮现,“专车”服务迎合了市场需求,对专车“一禁了之”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国内专车需求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专车”模式若想在中国走向成熟,监管制度、自身模式都需进一步完善。商务租车在短时间内很难摆脱非法营运和黑车洗白的标签,专车处于起步阶段,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隐患,也触动了其他方的利益,急需相关的规范和管理约束,才能开辟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