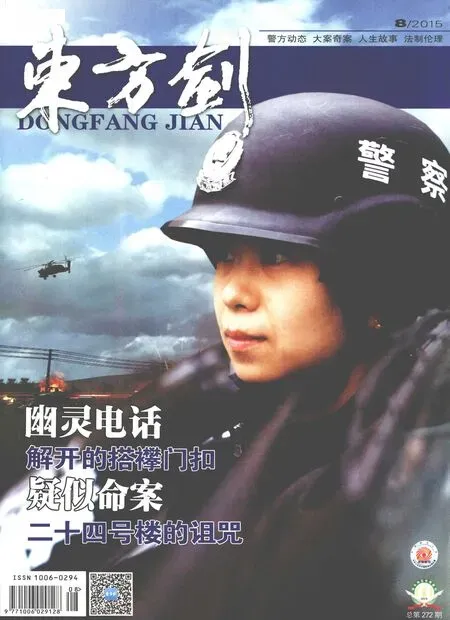解开的搭襻门扣
2015-12-26邵江红
◆ 邵江红
解开的搭襻门扣
◆ 邵江红

山里的夜来得早。春梅去前头姨婆那屋还了针线,转回自家屋门口的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她刚要去解屋门上的搭襻门扣,发现搭襻扣已经解开在那里,铁攀垂落着,那样子有些陌生。咦,她明明记得刚才出门的时候,搭襻扣是扣上的啊。
这就像一根针,无声地刺进了没有涟漪的夜里。
算起来,春梅去还姨婆针线的那天是1950年初冬的某一天傍晚。这一天,家里只有春梅和她的儿子,小孩子才一岁多的光景。丈夫宝银和他的伙伴们两天前出脚力去了。这山里民风淳朴,前脚后跟地离开一会,只挂个门搭襻,谁家也不会上锁。春梅立在门前,左右环顾了一会,一个人影也没有,心里狐疑着,还是推门进屋,随手点亮油灯。油灯的火苗由小到大,稳定成一簇跳跃的光源,将小屋照得有点暖意。春梅就这么拿眼朝屋里四周一望,觉得这屋里和刚才出门时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她说不上来。也许是头次碰到这样的怪事,春梅的直觉敏锐不过。可是也就这么怪,要说这春梅也没有特异功能,她就是觉得不对劲,那种不对劲不是屋里的物品被翻动过或者缺东少西,那是一种浮荡在空气里的丝丝缕缕的气息,不属于这屋的某种气息。
春梅转身抱起孩子出门,这回她只是将门拉拢。她特意不扣上搭襻扣,潜意识里也为自己的不祥预感留一扇消弭的门。她一路小跑来到长寿小伯家,长寿小伯是我们村管事的,也就是村长。春梅拍响门板,长寿小姆妈就来开门。春梅进屋后就如此这般地将事情说给长寿小伯听。长寿小伯当即叫了两个儿子,又到隔壁叫了老民兵二狗阿叔和他的堂兄弟等,六七个男人来到春梅的屋里。春梅刚才点燃的油灯依旧亮着光。男人们进屋,在这个一目了然的两个半间屋里,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包括木箱的里面,床的底下,灶头旮旯,二狗阿叔还掀起水缸的盖。这水缸里的水是满满的,宝银在出脚力之前都会为春梅挑满水。水缸的盖一般都是两个半圆的木板合拢做缸盖,一来防尘,二来翻起一半就可方便舀水。二狗阿叔翻开水缸外半圆的缸盖,看了看水,又将盖子盖上。该检查的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男人们撤退,嘱咐春梅关好门窗。
第二天天放亮,山里人起得早,春梅有个小姐妹叫水粉的来春梅家说事,发现春梅家门没有关紧,她推开门,见春梅倒在地上,早已没了气息。
我们村坐落在浙东崇山峻岭的一个小山坳里,四面环山,满目翠绿,从地形上看这个山坳就是一个竹篓子的肚底,窝在山的怀抱,出口细小如瓶颈,山路崎岖难行,全靠一代一代的脚力维系着村里和几十公里外的集镇的联系。我们村的第一个官名,就叫篓底村。这话说起来就有些早了,春梅是我们村几十年里最漂亮最能干的女人,据说她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眉眼自然是生得标致,而且条干长得好。她的手工活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缝制出来的长衫小袄,都是大小合适,针脚工整。婆婆妈妈要为自己屋里人做衣服,都要春梅看个样。春梅自己身上穿的,按照我奶奶的说法,那叫一个俊。我想象,她一定盘着一个大发髻,一件中式大襟上衣,一条玄色直通裤,就像电视剧《大宅门》里的大脚丫头,穿出美美的腰身。
这漫长的大半个世纪里,春梅之死就像一枚钉子,嵌在篓底村的岁月里,成了一只死角。等我渐渐懂事,我所知的篓底,竟然是和春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似乎春梅是篓底的一个著名符号,到了谁的嘴里,都会说一句“可惜了那春梅、可怜了那春梅”。我紧追不放地问奶奶,那春梅到底是怎么死的?
奶奶说,小女娃娃不用听,听了坏耳朵。但是春梅,这个活在篓底晨雾里、竹林中、针线穿行间的美丽身影,已经进了我的眼睛,坏了我的耳朵。那个时候我就会在奶奶刹住情节之后发表狂想,因为我已经囫囵吞枣地看过几集《福尔摩斯探案》的小说,特别想为春梅之死挖掘别人看不到的线索,那是我十三岁的梦想。我们村在社会不断的进化中已经等不得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断地陆续地有人家搬到集镇上或者更远的城里去生活,就像我的爸爸,读书读得离家越来越远,这篓底已经成了爸爸的故乡。但我还是要把它唤成我们村,我是觉得篓底肯定有一样东西紧紧吸引着我,促使我不断地在隔一段时光隔一段时光地要回到这里。村子已经很寂静了,几近是个留守村,三三两两有老人在屋门口做活或者端着碗吃饭,就好像村子长期地在午睡。但是我喜欢这样的安静,安静得非常干净。当我走在村里高高低低的石阶上散步的时候,飘入耳朵的丝丝缕缕都是天籁,我时常会这样走着走着走向春梅那屋的地方,就仿佛有谁在引领我似的。那房子早已坍塌,残壁倒是有的,还说明着这里曾经是一个家。
奶奶的讲述中,宝银和阿根也是重点人物。宝银和阿根是一对好朋友,阿根年长宝银有个近十岁,处处像长兄一样关照宝银,特别是在外面出脚力的时候,阿根宁可自己苦着累着也要让着护着宝银。宝银回家后就会一五一十讲给春梅听,春梅自是非常感激阿根。他们不出脚力的时候,宝银经常会喊过阿根来,春梅做几个小菜,两人喝点自家做的米酒。
阿根家的老婆是阿根在山外出脚力的时候带回来的,不是本村媳妇。那媳妇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高个头。按照小叔公的比画,我猜测那媳妇该有个一米七的样子,这在当时已经是一般以上男子的个头了,更何况她还长得壮实,粗大的嗓门,大脸小眼。阿根家穷,他在山外某个村子遇到了这个女子,这女子已经二十好几了,因为长相的关系,按照现今的说法,是个剩女。但是阿根就要了她,阿根看到了她的优点,那女子着实有男人的劳力。当时阿根给她家里留下身上所有的现金,就带着回村里拜了堂。长婆媳妇也争气,十年光景生下三个儿子,也正因为上下三代七张嘴巴吃饭,阿根家的境况一直穷兮兮。

农闲的时候,春梅剪鞋做褂,引来一帮妇女坐在家门口,手持针线,研究着手上的活计。这时候,村里哪个孩子鞋口裂了,哪个汉子褂子开了,都会跑到这里来,妇女们会放下手中的活,现场办公给缝补好。阿根的褂子掉了扣子,也会往春梅家跑。春梅说你等下,我找块近色的角布,帮你打个扣。那个时候,塑料扣估计还没有流行,村里人常用的还是布襻扣。阿根就坐在门口的石级上,看针线在春梅的双手里上下翻飞。有男人在的场合,女人们也扯些荤话,脸红的不是别人,而是阿根。阿根红了脸,成为妇女们取乐的对象。有好事的妇女问阿根:“你家媳妇会生孩子会干活,还会针线不?”阿根就会红着脸说:“没你会。”
春梅看阿根家的几个孩子们,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穿在身上的衣裤鞋子,永远是凌乱而破旧,这个时候她就会想起阿根,想起这个男人时不时流露出的羞涩,心里便会生出些许很柔软的东西来,好像阿根吃什么亏了似的,着实地可怜他和同情他。阿根来屋里头坐的时候,春梅总拿最好的招待他,或者塞个鞋垫递个坎肩,春梅便熨帖地接过阿根有些无所适从的感激。春梅也会偶尔给阿根家的孩子们缝一些衣裤,长婆媳妇捧着衣物感激涕零,穿在孩子身上样样合身合体,老少高兴,夸春梅的手艺夸孩子的精神。晚上关门落栓的时候,她才在房间里咬牙切齿:“狐狸精,你有本事,专门勾引男人,勾引男人的魂,去死,去死。”隔窗有耳,这话被后窗外走过的小叔公听见了。
和奶奶睡一张床的时候,常听奶奶讲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比方说老鼠如何偷罐子里的鸡蛋,黄鼠狼在生命危险的时候怎样放一个特臭的臭屁,还有谁家的童养媳怎样怎样的苦,她娘家的舅舅晚上如何着魇……反正都非常好听,很有情节。后来奶奶说故事都讲光了,等有了再讲。我想一想,就说,那你讲春梅吧。奶奶说,已经讲到春梅被害死了,没什么好讲了。我就说,那讲春梅的丈夫吧,他没死。
奶奶那辈,是不兴男女自由恋爱的,姑娘十五六岁起父母就会操心张罗婚事,主要的选择标准是男方家境是否还好,小伙子是否健康。因为不兴恋爱,所以也不见离婚。宝银家是最早落户篓底的村民,因为家里没断过丁,又是村里的传代脚力,境况相对而言不算十分穷。但是宝银个头长得小,虚力。奶奶就拿我认识的村里的几个老年男人做比方,我想宝银年轻时最多也就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子。宝银个子小,但是嘴巴活络,人情好,所以会得到旁人的相帮,阿根就是一个时常护着他的大哥。阿根长得俊啊,身板也扎实,心肠也好,从不骂媳妇,一个大男人还说不得地常脸红。奶奶说阿根的时候,脸色是美好的。说实在的,春梅的美和阿根的俊,反映在我的脑海里就是他们俩才是最好的一对,宝银和那个长婆都是不恰当的掺和,都是一种破坏。
“宝银矮小,又走脚力,村里对春梅动坏脑筋的男人自然是有的。”说到这儿奶奶就怎么也不说了,任我怎么催都不说。
好在我能聊,在村里遇到的老人,都是爷叔辈的,我喜欢和他们聊,聊生活也聊春梅。
谁是动坏脑筋的可疑男人?
我们村的那山坳,坳里也不是一块锅底似的平地。二三十户人家散落着,沿着山脚斜坡,高低参差地散落,大多独门独户。有的两户之间隔条小溪,有的坡上坡下间隔一个竹园呢。我最喜欢春天时候的篓底,竹园里春笋滋溜滋溜往上蹿,从地里挖出来,剥剥洗洗入水煮,用盐一撒,出锅就吃,那叫一个鲜。如果夜间落过春雨,第二天太阳亮亮地起来,会显得特别地新鲜,好像昨晚的落雨它一点也不知。阳光招呼着,这时候的笋多得像冒泡似的,来不及吃就会转眼长成竹竿。村人就抓住这亮晃晃的太阳,忙乎乎晒笋干,家家门前白花花一片,凑近了闻得着笋干的芳香,馋人得很。笋干做菜,那是山里人一年的储备。
春梅挖笋,可是与做针线不同,那靠的是脚上的功夫。她穿一双薄薄的旧布鞋,双脚在竹园里绕着竹子趟过去,用脚底板感触泥地里的笋尖尖,脚底板有了抵触就弯腰用短柄锄头刨开泥土,一记深挖,肉乎乎的笋裹着黄泥就到了春梅手中。山里人有经验,已经有一截露头的春笋,就不是最好最嫩的笋了。
所以挖笋是赶节气的活。春梅全心在趟笋的时候,有人悄悄逼近,突然从右侧身搂住了她的腰。她瞬间转头,一张粗糙的脸已经近在眼前,一张嘴贴过来,口里的唾沫都涂上了春梅的脸。春梅别转头,用力挣脱,可以使劲的左手胡乱地打着对方,一边还“啊呀,啊呀”地惊呼。不远处有挖笋的在喊:喂,啥事啊?那男人受惊般地放手朝竹林蹿去。这人就是东村头的癞子阿大。春梅心里翻腾着恶心,脸色自然挂不住。回家后宝银问她为啥事情?春梅没有说,她怕男人发火闹出大事体。
尽管春梅经常帮着村里人做点针线活,但就是有人专等宝银出脚力不在家,瞅着傍晚时间去春梅屋里求春梅补衣裤。春梅不好拒绝,将衣裤拿过来,隔着桌子为他缝了,却就是不见走人。春梅几次说天色晚了孩子要睡了,那人就是厚着脸黏糊。然后他探起身子凑过小桌面,指着春梅手里的衣服说:“喏喏,这里也给我缝几针,喏喏,还有这里……”指指点点的时候,不忘触碰春梅的手背。就在连空气都显得尴尬的时候,突然窗外“哐”的一声脆响,像是罐子砸破,屋里的那人倏地起身,走出门外看看,骂一句该死的猫砸了罐,这才拎了自己的衣裤走了,这人是老光棍阿堂。
还有,还有……反正有两夫妻吵架来着,丈夫冷不防就会这样骂老婆:“你看看人家春梅,啥事都做得勤勤快快有模有样,你鸡娘一样地笨,哪样及得了她……”
山村闭塞、民风淳朴也阻挡不了心思的诡变,春梅和姨婆亲,有些心思会和姨婆叨咕,姨婆就告诫她,宝银不在家的时候早点关门落栓。春梅也是乖巧的女子,守着孩子,日落闭户,除了那一天,晚饭后见天色还早,就抱着孩子去姨婆那里还了针线。
春梅死了,一起死的还有春梅的儿子,村子里就像炸开的油锅一样。
长寿小伯是主事的人,他让我奶奶和长寿小姆妈两个人进屋,将春梅和孩子安置到床上。让自己十三岁的小儿子去乡公所报告。
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在春梅家门前,长寿小伯说,在政府的人来之前,所有的人不许离开村子。
我奶奶和长寿小姆妈给春梅整衣裤的时候,看见春梅和儿子的脖子上都有掐痕,春梅还被奸污过。怕弄脏了春梅的名声,我奶奶和长寿小姆妈没有将春梅被奸污过的事情公布出来。
那么是谁杀死了春梅母子,谁与他们有这么大的仇恨?
春梅没有仇人,宝银也没有。年轻的小叔公这时候说了句话:“长婆媳妇呢?长婆媳妇要春梅姐死,我听见她在屋里咒了……”

长婆媳妇绝对有男人一样的体力和手力弄死春梅,长婆媳妇咒骂狐狸精的情景立即让所有村人回忆起来,这是绝佳的线索。当即有人冲向阿根家里,将长婆媳妇拖了出来。长婆媳妇只知道春梅被自己咒死了,春梅真死了,她也是悔青了肠子,哪怕春梅真是迷了丈夫的狐狸精,她也不想咒死她的。当几个壮汉来家里拖她,她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早已吓得浑身无力,小便失禁,瘫坐在地上。阿根的娘跪在地上给汉子磕头,说饶了她吧!饶了她吧!三个娃娃哭天抢地抱着娘的身子不让走。
我奶奶闻声挤出人群,她大声地说:“不能再出人命了,这事儿不是长婆媳妇干的,放了她吧。”
村人没有理会我奶奶的疾呼,有人开始抽打长婆媳妇,长婆媳妇是来自山外的人,非亲非邻,当然有可能是凶手,更何况她在屋里咒骂春梅,春梅不死也难活。怒火开始燃烧起来,万分危急之时,长寿小姆妈不知从哪家拿来一只洗脸的铜面盆,用一块门栓板当棒槌当当当地敲击起来,声音洪亮而焦急,这是当地救火用的信号。果然,村人停了怒吼和拳头,狐疑地回头张望。长寿小姆妈大声说:“这事不是长婆媳妇做的,我们两个帮春梅擦了身子穿了衣裤,我们看到了恶人留下的脏物了,那一定是男人做的。”
如果时光后退四五十年,DNA技术将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可惜当年,这么重要的证据不算线索。
起风了,风从西北方向吹来,吹到我们村四处碰壁,因为我们村四面环山。无处可走的风在村的上空打回旋,形成了回旋风。阳光被隔离在天空的上方,回旋风发出的呜呜叫嚣直压村人的头顶。长寿小伯抬头望望天空,叹了口气。他说:“昨晚春梅离开屋子的时候,恶人已经进入了,躲在屋子里头了,春梅感觉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搜出来。罪过啊!”
“可是真的都搜查过了啊,就这么简单的屋子,恶人能躲在哪儿呢?”
“会不会是妖孽啊,妖孽是可以遁身的。”
“一定是外村人做的,我们村的人做不出来的。可是近日也没有外村来的脚力啊。”
“也许是我们搜查的人离开后,那恶人再进屋害人的。”
……
长寿小伯长叹一声:“你们长眼看看,这屋子有撬门破窗的痕迹吗?屋里有翻箱倒柜的样子吗?”
老民兵二狗阿叔突然大哭起来:“天哪天哪,那人是躲在水缸里啊,啊呀,天哪,我该死啊……”
空气冷得钻进棉袄,再钻进肌肤,切入血液,跟着循环。二狗阿叔跪在地上,气急败坏地神经质地诉说:“是我搜看的水缸,我只掀起半个缸盖,油灯放在桌上,光线照不到水缸里面,里面黑乎乎的,他一定躲在那水下。那水缸的水满着缸沿,宝银都出脚力两天多了,春梅母子俩吃用了两天的水缸水,岂能还是满到缸沿的,那里面是蹲着个人啊!”
几个壮汉于是走进屋子里,果然看到水缸旁的砖地湿潮潮的,掀开缸盖,只见六分多的水位。
夏天的时候小叔公和小伙伴经常在村里的池塘里玩水,其中有一种玩法是大伙憋着气沉在水里,看谁能在水里躲得时间更长。小叔公憋不过人家,一会工夫就蹿出了水面,所以总被大头脑子指挥着扮狗扮猫地叫。他深有体会地说:“那是神仙了啊,能憋在水里好久啊!”
长寿小伯思忖着,是啊,他们在春梅屋子里搜查,少说也有一刻钟的时间,谁能在水里一动不动狠憋?他仔细环顾四周,看出了名堂,灶头堆着麦秸秆,做柴火用的。麦秸秆中空,选择一根粗壮笔直些的,一头含在口里,一头伸出水面,就能做呼吸用。伸出水面的那一小节麦秆,二狗阿叔在盖着一半水缸盖子又是微弱斜射来的油灯光线里根本没看见。
有一年暑假,大概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老师布置的作业里有一项作业叫作手工制作,要我们发挥想象,做什么都行。我在奶奶家里做完了所有作业,眼看暑假要快结束了,急得团团转。还是奶奶救了我,她说编个小鸟小花篮的行不?我大喜,快快,教我。奶奶去柴火间取了一把麦秸秆,我就跟着她的样子,梳理出一把发着银光的麦秆子来,在淘米泔水里浸泡一阵,麦秸秆就变得很柔韧。再学着奶奶的样子,怎么折怎么拧怎么插怎么穿怎么剪,一个下午忙碌,大功告成。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奶奶编的叫工艺品,我编的叫试验品,但是我总归是编出来了。本来我可以将奶奶编的工艺品当作作业直接交给老师,但是心里非常矛盾,不仅仅是害怕弄虚作假,更关键的是那只小鸟和小花篮太精致太漂亮了,我舍不得交出去。之后的几天,我就躲在奶奶家的柴火间里,拿麦秸秆精心地编了拆拆了编,当我要离开奶奶的时候,小模样已经编得相当不错了。奶奶惊讶地拿起来看了许久,啧啧称赞,奶奶还说:“长得好看的女娃娃家,勿要太过心灵手巧啊!”
当时我还真没听懂奶奶这话的意思,后来我当了记者写文章的时候,偶尔会笔墨涉及到我们村和我奶奶,再想起这句话来,就明白了奶奶说的是啥。
长寿小伯就是在领悟杀人的家伙躲在水缸里用麦秸秆呼吸的重大突破后,又在饭桌的桌脚边找到了一只用麦秸秆编的小鸟。长寿小伯只看了一眼,说:“这是那恶人编的,这是我们村的人。”
我想,长寿小伯肯定是从那麦秸秆小鸟的造型和外观上看出异样,春梅的那双手,绝不会编出这等货色。
长寿小伯作出决定,全村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站过来,看看差了谁?
时光转过当午,呜呜叫响的风声弱了不少,但太阳依旧没有露头。长寿小伯在男人堆里点了所有的人头,一个不差。
我们村自古有一种说法,人屈死后如果没有审清冤情,是不能下葬的,下葬后死者的魂会不得安宁,始终会在人间寻找仇家,估计也会影响到无辜者的平静生活,所以人人都在指望害春梅的恶人能揪出来。这让主事的长寿小伯变得极其忧郁。
宝银是一时通知不到的,宝银的爹娘已经慌得没了主意,宝银的二哥跟在长寿小伯的身后,听候着调遣。长寿小伯说,报官了也不一定会有人来,尸体放不牢,先在屋后竹园子里挖墓吧。长寿小伯说完,又低头走进春梅的屋子。
我当记者那阵已是上世纪末,经常采写公安机关的侦破通讯,写到刑警在案发现场反复仔细勘验的时候,不时会想起长寿小伯的形象,他低头进出春梅的屋子,凝固着表情,警惕着目光,角落周遭,看了一遍又一遍,就像个刑警一样。还真是,有个情况被他看了出来。春梅做针线活有一套手用工具,集中放在一只青竹篾编制的小坦箩里,用得年代久了,青竹篾变成了褐红色,里面盛有戳着多枚长短粗细缝衣针的棉团、五颜六色的棉线、顶针套、布头布脑、短尺、画粉石……但是没有看见剪刀,春梅的坦箩里竟然没有剪刀,长寿小伯对身后的二狗阿叔说,叫两个心细的人进来,仔细找剪刀。
剪刀是小叔公找到的。
当年的我们村,无论屋大屋小,堂前的一隅都会砌一尊柴灶,灶肚口一张小矮凳,烧火的主妇坐在小矮凳上给灶肚塞柴火。为方便烧火,总是右手边堆待用的柴火,左手边靠近灶肚的地方放一只矮矮的石墩子,大多是鼓圆形的,就像和好后稍稍压扁的大面团。烧火时有较粗的树段、竹柱或者嫌长的树枝,就抵在这石墩上用柴刀劈一下砍一刀,然后塞进灶肚里。而春梅的那把手用小剪刀就躺在紧挨着小石墩的右侧地上,剪刀头朝着小石墩子,上面还有一层麦草浅浅地覆着。
长寿小伯凝视着这一幕,只觉得周身血液汩汩地加快了流淌的速度,他感知着有一个秘密即将揭开。他权威地挥了下手,叫身边的人退到门槛外面去。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挪开石墩,一样东西呈现在眼前。
那个年代的物资匮乏难以想象,一户人家几个兄弟合穿一件棉袄并非传说,有的甚至单衣薄裳抖抖索索也过冬。奶奶和我说起过,她出嫁的时候娘家给她做了一件棉袄,是很丰厚的陪嫁了,入冬后她就是靠这一件棉袄扛一个长冬,那是准备穿一辈子的。做棉袄的时候,里单布一般都是旧的包棉袄布衫改了做,里头的棉花老点不要紧,外单布一般会尽量考虑用新的或者半新的,脱出来不至于难看。奶奶说,妇女都做成花布外单的大襟棉袄,男人做的都是深蓝或藏青的对襟棉袄。这会儿,春梅家小石墩下压着的是一块三角形的深蓝色棉布,边线大约三公分长的样子,反面粘着一层薄薄的棉花絮。这分明是从某件男人的棉袄上剪下来的外单布,有半成新。
这时候的长寿小伯,浑身禁不住地颤抖,试想春梅一定为这个水缸里爬出来的男人烘过棉袄,一定在男人不注意的时候在棉袄的后背剪下了这块三角,再将棉袄与包棉袄布衫套好,不至于让那男人发现。她斗不过恶人,却为自己生命的死亡留下了伏笔,也为那畜生留下了声讨的记号。
长寿小伯走到众人面前,手心里托着那块蓝色的三角布,尚未开口已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男人都把包棉袄布衫脱下来……
众人无语,互相顾盼,尽管有点打愣,还是很服从长寿小伯的指令,有的男人已经开始脱罩衣,这时候,一个男人“噗”地跪倒在地,嘶声力竭地喊了声:“妈呀!”
现在我可以拼凑还原1950年那个初冬夜里春梅的遭遇。
春梅送走了男人们,关门落栓,将孩子抱到里间床上,安顿睡觉。油灯的火苗微微抖动着,四周便沉在黑暗里。我肯定,春梅对刚才感觉到的那种不对劲的警惕,丝毫没有消除,每做一个动作都是小心翼翼。这个时候,外屋哗啦一声响动,春梅愣了一瞬,她明白,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春梅那屋坐落在村子最南边,靠山而建,房间仅有的一扇小木窗,打开便是山体,没有可以翻越或躲避的出口。当时春梅也许根本没有想要那出口,她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立即循声走出里间,看见一个男人浑身湿淋淋地站着直打哆嗦,地上汪着一摊水。
春梅的惊心无以言表。男人抖索着说:“给我找件干衣服。”春梅不动。男人开始往里半间方向走,手已经快要触到了粗布门帘。
里半间有一岁多的孩子。春梅赶紧应诺着,去木箱里找出丈夫的衣裤。男人就在门帘边换衣裤。他说:“不要去开门,开门的话这孩子就没命。”
男人又说:“给我做点吃的。”
春梅热了咸菜和剩饭。
男人说:“给我将湿衣裤烘干。”
那时候的我们村,有幼儿的屋里,都会有烘尿布的竹罩,罩在燃旺的火盆上,尿布片膏药一样摊在竹罩上,尿片会烘得又干又消毒。春梅家的竹罩挂在灶壁墙上,她取下来,拨旺火盆,将湿衣裤拧干,开始烘,水蒸气很快腾腾地升起。男人吃饱了饭,从里间抱出孩子,装出很亲热的样子。孩子不从,要离开他的怀抱,他从地上捡了根麦秆,认真地编个小鸟哄他玩。孩子经不住时间,一会儿就睡着了。男人将孩子放在手边的桌子上,用块小被子裹着
正是初冬的节气,这男人穿的是贴身一件夹衣,一件薄棉袄,外罩一件包棉袄布衫,下身是两条单裤。春梅不断将竹罩上的衣裤翻来覆去,加速烘干。男人盯着春梅看一阵子,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门边,将脸凑到窗缝里、门缝里,眯上一只眼朝外看。外面黑咕隆咚,寂静无声。
好久,竹罩上的蒸腾的水汽慢慢淡下去,衣裤干起来了。
其实,春梅一看到这男人,她就惊惧了。那时候的篓底,家家户户穷啊,没啥东西供人偷,这妖孽一样钻进屋里来的,多半是偷人。春梅紧紧张张地说:“烘干了。”
男人终于说:“我看上你很久了。”说着就走过去抱春梅。
春梅说:“不行,我有丈夫的。”
男人说:“我看见阿根在你跟前老粘着转不开身,我看见东村头癞子阿大还抱你啃嘴,连老光棍都可以捏你的手,我怎就不行?”
春梅心想,今天真是遇到头“毒”了,但还是强硬地说不行。
男人过来拖春梅,春梅张口就咬。被男人推开后,春梅大声呼叫,但只发出一个声就闭了口,因为男人已经将大手火钳般地叉向桌上孩子的头颈。
这一晚,篓底村最南边的这间屋子里,一定闹出一些不祥的响声,只是山深雾重,这屋子成了孤岛。
后来呢?后来,春梅的姨婆从此闭门不食,天日不见,因为她就是那个恶人的妈,恶人是春梅的表阿叔来春。来春平时寡言,不扎闹猛,却窥觑春梅好久,或许因为和春梅的辈分关系,或许是心性的自卑和猥琐,或许受阻于春梅的防范,迟迟不敢对春梅下手。他嫉恨阿根老往春梅家走动,人背后多次暗示长婆媳妇春梅勾引阿根,挑拨长婆媳妇的醋意。他怀疑光棍阿堂找春梅缝补怀有歹意,跟在阿堂身后隔着春梅家的毛墙偷听,果然见阿堂耍赖,恨恨地在门前砸了一只破罐。在疏疏密密的竹园里,他偷看春梅趟笋,联想着春梅无比曼妙的身姿,意外发现癞子阿大调戏春梅,忍不住“喝”出了声……他无法容忍别人染指春梅,但看到的景况又促使他迫不及待。他渴望着春梅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又不敢正视春梅的目光,经常远远地看春梅做针线,故意绕着道走过春梅屋的门口,有时候见春梅在前头走,悄悄跟一阵也是好的。他被那种相思的煎熬折磨了好久,终于在宝银出脚力的时候,终于这天春梅没有早早地关门落栓,见春梅抱着孩子到姆妈屋里还针线的当儿,溜出家门折到村南头,解开了春梅屋的门搭襻。当春梅疑惑重重地进门后,躲在里半间的来春等着春梅关门,不料春梅点亮油灯就抱着孩子转身离去,稍后就等来了长寿小伯率领的那伙男人,夺门而出已经晚了,情急之中,他随手择根麦秆委身躲进了水缸。
那时政府的审判程序明快,来春被法办后不久,姨婆悄然死去,村人收敛了她的尸体。
这个结局,老长一段时间在我脑子里挥散不去,总觉得心里搁着什么,甚至连晚上做梦都做到我在一大群蓝色的羊里面找来找去,找一只背上有一块三角形白毛的羊。可当我无限接近这只羊的时候,发现它就在我眼前遁了去……
春梅的故事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是一笔悲凉的记忆,也是奶奶指导我生活的教科书。我以为我已经长大,我以为往事都云烟散尽,却不料在奶奶过世以后,奶奶依旧给我留下了一个重重的记号。我奶奶是我们村至今为止活得最长寿的人,她是2014年春上去世的,享年98岁,被称为喜丧。当奶奶的丧葬尘埃落定,我们家族的亲人又将各奔东西,这时,大伯取出一个暗红色的帕布摊在桌子上,说是奶奶留给孙辈的一点纪念。大伯拎起三串红丝线穿着的铜钱,对我两个堂兄和弟弟说“这是给三个孙子的,每串五枚,收好。”然后对我说:“诺,这是给孙女的。”
奶奶留给我的,是一把浑身乌黑、红线缠着双环的女红小剪刀。
发稿编辑/姬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