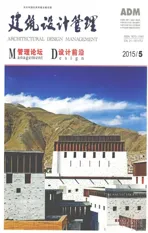建筑的情结
2015-12-25
建筑的情结
“结”,意为情结)

张宝贵:祁总设计的208所,外墙板本来是混凝土肋结构,后来考虑肋结构的板子比较厚比较重,南口是北京的风口,冬天风很大,吊在顶子上又是室外恐怕不安全,就改成钢架结构了。甲方领导知道以后跟公司业务说,你们太为我们着想了,合同已签了,技术交底也有了,再改怕影响你们的效益,没想到你们主动改了。那时公司已经做了四五百平方米,造价好像有二三十万。
祁斌:是的,那个项目的合作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经历了很多戏剧性的故事,过程也拖了很长时间。当时张总很忙,好像是在忙一个革命博物馆的项目,起初根本就来不及。好在项目业主在施工过程中逐渐回归理性,将一个献礼工程回到了正常的周期,正好赶上了张总的档期,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张宝贵:是这样,做208所墙板的时候,正在为湖北一个革命博物馆做样板,设计院来了好多次,前前后后近两年的时间吧,做了不少样板,不过最后流标了。我们知道这个活动100周年很重要,那个设计挺奇特的,我们组织很多人,把功夫都用在研发上了。我们做的板多大呢?像一面墙这么大,而且做了十几块。摆在现场很气派,我们和很多建筑师完成了不少挂板项目,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肯定中标,我们也沾沾自喜,以为板上钉钉。开标的时候建筑师说张先生做的东西不是我要的,这一句话我们技术标是零。那几年,没人做墙板,也就没有竞争,我们虽然难,多是技术和报价上,这种困难对我们来说容易克服,没想到这个项目在运作上走了麦城。市场其实挺复杂的,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祁斌:好像每次见到您,都会听到您又在墙板的技术上有了新突破,或者有什么新纪录诞生了,问个简单的问题,您现在做过的最大、技术最复杂的板有多大?
张宝贵:已经做过的应该是九米长,一米五宽,还可以大,只是运输中不是超高就是超宽,当然还有费用问题。做大板和薄板不是脑子一热想出来的,2001年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国际GRC年会,在爱尔兰看过许多工程,很多都是大板,宽和长是一比四的关系,最大的板二十多米长,背后是一个双层的钢架,从那天开始,我对大板产生了兴趣。大家都明白,做大板安装效率特别高,尤其是效果和以前的板不一样,建筑师的想法会活跃起来,多少年过去,果然如此。带着模糊的想法,开始试验摸索,用了近八年的时间吧。崔愷、崔彤最早在工程中用,然后又出现了U型板、L型板、曲面板或双曲面板。国外的墙板一般不过分追求表面效果,他们的条绒状墙板,橡胶模一翻就可以了,不剔凿,人工费太昂贵了。我们做的板表面都去剔凿,可以出现石材质感,建筑师喜欢,并由此产生了很多新想法。剔凿的过程可能对板材造成内伤,避免内伤怎么办呢?就在板材内部加了耐碱玻璃纤维,剔凿中纤维可以把应力释放,避免了内伤。现在很多企业也模仿着做墙板,要么不剔凿,没有石材的质感。要么剔凿没有保护性工艺,过一两年裂了,比如说东部城市一个什么码头做了不少的板。那天兴刚见我说,张先生那东西是不是你们做的?我说怎么了?为什么裂了变型了,我想可能是工艺处理上有薄弱的地方,又是巨大的板,加上结构应力变形。阻裂要通过一整套完整的工艺来保证,喷射纤维增强抗冲击能力,底层加网格纤维或纤维毡子,以增强抗弯能力,当然这些纤维的含锆量在16以上,否则不耐久。再有就是制品要做薄,比如一两公分,越薄越合理,关键是纤维加得要充分,不能少于水泥量的百分之三,最好争取百分之五。像老年间的旱伞,一层桐油,一层道林纸,反复开合,但是它不会轻易破损,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柔韧体。还有老年间的打袼褙,一层布一层糨子,柔中硬。我们现在盲目强调钢性,钢筋混凝土很结实,一旦遇到地震,作为钢性物质宁碎不弯,成为制造灾难的潜在因素。长期以来把桥梁的制造技术全面搬到墙板上是一个误导,因为前者有功能要求,后者只管装饰,从铠甲式混凝土转到丝绸式混凝土是有必要的,这不但有利于安全,有利于降低造价,还有利于节能减排。
祁斌:其实我很早就对张先生及他的宝贵石艺有些知闻,因为经常在建筑师的论坛、聚会活动里看到张先生的影子,而且经常被张先生的发言所吸引。印象中,他是个很善于演讲的人,更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的一些观点,无论技术上还是设计理念上,都很独到,发人思考。
众所周知,张先生是国内最早在建筑中运用装饰混凝土的人之一,在这方面,他应该是位开拓者,他独特、开创性地运用给了混凝土这种最普通材料以更生动的表现力。建筑师能够通过他的材料,表现出更丰富的建筑语言。
其实在我印象中,张先生留给我更深刻的,在于他不同寻常的思想能力,他对很多问题独特而富有见地的思考,经常能给予听者很多启发。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我想他之所以能够实现“宝贵的25年”——25年间深受大家的认可和赞许,并且在这个行业里不断推陈出新,源于张先生独立的思想能力。他总是能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做事求得弄清事情的本质,这是他创新的源泉,也是不断进步的源泉。
我认为张先生还有一点也很“宝贵”——他做事有一种非常执著的精神,非常投入,将每个项目都当作自己的作品,从不随意,更不会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把每个项目当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事业来完成。一旦进入工作的状态,几乎不为困难所动,张先生会用一种全神贯注的精神,投入最大的精力来完成一件作品,这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状态。
张宝贵:每个建筑师关注问题都不一样,祁总不但关注产品,也关注人,他说我为了项目全神贯注,有时候拉都拉不住。我知道建筑师关心的东西和商业关心的不一样,两种关心角度会培育两种态度,我们喜欢研发,效益一直不好,只是工程效果让建筑师满意,这也能让我们有所寄托。祁总从建筑学角度关注我们,对我们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鼓励,其实也说明好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建筑师和其他的专家不一样,他有人文的东西,他关心人的内心世界,而且很会表达。
祁斌: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我们合作的208所。这个项目基地所处的是一片空旷的旷野,建筑主题又是一个军事题材,项目本身带有很特殊的环境背景。在考虑建筑外装饰材料时,我想到了张先生的装饰混凝土。那种粗糙、质朴,还有些人文内涵的混凝土能够表达出跟项目所处环境十分契合的质感和肌理,这种冲突中的协调性是贯穿整个设计追寻的灵魂。在那个环境中,过于表皮化的材料——无论是加工过的石材、金属板,都无法满足环境的尺度肌理。于是我找到了张先生。但是很不巧,您当时很投入地做着另一个项目,当听到工程进度要求之后,言明抱歉并且明确告之无法腾出档期。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因此而和业主沟通时,他们反而被感动了,认为您是个负责任的企业家,您的企业是个负责任的企业,不会为了追求利润而一味承接项目。为此,业主特意调整工期计划,赶上了您的档期,这是一种很难得的相互信任。
与您的接触使我能够感受到建筑师与您在工作态度上的契合感。建筑师在每个项目上都在寻求突破,创新突破往往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建筑空间层面,这是解决建筑的基本功能,也是建筑给人的整体空间感受,贯彻着建筑内外的逻辑性;第二个创新突破点往往来自新材料的运用。您在建筑材料、质感,尤其是表皮质感上给了建筑师一种能够充分展示建筑性格的与众不同的方式,让建筑师的理想有了更多的展现手段。建筑师与您的创作融为一体,成就了很多精彩的作品。
在这个方面我其实一直想跟张先生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您不是建筑师,是个企业家,面临的首先问题是要支撑起一个企业,让企业能够生存。但同时又十分真切地感觉到您与一般企业人的不同,您似乎非常喜爱建筑,喜爱到能让我感受到您全情投入而陶醉其中的工作状态,这种喜爱与沉醉完全不亚于建筑师。似乎您对建筑有种特殊的情结,正是这种情结让您不遗余力地全情投入去完成一个个作品,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做产品。

张宝贵:祁总提到建筑情结,我不一定答得准。往远了说,八十年代我舅舅曾任北京建材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现在北京建材研究院的前身。八十年代知青开始返城,我舅舅觉得新型建材很有希望,让我办了停薪留职,我带着老婆孩子由山西石英制品厂到了北京郊区一个叫奤夿屯的村子里。1987年7月31日晚上,一辆卡车,把我们一家四口拉到村里,住进了一个很老的房子,屋里的地是土地,没有一块砖,顶棚冬天刮大风三四尺的抖动,窗户是纸糊的,有一块巴掌大的玻璃。屋里有个小炉子,冬天外面有多冷,屋里就有多冷,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起。我跟我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在几块木板上睡觉,白天是办公桌,晚上就是我们的床,底下是几根钢筋棍,好在奤夿屯收留了我们。我老婆在院子里养鸡、种菜,还给我们一家四口做鞋、做衣服。大家问苦吗?没觉得,周围老百姓都这样,我们又插过队。我们一家四口有空就下棋、打扑克牌,在院子里打乒乓球,附近的街坊也来看我们,有的大娘还送好吃的,我们开始了这样的生活。
我晚上点煤油灯画图,白天到北京城里跑业务,经常忙了一天,很晚了没有吃饭,找个饭馆买一张大烙饼,一碗鸡蛋汤。我父母都去世了,我像个流浪狗,无家可归。有一次半夜十二点了,没有回昌平的末班车了,敲兄弟家的门不合适了,坐车到北京火车站,在那儿待了一宿,天亮了,五点半,坐上头班车回昌平,一块三毛五吧。我们最初搞的水泥制品,起了好听的名字,叫“石花”,现在有的老人还叫我们“石花厂”。当时我不懂得灰砂比、水灰比,我舅舅告诉我观察水灰比有个土办法,就是把配好的料用手去攥,出汤了就是水大了,一松手散了就是水少了。我舅舅介绍我认识了国家建材局科技处的处长,叫陈燕,陈燕把我介绍给曹永康,曹永康是中国建材研究院的院长,到今年我们有二十四年的交情了,曹院长又介绍我认识了若干个建材系统的领导和专家,每当有建材的会就叫上我,1989年首届装饰混凝土研讨会在北京管庄召开,曹院长让我做大会发言。我舅舅又介绍我认识了北京建委的陈增泰,陈增泰是北京建委科技处处长,陈增泰介绍我认识了方展和,方展和又介绍我认识了很多高级建筑师,比如费林、王昌宁、吴观张等等,把这些人介绍完了,他也走了,走得很突然。那时候再造石装饰制品还没有模样儿,在那个时期,改革开放了嘛,想干什么都行,我一个初中生,硬是在材料、艺术、建筑的边缘上转来转去,没想到把三个看似不相干的东西靠到了一起,而且越来越近,相互渗透,产生了效果,用曹永康的话说叫做“三边现象”,其实最初云里雾里,一切顺其自然吧。祁斌:这些都是个人的喜爱和奋斗,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办这样一所工厂来成就您的个人梦想的?


张宝贵:这个项目是1987年开始研究,1993年注册的私营企业。1987年到1990年之间三年我是给村里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奤夿屯收留了我,我所有的创作离不开他们,很多人帮我活灰、钉木板、搞震捣,还帮我到北京图书馆办展览,他们人背肩扛,把混凝土雕塑放到展馆,然后他们就回村儿了。我出名了,只有回到村里我才觉得到家了。1993年,张镈老先生80岁了,单老也80了,到昌平来,看到水泥的小雕塑,单老说:“张厂长,你多给我一个行不行,我太喜欢了”。听到单老这话我不知说什么好,他拿拐棍敲打着我那些“长城砖”,跟我唠家常。张老喜欢、单老也喜欢,还有马旭初马老。那砖怎么出现的呢?单士元、张镈告诉我这叫“金砖”,主要来自苏州,老年间制砖之前要把土的性晒没了,然后澄浆,做完砖以后还要刷桐油。只要建筑师有需要我就做,不想别的。建筑师用专业领着我往前走,一代又一代的。
祁斌:是啊,建筑师没少给您出难题。
张宝贵:是难题,不过也是课题。我没有上过建筑学,通过工程让我知道一些技术和原理。最开始那会儿,他们去工地也叫上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没盖好的房子里很黑,到处是渣土和钢管,弄不好会碰头或摔倒。然后他们又开会,和甲方、施工方讨论好多事情,没完没了的洽商,只要没交工使用就老有变化,老有新想法,看得出来大家很把建筑师当回事,哪怕毕业没多久的,我慢慢地知道了建筑师的价值。中午吃饭他们也叫上我,不论是盒饭还是桌餐。快完事了,才会想起我,“对了,那个浮雕厂家来人了,大家说说吧。”他们一开头,我就好办了,也试着说技术,说想法,大家开始注意我,我慢慢的懂得了一些建筑常识,什么立面啊,平面啊。我作为一个乡下人,和农民用水泥做了一些不成样子的东西,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小看我们,心里暖暖的。
崔愷的设计,以前都是写一种材料的名字,什么GRC,什么装饰混凝土。现在干脆就是“宝贵石艺”。崔愷告诉我,有了工程你一定要让利,不然会出局,我画了半天图就白画了。
祁斌:当然,这是建筑师的职业精神,是每个项目中必须关注的问题。
张宝贵:说个跑题的事啊,我每年清明回老家蓟县上坟,我就把这些画册烧了,我去磕头。什么意思?我就希望我的父母能知道我在好好活着,小时候,他们告诉我不管怎么样要当个好人,我知道当能人容易,当好人太难了。但我在努力,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我一直把建筑师的事儿当做自己的,不讲条件,时间久了,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有事儿就想到了我,我们做起事情来很简单。
祁斌: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参与了吴良镛先生主持的孔子研究院项目。在那个项目里,吴先生曾用您的石艺做装饰雕塑,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有您这样一位建筑雕塑家——“宝贵做雕塑”,与建筑有着交集。后来在首都规划展上,我又经常看到张先生的身影,当时觉得有些奇怪,一个雕塑家为什么会出现在规划建筑展上——那可是一个纯粹建筑圈子里人们的活动。参观宝贵的展览,看到很多您设计制作的精美的室内装饰品让我有了个概念——“宝贵做建筑装饰雕塑”。以后逐渐发现宝贵的产品更多地与很多建筑作品结合在了一起,十分独特的效果让我着实对您的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我知道“宝贵做建筑”。这些年更多地在一些建筑研讨会上遇到您,您对建筑、建筑文化的真知灼见让我领会到“宝贵在思考建筑”。
早年我在日本看到一些建筑混凝土外墙板项目实例,确实印象深刻,不但外墙板尺度巨大,而且加工工艺成熟精湛,各种表面质感运用丰富。国内在这方面应用还刚开始,不但工艺稚嫩,制作者也是寥寥无几,而张先生就是这寥寥无几的其中之一。张先生的材料不光是在尺度上有所改进,在工艺上也在做着改变。最重要的是材料肌理上的表现,不难看出您在研究材质肌理的表现力上下了很大的工夫。这或许就是您以及您的材料不断转变、发展的动力吧。原先我认为张先生是一个艺术家,在做艺术的东西。后来发现您的事业正在跟建筑融合,到如今您已成为引领这个领域发展的一个风向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您从做雕塑转化到做建筑的外墙板,这个过程中把握雕塑性的建筑语言与建筑性的建筑语言是很大的挑战,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正如一句俗语所说:隔行如隔山,有时候迈过这座“山”的确需要巨大的蝉变。有很多艺术家,他们在艺术领域做得非常好,但是希望将艺术与建筑结合的时候就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契合点,而我恰恰在张先生的宝贵石艺上看到了例外。
张宝贵:祁总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情结,第二个问题关于转化。大家知道我是从材料起步,做阳台栏板的时候我舅舅告诉我做成蘑菇石,我当时不懂蘑菇石,以为是蘑菇样的石头,后来才知道是石头劈出来的疙里疙瘩的效果。当初搞再造石,不知道翻模的程序,最初用什么呢?没用硅胶,硅胶是最好的,但是很贵,用不起。后来建工研究所赵孟彬告诉我有一种防水涂料,叫聚氨酯,黑糊糊的,像沥青,有弹性,很便宜。我们到了西郊一个防水材料厂找到了这种东西,是甲乙双组分,一个黑、一个黄,按比例配,倒在一个大塑料盆里,几个人一个大棍子轮流搅和,那可真是个力气活儿,搅匀了,倒在石膏浮雕上,用这种胶模翻制了“松鹤延年”“喜鹊登梅”。建筑师看了都不喜欢,说太俗了,不像石头。后来我做了一个牛头,抽象的,聚苯板直接做阴模,这个造型很概括、毛毛茸茸,有现代感,他们喜欢了。从那儿以后,一直在寻找现代感和石材的质感。每次从昌平进城,办完事情,唯一的去处就是书店,经常到西单、西四、王府井、美术馆去买书,花光身上的钱,买了很多书,什么装饰图案的、雕塑的、建筑的、材料的、还有宗教的、哲学的,我不求甚解,只求一瞬间。
1989年1月23日在北京图书馆搞了一次再造石装饰制品展,200件作品都是模仿的,有书上的,有他人的,也有装饰画上演变来的,那时候三四个农村妇女帮我把这些雕塑从昌平运到位于白石桥的图书馆。各方面来了很多人,还有一些著名艺术家也去了,比如郑于鹤、何镇强等,我很兴奋,一再告诉大家展现的是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水泥做的雕塑,认为很有艺术效果,从那以后我才明白原来这也叫艺术。那个时候找我的建筑师都是由于雕塑,包括崔愷的丰泽园饭庄。2002年周庆林带安德鲁找到了我,让我们做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吊顶,从那以后又回到了建材这儿,特别是2004年朋友聚会,清华陆志成让我研究墙板,我就彻底的回到了建材界,很多人说,张宝贵不搞雕塑了,又干建材了,这种转化并非设计,还是和生存有关,和大家的呼唤有关系。
我出于建材又归于建材,在雕塑上兜了个圈儿又回来了。我没有师承和名分,虽然北京市给我授予了“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其实我的艺术在民间、在市场,没有包袱也就随意许多。
为孔子研究院做的凤形雕塑,是从建筑上的螭吻演变来的,螭吻通常出现在建筑屋脊的两端,呈鱼龙的形状,这样设计据说为了防火。凤形雕塑的凤尾前移,呈弧状,饱满的,像张工搭箭的弓背,表现一种张力。凤尾之间拉开了缝,通透增加了灵动感。正面看这个雕塑,有佛龛的感觉,有王冠的感觉。雕塑上的线都是S型,相互有联系。吴先生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远古的时候人们做造像,往往佛像脚底下也有纹样,一立起来看不见了,为什么还做出来呢?是雕塑者的虔诚。他的意思是要做一个完整的雕塑,要把凤爪表现出来,我用线刻的方式做了简单的勾勒,注意时会发现,但是不彰显它的存在,大家说,凤型雕塑成了孔子研究院建筑中有灵性的一个部分。
祁斌:我也有同感,从这个建筑语言到建筑材料,最终提升到建筑,张先生的宝贵石材不仅是建筑功能化或装饰化的语言,同时还有一种提升建筑的精神在里面。
品赏一个建筑有几个层次:首先建筑要好用,第二要可赏可看,也就是常说的好看,真正上品的建筑应该是能够感动你的,就是“可感”,这种建筑可遇不可求,不但赏心悦目,还感动了你的内心。令人感动的建筑必定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它的空间,建筑的核心语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它的材料,建筑空间体系里的材料体系是它最重要的表现手法。
所以张先生您的这个材料语言,我认为已经跨越了简单的装饰,而上升到一种雕塑化的建筑、建筑化的雕塑的程度。
张宝贵:我觉得祁总今天这三个问题很好,第一是情结,第二是转变,第三讲到了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可用、可赏、可看这三个“可”很有新意。最后一个问题很有必要,我在考虑研究第二代产品就是“六合一”,第三代产品是充分利用建筑垃圾做墙板,很多事情都是从想象开始的。如果能够有幸和清华合作,建议做一个课题,着眼点在地震灾区,或者是贫穷的村落。
祁斌: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就地改造,再生原有材料,不产生新的污染,也不浪费材料。
张宝贵:我常有想法,毕竟还是企业行为,如果变成产学研行为,会成为一些比较主动的东西。我和天大张颀院长讨论过天大建筑学院外墙一事,就是把废旧的墙皮铲下来,不丢弃,粉碎后变成原料,和水泥搅拌在一起,做成墙板,再挂在天大建筑学院的墙上,当然这之中还有很多技术细节。这只是个想法,不知道会怎么发展下去。我跟张颀说,从一开始搞这个东西就应该拍照拍录像,留下一些素材,或许对大学生的学习和创作有提示的作用。那么在艺术家看来,也许叫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