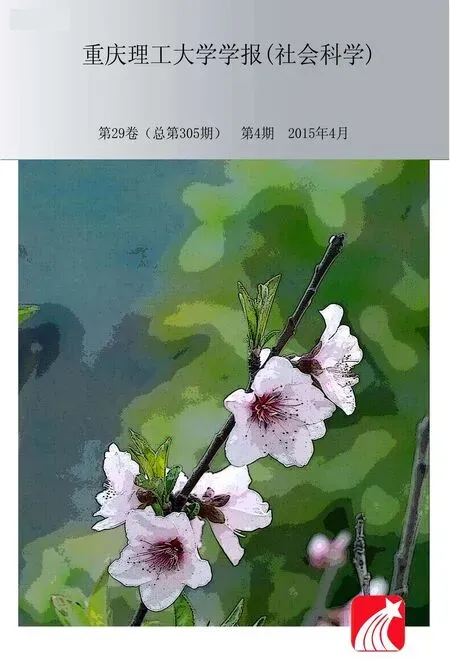从塔尔斯基转向看公理化真理论
2015-12-23李娜,李晟
引用格式:李娜,李晟.从塔尔斯基转向看公理化真理论[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4):4-9.
Citation format:LI Na,LI Sheng.On Axiomatic Theories of Truth from View of Tarskian Turn[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4):4-9.
主持人语:
中国逻辑学会会长邹崇理 研究员
从实质真理论研究到公理化真理论研究,是当前逻辑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尽管在各自的研究中,两种真理论都还存在理论缺陷,但认识这种理论缺陷,却是当前真理论研究的转型以及强化公理化真理论研究的必然途径。《从塔尔斯基转向看公理化真理论》一文从追根溯源入手,一步步地详细阐述论证了这个必然途径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能够深化对逻辑哲学中真理论问题讨论的理解。
关于意义问题的探讨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对于意义问题的研究涉及了众多的领域,如哲学、逻辑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等。因此,意义问题也就一直是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很多哲学家、逻辑学家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义理论,但似乎又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困境与诘难。国外对于布兰顿的研究很盛,但当前国内对于布兰顿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本期发表的《意义的推理路径选择》就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之一。对于正确理解布兰顿的语言实用主义和非形式逻辑的实用价值,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塔尔斯基转向看公理化真理论
李娜,李晟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塔尔斯基的语义真理论是逻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带来了真理论研究的塔尔斯基转向:在研究基础上,发生了从本体论或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在研究动力上,发生了从揭示真之本质到克服语义悖论的转向;在研究主题上,发生了从研究真之本质到研究真之规律的转向;在研究进路上,发生了从下定义到公理化的转向。公理化真理论是在塔尔斯基转向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真理论。理解塔尔斯基转向是理解公理化真理论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塔尔斯基转向;公理化真理论;真之本质;真之规律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5.04.002
中图分类号:B81
文章编号:1674-8425(2015)04-0004-06
On Axiomatic Theories of Truth from View of Tarskian Turn
LI Na, LI Sh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Tarski’s theory of truth is the first complet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 in the history of logic. It has radically chang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for theories of truth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theories of truth after Tarski’s have turned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from ontology or epistemology to linguistics, turned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from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truth to overcoming the semantical paradoxes, turned the research target from the essence of truth to the laws of truth and turned the research approach from definition to axiomatization. Axiomatic theories of truth, a class of new kind theories of truth, are occurring and develop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arskian turn. Understanding this turn is the key for understanding axiomatic theories of truth.
Key words: Tarskian turn; axiomatic theory of truth; essence of truth; law of truth
一、变革:真理论的塔尔斯基转向
塔尔斯基转向(Tarskian turn)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是由当代英国学者霍斯顿(Leon Horsten)在《塔尔斯基转向:紧缩论与公理化真》[1]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的。霍斯顿认为,真理论的主题自塔尔斯基开始,逐渐发生了从研究“什么是真”或“什么是真之本质”,到研究“如何使用真”“真有什么规律”,以及“如何描述真之规律”等问题的转向[1]15-16。一句话,真理论从研究真之本质转向了研究真之规律。笔者认为,霍斯顿抓住了塔尔斯基转向的关键,但是并不全面。弄清塔尔斯基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理解公理化真理论的一把钥匙。
塔尔斯基在其著名论文《形式化语言中的真概念》[2]中,建立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语义真理论。后来经过哈克、达米特和戴维森等人的发展,语义真理论对20世纪中后期的哲学和逻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这篇论文一直被看作是逻辑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相比以往的真理论,塔尔斯基真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以下3个方面:
第一,以语言为立足点。塔尔斯基在文章的开篇写道:“本文的全部几乎是致力于同一个问题——真之定义。其任务是针对一种给定的语言,为真语句这个词建立一个实质上恰当且形式上正确的定义。”[2]152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塔尔斯基已经注意到语言是真之定义的前提,真和语言是紧密相连的。同一个语句在一种语言中可能是真的,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可能是假的,或无意义的。这与塔尔斯基之前的真理论在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基础上讨论真之定义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以规律为着眼点。虽然塔尔斯基用“满足”定义了“真”,但他的定义是一种关于语句结构复杂度的递归定义,并不是传统的“属加种差”定义。递归定义所依赖的是真概念的组合性,实际上刻画的是真与逻辑联结词和量词的关系,并不是着眼于真之本质,而是基于逻辑规则的真之规律。正如戴维森所说:“我们对真这个概念的一般特征仍然缺少一种令人满意的说明,而我们在塔尔斯基的工作中并不能发现这种说明。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向塔尔斯基学习许多东西。”[3]32这些缺少的“说明”就是真之本质,而可以学习的“东西”正是真之规律。
第三,以悖论为切入点。塔尔斯基认为,真之定义应满足两个条件:实质充分和形式恰当。实质充分是目标,形式恰当是保证。在塔尔斯基看来,一种令人满意的真理论不能导致语义悖论。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分层思想,通过禁止同层次真谓词的自由迭代而避免了悖论的产生。塔尔斯基此举可谓切中要害,因为面对繁多的真之规律,悖论是最好的突破口。这是一种“反推”的方式,从悖论产生的条件出发,反推出人们所要遵循的真之规律。
以上3点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以语言为基础,也就是要以语句为真之载体,那么说谎者语句就不可不讨论;而一种令人满意的真理论必须是自身无矛盾的,所以避免说谎者悖论及其各种变体就是最起码的前提,那么无悖论地使用真概念需要遵循哪些规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问题;而使用真概念不可能脱离语言,所以又要以语言为基础。这三者共同构成一个首尾相接的“环”。
应该说,如此特征的语义真理论的确是塔尔斯基首创,但未必只能由塔尔斯基创立。从当时的哲学大环境来看,形式语言的建立和现代逻辑的成熟,已经使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得以如火如荼地进行;罗素悖论在数学基础中被发现,也使得古老的说谎者悖论从沉寂走向了风口浪尖;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更是加速了人们对真之直观理解的反思。所以,真理论的塔尔斯基转向实际上是大势所趋。
由此,塔尔斯基转向的内容至少应包括3个方面:在真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发生了从本体论或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在研究的动力上,发生了从揭示真之本质到克服语义悖论的转向;在研究的主题上,发生了从研究真之本质到研究真之规律的转向。因此,霍斯顿所概括的只是塔尔斯基转向的一个方面。
二、突围:走出本质追问的千年困境
根据塔尔斯基转向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塔尔斯基转向之前的真理论概括为:立足于本体论或认识论,旨在为真之本质提供确切定义的真理论。这类真理论通常也称为实质真理论。实质真理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著名理论包括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等等。但直到目前为止,任何真之定义都不是毫无争议的。这是因为实质真理论也有3个特征,或者说存在3点不足:
第一,相对性。用于定义真之本质的概念或命题是基于某种特殊的理论。比如实用论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真理论,支持实用主义的人自然支持实用论,但是在反对实用主义的人看来,实用论所断定的“真”未必就是真的。然而,正如弗雷格所说:“真的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承认而是真的。”[4]207如果一种真之定义使得对真的判定结果是相对的,那么这断不是令人满意的真之定义。
第二,复杂性。真之本质往往并非一句定义所能揭示。一种实质真理论对真之定义的补充解释,事实上远远超出了定义本身的复杂程度[5]。就像融贯论虽然一般将“真”定义为信念集合中的融贯关系[6]116-119,但融贯并不是一个简单直观且毫无争议的概念。何为融贯?如何判断融贯?信念集中的元素是什么?谁的信念集?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使融贯论分成多种派别而变得复杂,而且使真概念与它在日常使用上的直观性相去甚远。
第三,模糊性。用于定义真之本质的概念或命题本身并不精确。在众多实质真理论中,符合论最合乎人们对“真”的直觉,而且千百年来也最能为不同哲学家持有或赞同。但直觉的背后却大有文章。比如亚里士多德曾说:“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7]79根据直觉,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却也无法放心地接受。什么是实?如何判断实?假与真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并没有被阐释清楚。所以,实质真理论只是看似直观,实际却很模糊。
实质真理论的上述3个特征皆与真之定义密切相关,这说明给出一个满意的真之定义确有难处。“真”这个概念在哲学中比较特别,它并不是必须借助严格的定义才能把握,而是可以通过直觉来理解,它类似于初等几何的“点”与“线”。在对“真”的直观理解的基础上,人们可以定义“必然”“可能”“有效”等一系列概念。因此从逻辑上看,除非循环定义,否则能够充当真之定义项的精确概念十分有限。但是要定义“真”,不可能不借助已有的知识和理论,那么对不同依据的选择就为真理论注入了相对性的基因;而相对则必然导致观点的分歧,即使在同种真理论内部,也会因为对定义要素的不同理解而增加真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其结果虽然可以揭露潜藏在真理论内部的模糊因素,但是对模糊的追问和澄清,却带来下一个相对性。所以实质真理论的3个特征也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环”。
我们可以将上述的这两个“环”连同塔尔斯基转向用图1来表达。

图1 3个特征的真理论的塔尔斯基转向(初步)示意
可以看到,左环所代表的真理论(以下简称“左环真理论”)是以真之定义为核心,它们坚持真之本质是真理论研究的主题。但它们被相对、复杂与模糊团团包围,且三者浑然一体,很难就一点而突破。相比之下,右环所代表的真理论(以下简称“右环真理论”)则有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悖论。如前所述,悖论是一种反推式的研究,也就是可以通过对悖论产生条件的否定而得到一些肯定的结果。例如塔尔斯基认为,真谓词的自由迭代是产生悖论的原因,所以他用语言分层限制了这种迭代,由此形成了第一个语义真理论[2]。而克里普克则认为语言分层与直觉相违背,但是为了避免语义悖论,像说谎者语句这样的句子就不能做真与假的断定,因而形成了一种允许存在“真值间隙”的语义真理论[8]。对于其他语义真理论也可做类似的验证。总之,塔尔斯基以来的真理论(即右环真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种真理论研究与悖论研究相辅相成的局面。霍斯顿在评价语义悖论时说:“语义悖论带来的是一场真理论的巨变。”[1]14
反推式研究对于真之本质来说是不适用的。因为我们所给出的真之定义必须是肯定的,也即是必须给出“真是……”而不能给出“真不是……”反推的困难就在于,从否定的说明虽然能得出一些关于“非真”是什么的结论,但始终无法确定这些“非真”是否能构成“真”的补集。所以,从“非真”是什么并不能必然推出“真”是什么。因此,对真之本质的探讨最终还是要落脚到肯定的定义,那么它就又将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而更重要的是,无论给出什么样的真之本质的定义,像说谎者悖论这样的语义悖论依旧会出现。所以,左环真理论若想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走出本质追问的千年困境。
三、破局:公理化进路的可能与提出
现在的问题是:真之定义是否能成为右环真理论的核心?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真之定义除了预设真之可定义性以及面临无穷倒退的困境外[9]118-119,至少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容易使人误认为右环真理论也是以真之本质为研究主题。这种误会通常见于对塔尔斯基真理论是否是符合论的争论。笔者认为,尽管塔尔斯基的“T模式”可以体现符合论的一些特点,但是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两种真理论的研究主题事实上完全不同,所以不可同日而语。霍斯顿也注意到,塔尔斯基真理论的真正用意是想指出无悖论使用真概念的条件,但可惜的是这一用意被定义之名遮蔽[1]20。第二,容易使人误认为右环真理论研究了与左环真理论不同的真概念。这种误会常见于对“truth”的译法分歧。王路教授曾精彩地讨论过这种分歧产生的根源,并且澄清了关于逻辑学家研究“真”而哲学家研究“真理”的误解[10]。笔者认为,塔尔斯基转向为该分歧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我们之所以习惯于把哲学家研究的“truth”称为“真理”,主要是因为这些真理论立足于揭示真之本质;而之所以发现逻辑学家研究的“truth”有别于“真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探讨的是基于逻辑规则的真之规律。所以,二者的区别不是真概念本身的不同,而是同一真概念的不同研究视角。
鉴于上述问题与不足,如果我们只是想借“定义”来规定一组无悖论的初始真之规律,并且不需要对真之本质进行充分的说明,那么我们也就没必要非冠之以定义之名不可,完全可以把“真”当作一个初始概念。按照戴维森的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定义’这个词与谓词是初始的东西这个思想不协调,我们可以抛弃这个词,这不会改变这个系统。但是为了允许承认语义谓词是初始的东西,我们可以放弃那对于塔尔斯基来说把递归说明变为明确定义的最后一步,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结果看作是关于真的公理化理论。”[3]33
关于公理化真理论,塔尔斯基本人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条可能的进路[11],但他对此存有疑虑。他认为无论怎样选择公理都难以避免“随意性”和“偶然性”,况且只有明确的定义才能保证所形成的理论不会出现语义悖论[12]。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这些疑虑,才使得塔尔斯基坚持要为“真”下定义。但戴维森对此指出,如果我们把公理限制在说明“满足”所需要的递归条款上,随意性和偶然性就能被克服;而且只要不采用已知会导致悖论的方法,就能避免语义悖论[3]33。
那么,真之公理化是否能成为右环真理论的核心呢?
四、建瓴:公理化真理论的特征与成就
公理化真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非承接自戴维森的建议,而是发生于数学家对算术不完全性的反思。其基本做法是把“真”处理成一个初始谓词,直接添加到一种基础理论(base theory)的语言中,并以若干刻画真概念基本事实的语句作为公理,对基础理论进行扩充,从而得到公理化真理论。一般说来,公理化真理论是以弗里德曼(Harvey Friedman)和希尔德(Michael Sheard)的论文《自指真的公理化方法》[13]为开端的。此后费菲曼(Solomon Feferman)在《反思不完全性》[14]一文中继续贯彻了公理化的进路,并最终促成了公理化真理论的勃兴,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真理论,主要包括四大理论:DT、CT、FS、KF[15]91。
第一,公理化真理论是一类以语言为基础的真理论。公理化真理论把“真”处理成谓词T,这就需要借助语言,而基础理论恰好能满足这一需求。比如,通常以皮亚诺算术PA作为基础理论,那么T谓词就被添加到PA的语言LPA中,从而得到新的语言LT。哥德尔编码技术使得LPA和LT的任意语句φ都能获得一个唯一确定的编码┌φ┐。T谓词作用于并且只能作用于这些语句编码,这就说明公理化真理论是把语句作为真之载体。根据语言的不同,如果T谓词只能作用于LPA的语句编码,那么所形成的公理化真理论就是类型的(typed);如果允许T谓词作用于LT的语句编码,那么这样的公理化真理论就是无类型的(type-free)。对于语句“0等于0是真的”(即:T┌0=0┐),它在无类型公理化真理论中就可以证明为真(即:T┌T┌0=0┐┐),而在类型公理化真理论中却是无意义的。所以,语言是公理化真理论的基础。
第二,公理化真理论是一类能克服说谎者悖论的真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说谎者悖论及其各种变体不仅是公理化真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公理化真理论自身演进的动力。虽然说谎者悖论是一种语义悖论,而公理化真理论是一类语形真理论,但是对角线引理[16]221使得说谎者语句λ可以在LT中获得一种特殊的语形表达:﹁T┌λ┐。这就使公理化真理论具备了讨论说谎者语句的能力。很显然,λ在所有的类型理论中都是无意义的,因而类型理论不会导致说谎者悖论。不同的无类型理论对λ的处理方式虽有所不同,但说谎者悖论也都能适当避免。比如,在FS中,λ和﹁λ都是不可证的;而在KF中,λ是无法做真假判定的。
第三,公理化真理论是一类旗帜鲜明的以真之规律为对象的真理论,这是公理化真理论区别于以往一切真理论的最显著特征。如前分析,左环真理论不研究真之规律;以塔尔斯基理论为代表的语义真理论虽然研究真之规律,但因为执着于下定义的进路而难免遭受误解。公理化真理论则完全不同。在论文《自指真的公理化方法》中,弗里德曼和希尔德明确提出,他们要在哲学上保持中立,不去讨论真之直观理解(即真之规律)的哲学意义与合理性,只考察哪些真之直观理解的集合可以相容,而哪些不可以;并且二人明确提出了要采取公理化的方法[13]2。此后的发展只是进一步确定并完善了公理化进路的基本框架。
以上分析表明,公理化真理论完全具备塔尔斯基真理论的所有3个特征,因而也属于右环真理论。公理化真理论和语义真理论的紧密关系体现在,真之公理的选取是基于语义真理论的真之递归定义。这说明公理化真理论和语义真理论只是在研究的进路上有差别,但这使得前者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后者。
真之紧缩论是右环真理论的天然盟友,它主张“真”是一个非实质的概念,不会为人类知识增加新的内容[9]121。语义真理论虽能利用紧缩论作为自己的方法论依据,却难以就实质与非实质的问题为紧缩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公理化真理论则不然,它们通过把保守性作为另一个核心问题而推动了紧缩论的新发展。所谓保守性是指,当T谓词及其公理被添加到PA后,所得到的真理论在算术上应与PA等价。如果满足保守性,则说明“真”是一个非实质的概念,从而支持了紧缩论的观点;但如果不保守,则说明“真”有实质内容,这对紧缩论就构成了一种挑战。尽管事实证明在4种主要的公理化真理论中,除DT外,CT、FS、KF都是不保守的,但这促使了紧缩论者对保守性问题作出反思[9]122-123。语义真理论没有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建立语义真理论的目标只是为克服语义悖论。而公理化真理论则是在此基础上,把真理论本身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利用已知的证明论技术充分地讨论其元性质。所以,公理化真理论比语义真理论走得更远。斯特恩(Johannes Stern)在系列论文《模态性与公理化真理论》[17-18]中,以FS和KF为基础,分别建立了不弱于标准模态算子逻辑S5的模态理论。这不但说明了公理化真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且彰显了“真”作为基本哲学概念的理论地位[15]94。这些成就更是语义真理论望尘莫及的。
所以笔者认为,公理化真理论是右环真理论的最杰出代表,而右环真理论的核心则应该是真之公理化。因此,塔尔斯基转向就应该包含第4个内容:在研究的进路上,发生了从下定义到公理化的转向。所以,此前有论文把真理论的进路转向看作是真理论的转向[9],实际上还是一种片面的认识。现在,让我们把塔尔斯基转向的4个内容正式地用图2来表达。

图2 4个特征的真理论的塔尔斯基转向(完整)示意
客观地说,当前的公理化真理论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首先,当前的公理化真理论是以LPA为基本的形式语言,而LPA是一种表达力十分有限的语言,这就使得公理化真理论所得到的结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尽管藤本(Kentaro Fujimoto)在论文《集合论中的类与真》[19]中,将基础理论推广到了集合论,扩大了公理化真理论的语言,但集合论的语言表达力相比自然语言仍然差距很大,不可能实现哲学家弄清自然语言真概念的最终愿望。其次,当前的公理化真理论具有浓烈的数学色彩。虽然它们在数学强度方面证明了十分严谨而漂亮的结论,但是正如霍斯顿在介绍PA的功能时所强调的,PA仅仅是一种用于讨论句法和进行句法推理的工具[1]23。选择PA只不过因为它简洁且为人们熟知,并非是由于自然数与真理论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倘若是以某种非数学的句法理论作为基础,那么数学强度就不再是真理论所必须要探讨的。所以笔者认为,当前的公理化真理论只是真之公理化进程中的一种具体形态,并不是唯一形态。
五、细节:通往更广义的公理化真理论
对于当前的公理化真理论的上述第一个缺点,笔者认为,这在真之公理化进程的初期是无可厚非的。一方面,自然语言的丰富性使得其中必然包含与真理论毫不相关的复杂内容,当自然语言的分析工具尚未完全发达时,这些无关内容的存在势必会增加真理论研究的难度,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另一方面,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使得我们难免会在排除无关内容的同时,在一个并不严格的环境中将有助于真理论研究的重要结构人为地忽视。如果改用经过精心设计的形式语言,这一切就都可以避免。当然,LPA在形式语言中确实只是个“小语种”,但它却是在更具表达力的语言中进一步弄清真概念的必要前提。
对于第二个缺点,这不得不归因于眼下从事公理化真理论研究的学者大多是数学家,所以他们提出和回答的问题都紧密地围绕着数学,总体缺乏系统的哲学反思和评价。数学家对真理论感兴趣,主要是为了运用真概念来处理一些数学上或者是计算机科学上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并不需要了解什么是“真”。所以,公理化自然成为数学家们青睐的方法。而哲学家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其目的却是揭示真之本质。所以,如果哲学家不能很好地参与其中,不能及时有效地对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加以甄别和反思,那么公理化真理论就很有可能与哲学家渐行渐远。因此,无论是从塔尔斯基转向的角度看,还是从数学基础理论的实际功能的角度看,上述第二个缺点都要求我们去探究一种更为广义的公理化真理论,也即是要能够运用公理化的思想完善以真之本质为目标的左环真理论。
公理化真理论的成就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厘清真理论的各个细节。就左环真理论而言,“公理化”并不意味着采用完全形式化的方式把左环真理论两千多年的思想全部建立在PA之上,而是要把一种真理论当成一个由各种哲学范畴相互联系所组成的有机系统来加以反思。反思在我们的真理论中哪些概念是相对初始的,哪些概念是由这些相对初始的概念定义的;反思我们对这些相对初始的概念的表述是否清晰而恰当;反思哪些原则在逻辑上是具有优先性的;反思我们的真理论内部是否潜藏着悖论;等等。对于细节,霍斯顿幽默地写道:“他们说上帝就在细节里,不过魔鬼也在。我们将看到,通过拟定形式真理论的细节如何使真概念哲学构想的轮廓得以浮现;我们也将看到,真概念哲学观点的缺陷将随着以形式的精确性对其内核的阐述而暴露。”[1]19如果左环真理论能在细节上实现精确和严格,其实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公理化的思想相吻合了。目前,为左环真理论拟定细节的尝试性工作已经在开展[20]。借鉴公理化的思想,而不是教条式地执行公理化的方法,对于真之本质的研究必定是有益的。所以笔者认为,公理化的进路不仅值得右环真理论选择,也应当受到左环真理论的普遍重视。
参考文献:
[1]Leon Horsten.The Tarskian Turn:Deflationism and Axiomatic Truth [M].Cambridge:MIT Press,2011.
[2]Alfred Tarski.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M]//Logic,Semantics,Metamathematics. Oxford:Clarendon,1956:152-278.
[3]戴维森.真与谓述[M].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王路,译.王文炳,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薛瑞.论弗雷格的概念[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7):10-15.
[6]哈克.逻辑哲学[M].罗毅,译.张家龙,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8]SaulKripke.OutlineofaTheoryofTruth[C]//RecentEssaysonTruthandtheLiarParadox.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53-81.
[9]刘大为,李娜.真理论的转向:由定义到公理化[J].哲学研究,2013(5):118-125.
[10]王路.“是真的”与“真”——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0(6):7-13.
[11]AlfredTarski.TheSemanticConceptofTruthandtheFoundationsofSemantics[J].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1944,4(3):341-375.
[12]AlfredTarski.TheEstablishmentofScientificSemantics[M]//Logic,Semantics,Metamathematics.Oxford:Clarendon,1956:401-408.
试验为单因素品种试验,随机区组排列,重复3次。每个试验小区宽4m,小区长度65m,小区面积260m2。每个品种种植6行,地膜幅宽140cm,每膜播种3行玉米,平均行距50cm,株距25cm,播深四五厘米,小区四周设保护行,试验单收计产。
[13]HarveyFriedman,MichaelSheard.AnAxiomaticApproachtoSelf-referentialTruth[J].AnnalsofPureandAppliedLogic,1987,33:1-21.
[14]SolomonFeferman.ReflectingonIncompleteness[J].TheJournalofSymbolicLogic,1991(1):1-49.
[15]李娜,李晟.公理化真理论研究新进展[J].哲学动态,2014(9):91-95.
[16]GeorgeSB,JohnPB,RichardCJ.ComputabilityandLogic[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
[17]JohannesStern.ModalityandAxiomaticTheoriesofTruthI:Friedman-Sheard[J].TheReviewofSymbolicLogic,2014,7(2):273-298.
[18]JohannesStern.ModalityandAxiomaticTheoriesofTruthII:Kripke-Feferman[J].TheReviewofSymbolicLogic,2014,7(2):299-318.
[20]IgorDouven,LeonHorsten,Jan-WillemRomeijn.ProbabilistAnti-Realism[J].PacificPhilosophicalQuarterly,2010,91(3):38-63.
(责任编辑张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