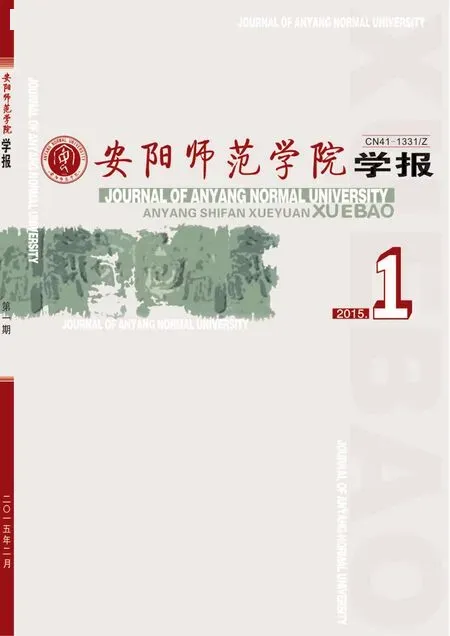孤独的回望——浅析钟文音《在河左岸》中的原乡情结
2015-12-18郜淼
郜 淼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孤独的回望
——浅析钟文音《在河左岸》中的原乡情结
郜淼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在河左岸》是钟文音于2003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六、七十年代,以一个从台南到台北打工的黄姓人家的家庭聚散为主线,以小女孩黄永真的视角,展现了一群从农村到城市、从右岸到左岸的“新移民”的悲欢离合。本文首先介绍了这部小说写作背景,然后解释了作家为何会有这种“原乡情结”,并以原乡情结为切入点,通过与传统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原乡比较,得出当代作家笔下原乡的不同;又通过与大陆70后作家群的一些作品比较,试图探讨他们的作品是否可以因为“原乡情结”而称之为“新乡土小说”。
[关键词]《在河左岸》;原乡情结;新乡土小说
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飞速发展,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渐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在经济发展中许多农民或因天灾破产,或因城市化而失去土地,他们被动或主动地离开了家乡,奔赴到传说中繁华的大城市去谋求更好生活,于是便形成城市中一群特殊群体——“新移民”。钟文音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出生的,由于随着父母在城市打工,她的童年和青少年一直在迁徙和漂流中度过,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恒常的漂流生活造就了她不安定的性格。大学毕业以后,她去当了一名记者,整日奔波采访;后来,她又爱上了摄影,当了一名电影剧照师;可是由于对绘画的喜爱,她又放下工作去美国“纽约学生艺术联盟”当起了学生,学起了油画。终于,在两年之后,受够了思乡之情的钟文音毅然决定放弃油画学习,回到台北,重新拿起笔专注于写作。于是,她写下了这部带着浓浓的怀乡之情的长篇小说——《在河左岸》。小说以小女孩黄永真的视角,展现了父母北上后的情感的裂变,身边亲人和密友的故去,以及一些远亲在城市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在故事中,作者不仅融入了童年时期她作为一个异乡漂泊者对于故乡的怀念,同时也深深地表达了她在异国学习时对于原乡的思念之情。
“原”是“源”的古字,在《说文》中意为“原,水泉本也”,源,即水泉的源头,由此演化出原为“根本、起源、根由”之意。以此,原乡就是人的根源,也就是人的祖先居住的地方,简称祖居地。然而在近现代文学作品中,原乡不仅仅是祖居地,也是作家笔下曾经居住过而又远离的地方。从现代作家鲁迅笔下的“绍兴乌镇”到沈从文的书中的“边城”,到萧红梦中的“呼兰河小镇”,再到当代作家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汪曾祺的诗乡“高邮”,徐则臣的“花街”等,对于原乡的书写从来都不是狭隘的对于故乡的人和事的回忆,而是作者在回忆故乡抒发思乡之情时,对于自身的根或者精神家园的追寻。
在海外华人作家笔下的原乡含义更加的广泛,它不仅指曾经居住过的故乡,也可以指虚拟想象中的故乡,泛指的母国故土,甚至是融入了异乡元素的“原乡”。这里的原乡更倾向于精神意义上的“原乡”。在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原乡人》中,“原乡”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而是小说主人公在痛苦的现实世界中的精神家园、灵魂的抚慰之地。
所以,“原乡情结” 就是作家对自己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产生的一种眷恋、思念或者深沉、复杂的情感认知。作家在表达这种怀乡情感时,不仅表现了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地域风貌,还表达了作家在身体或精神离乡时,从内心深处所催生出的精神还乡。精神还乡而身体却处在异时空当中,伴着错位的身与心而来的情感就是浓浓的乡愁。有学者说:“乡愁是一种病, 它呈现为一种心灵的意绪,如怀望、思念、悲怆或哀愁等。乡愁之所以是痛苦的,是因为人们在经历着无‘家’可归。”[1]古代以及近代的“乡愁”是由于贬谪、战乱或者天灾而远离家乡无法回归,但现代的“乡愁”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体制、历史的原因,还有飞速发展的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让“家乡”面目全非,于是在“小小的岛屿,南北从密合到断裂,再从断裂到衔接,每个人都在改变更新注入乡愁的混合气味,没有真正的原乡,若有也不再以地理方位,而是以喜好以金钱财势以名气来画出领地。”[2](P42)
小说的主人公黄永真从幼年便罹患了“乡愁”的病,这种病似乎是从母胎里带出来的,使得她的眼睛像湖泊,湖泊深处常圈着一轮如泪的薄薄月光。当因为自然灾害失去田产父亲郁郁离家后,在“我”随着外公北上与家人团聚的路上碰到了开柑仔店的表姨时,看着表姨听说我要北上而转身回店里给我拿糖的背影,“长大后我回想那个背影,才明白了那个背影就是一种嵌着乡愁的离别身影。”[2](P54)怀揣着无限的乡愁,“我”在淡水河左岸度过了孤独而贫穷的童年,这样的童年经历使得“我”是倾斜的,根在台南,树干和枝叶却倾斜地长在台北。然而不论是左岸还是右岸,经济的发展,环境的巨变,使得“我”恒常的觉得孤独、寂寞,有种被遗弃的感觉。小说中“我”的童年生活经历就是作者自己曾经的生活写照,在后记《属于台北人的河流故事》中,作者明确的表示“我童年时曾经住过这条河流的左岸,当年的左岸贫穷与杂乱。沿岸的留驻了许多来台北打工的南方移民,想到繁华都市发财的梦想家、失婚的妇人、寂寞的男孩女孩……”钟文音在童年的时候就随着父母来到台北生活,由于父母经常换工作,她也就经常随着父母在台北城里漂流。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黄永真一样,她的根是倾斜的,台南和台北同样都是她的“原乡”,这样也就造成了她是一个特别的具有“双乡心态”的作家。
二
由于钟文音这种特殊的创作心态,使她笔下的原乡与现代传统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原乡有着许多相同却又不同的地方。首先,作者继承了萧红、沈从文传统乡土小说作家对于故乡的诗意化的处理,原乡犹如精神的桃花源,在痛苦孤独的现实中给人以精神的慰藉,那里的山水土地似乎都带着灵性。其次,是作者的个人成长历程造成的特殊的“原乡”,这个原乡并不是作者长年居住的地方,而是从幼时离开后来又不断回去的故乡,于作者而言,这个故乡大多是从先辈回忆的想象里和自己回归的现实经验结合而成的。最后,是现代化的发展异化的原乡,这里的原乡已不再是作者童年时候的原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的现代化,即使身处原乡,也使得作者流浪在异乡。
1.诗化的原乡
在小说中,作家从小女孩黄永真的视角,以她出生后睁开眼睛到成长为一个在淡水河两岸漂泊的少女为时间线,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段围绕在她周围的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的故事。在小孩子的眼中,成人复杂的世界反而变得简单、淳朴,充满诗意,犹如世外桃源。
“我”(黄永真)爸在同意北上的那天下午第一次抱“我”,“当我们看出去的风景是降低水位成了浅滩的河水,我爸突然击掌,对拍的掌声音量如枪爆阵阵,瞬间我的头顶有影飞过,成群的白鹭鸶从浅滩惊慌飞起,泛白的日头照得水面闪闪如白银发亮。”[2](P8)拨开茂密的芦苇,成群的白色大鸟飞起的景色,让人不禁想起杜甫的那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可是在美丽清新的景色背后却是表达主人公的父亲即将北上忧愁与彷徨。主人公“我”虽然笑得咯咯响,但是在年幼的身体中的老灵魂却敏锐的觉察到了父亲那说不出的乡愁。
从台南搬到台北,黄永真一家生活在淡水河左岸的矮厝中。河边一片片豆腐块似得矮厝里有着一群靠着皮肉生存的妓女,而这左岸是女人的寂寞堤岸,男人的欲望城邦。白天当太阳高照时,她们揽镜对照化着看不出年龄的浓妆,夜晚她们寂寞的等待那些南来北往的男人,给他们一点点身心的安慰。这些妓女原本应当是被人所不齿的下等人,然而在黄永真的眼睛里却并不讨厌,她甚至和妓女菊菊建立了特殊的友谊。
作家在小说中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再表现或者说是再生,实际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所以那逝去的童年场景必定是充满诗意与美好的。正如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小城”,在小镇中发生的那些残忍的故事,却在孩子般稚气的口吻和语言中消解,表达出的却是作家对于家的温暖与爱的渴望,以及身处异乡的悲凉之感。对于钟文音而言“长大后,不断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旅行。我回首才发现,其实去哪里不都一样。如果还有不一样的世界,那是重返我和你的童年境地,就像我们常常突如其来的小小旅行一般,只有回到那个状态,才有惊奇,才有温度。我一直在重返过去,因为现实太无趣。”[2](P119)正如唐小兵所说:“故乡是成人世界中儿童天地的遗迹。儿童是不需要故乡的 ,因为孩提时代本身就是故乡。”[3]对于童年故乡诗意化的再表现,正是钟文音对于在现代社会中失去原乡的孤寂感的弥补,使她在现实世界不至于太寂寞。
2.非经验化的原乡
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春明、王祯和的乡土小说对于乡村人情和农民价值观、人生观的深层表现和刻画,钟文音小说中的原乡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在小说中,“我”离开故乡不过才四岁,对于故乡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发生了什么故事,只能通过想象结合童年的记忆和从先辈那里听来故事。正如小说中作者说“纪实本身隐含虚构,虚构也是某种纪实。执笔的诉说者明白故事在我和台北之间形成这样的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关系,不论这个叙述者‘我’是否在现场,故事总是可以流传到‘我’身上,想象力为‘我’开辟了一个微观的天地。”
穿过黑乌乌的厅堂,我母亲的几代余家祖宗牌位上方长年挂着一盏垢黑的油灯。我真正的外婆挂在其中,她在我妈妈一岁时就撒手而去,那年她才十八岁。我妈上头另有一位大舅舅,大她三岁,我外婆十五岁结婚生子,三年后告别人世,生命的节奏快速紧凑。我妈幼童时第一次看见飞机,她说她仰着头望着天空快速留下一道白白长烟痕时,她想起的画面气氛带着一种模糊的感伤,在那天空白烟的仰望里她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一个过于早逝竟没有留下任何一丝一缕记忆给她的一个历史人物。原来任何人事和事件都可以有着超越时空的速度可一飞冲天,“真是一切都难想象啊。”我妈在追溯这件事时,她正在廊下洗摘下来的一串串白葡萄,白葡萄等着入瓮浸泡成酒,整个空间都是葡萄的酸和糖混着酒精的气味。我妈并不是说给我听的,她是在自言自语。”[2](P47)
对于外婆的记忆“我”是通过母亲的“自言自语”了解到的,那个生命短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外婆就像飞机喷气在空中留下的一道白色的长烟痕,纯洁却转瞬就消失了。在小说中,主人公的原乡是如此的模糊和飘忽,似乎也和外婆短促的生命一般。原乡的人和故事大多是“我”同乡人、先辈和朋友那里获得的一种间接经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原乡回忆都是间接的经验,还有作者一些自己的体会,比如,当“我”北上后,拆着存钱买的可口奶滋和义美夹心酥饼干时却总是会想起那些属于亚热带小杂货铺的糖果饼干,吃完后嘴唇总是粘黏着果浆和饼屑。
通过直接或间接经验而刻画的原乡,是飘忽、模糊的情绪记忆,这是由于作者并没有一直生活在故乡,而是在幼时便远离了家乡,即使后来回到故乡也是因为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情。原乡的亲人纷纷来到台北打工,而剩下的老一辈亲戚也相继过世,再加上经济飞速发展,乡村城市化、现代化,回到故乡也感受不到原乡的温暖,身在故乡却是“他乡”。而且,作者也并没有具体刻画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是怎样劳作,怎样生活,有什么思想观念等问题,而是巧妙的运用意识流的方法,通过一个个片段式的描写,将原乡与异乡、现在与过去的故事相互交融。
3.异化的原乡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加速,当代作家的“原乡”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的异化,小说里台南那个美丽的小乡村也不复存在。小说中的“我”最后一次回到南方是因为十三年才轮一次的村落作醮。
别人是沧海变桑田,我们老家却是桑田变沧海,田地换鱼塭,四处在抽着地下水,散着养猪的馊水味,那是家乡的气味。四处有杀猪宰鸡的哀号声,猪公的白色尸体堆积如战场,入夜需动用挖掘机才能把猪只运上卡车,白白的猪体映着惨白的路灯,黄色车身挖掘机声音哄哄响,电子花车燃亮巨型灯光行过,原来这叫后现代。
嘉义布袋附近的“好美里”海边,有过我们快乐的海边闲走。好美,好远。[2](P248-249)
南方的原乡在大洪水重建中变成了鱼塘和养殖场,隆隆的机器声在原乡不停地轰鸣,俗气却又耀眼的电子花车,盯着钢管舞女郎欲望露骨的老人家……在时间的长河中,故乡早已不复原来的样子,亲人离散,桑田变沧海,环境的破坏使得原本熟悉的家乡变成了陌生的异乡,就连淳朴的乡村风俗都变得电子化、商业化、欲望化了。
乡村的原乡变得城市化,而城市的原乡也因经济的发展而变成了异乡。那条恒常流动的淡水河,是作家童年原乡的象征,然而现在原本清澈的河水早已不见,漂满鱼贝的腐尸,岸边蛋形的污水处理厂强暴着人的眼睛。与古代诗人乡愁的不同,诗人的家乡可能是因为战乱或者巨大的灾难而无法回去的远方,即使家乡被毁去,心痛难当也如当心一刺,巨大的痛苦是一时的;在现代传统作家的笔下,家乡是在战争年代颠沛流离时的精神家园,在痛苦的现实与甜蜜的回忆之间撕扯;而在当代,故乡却在一点一点的消失,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却无法阻止所谓的现代化进程,这比之被天灾一下子毁去家园还要令人心痛,如凌迟。所以作者常在小说中借主人公的角色,表达自己孤寂、无奈、哀愁的感情,这种情感无不显示著作者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根的缺失时而流露出的精神危机。同时,作者通过对于异化原乡的亲身经验,批判地完成了对于自己的根和家族、民族的认同。
作家的还乡不仅是寻找自己在现实中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呼吁人们保护家园的呐喊。作者小时候生活在淡水河边,家门口恒常的风景就是河流和动物。然而,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原本鱼贝繁多的淡水河如今已经变成了腐尸漂流的毒河,海水倒灌,水患成灾,涝病散肆,家畜死亡。昔日繁华的淡水河岸边,如今已被污水处理厂占据。作者在《淡水河记》中,强烈的表达了对于台湾生态危机的忧虑,呼吁人们和政府保护生态环境,让我们回归到原乡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回归到经济飞速发展前的质朴的乡情。这无疑表达了作者对于传统文化回归和建构的渴望之情。
三
在大陆,一些“70后”作家的作品与钟文音的长篇小说《在河左岸》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这群70后作家与钟文音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七十年代的大陆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探索改革开放的道路,经济也随之逐渐好转。社会现代化进程加速,大批农民进城打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0后作家出生了。童年或青少年时在乡村出生,后跟随父母来到城市,他们是目睹原乡变化的乡村城市人,90年代初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写下了一批关于当代新的“乡土小说”。
70后作家群中有不少作家都有对“乡土”的书写,徐则臣的“花街”、“石码头”,鲁敏的“东坝”,魏微的“吉安”小镇,艾玛的“涔水镇”,乔叶以“非虚构”抵达的故乡。其中徐则臣笔下的“故乡”书写最令人注目,他笔下的一系列关于“故乡”的小说:《花街》、《镜子与刀子》、《水边书》、《花街上的女房东》、《人间烟火》、《紫米》、《午夜之门》、《还乡记》等等,都是关注了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中的乡村人故事。这些小说有个核心的意象就是“花街”、“石码头”,这些地方通常在码头或者古运河岸边,这与钟文音《在河左岸》中的淡水河以及那些河岸边矮厝里的妓户街相似,同样都是诗意化的原乡,如雾一般弥漫的淡淡的哀愁。还有他笔下“京漂”系列的小说:《天上人间》、短篇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同样讲述从乡村到大城市北京打工的外乡人在异乡打拼的故事;并且同样在故事中使用儿童视角,以追忆的方式来书写“故乡”的风土人情、地域景貌。有的评论者称他的这些作品为“新乡土小说”,那么钟文音的这部《在河左岸》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新乡土小说”呢?
在台湾,自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战就已经开始,当时出现了许多关于“乡土小说”的理论著作,叶石涛的《台湾乡土作家论集》,陈映真的论文集《知识人的偏执》,王拓的论文集《街巷鼓声》,由尉天聪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等等。王祯和说:“我认为‘乡土’ 最简单的意思是写你所熟悉所爱的事情,写你所关心的人、事。”王拓认为:“乡土含义所指的应该就是台湾这个广大的社会环境和这个环境下的人的生存现实,它包括了农村,同时又不排斥都市。而由这种意义的‘乡土’所生长起来的‘乡土文学’就是根植在台湾这个现时社会的土地上来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们生活和心理的愿望的文学。它不仅是以乡村为背景来描写乡村人物的乡村文学,它也是以都市为背景来描写都市人的都市文学。这样的文学不只反映、刻画农人和工人,它也刻画民族企业家、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教员以及所有在工商社会里为生活而挣扎的各种各样的人。”这样看来“各种乡土的解释,都可以在意义模糊的‘乡土文学’旗帜下兼容并包。”[4]乡土小说的含义已由传统的描写乡村风貌、乡村人,有地方色彩,怀着浓浓的乡愁的作品,扩大到已经不分城市与乡村的地域差异,变成了精神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被赋予了与“现代”相对立的“传统”文化内涵。从广泛的“乡土小说”的定义来讲,钟文音与大陆70后作家的关于书写乡土的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新乡土小说”或者“轻乡土小说”。
但是,综观徐则臣的小说似乎具有一种后现代主义,就是把什么都可以放在台面上来写,但是却缺乏真正的精神超越。正如评论者所说的“从某种共性上讲,也许70后这代最要紧的问题就是他们大都有一个虚无主义的精神底子,在这种底色之上,什么东西都被放到怀疑主义的案板上切割,一切都难以真正落地生根。这种价值立场的悬浮状态,不是徐则臣个人的困惑,而是一代人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70后作家就处于这样一种‘互糅掺杂’ 的精神状态。”[5]在钟文音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杂糅的痕迹,在阅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原乡情结”只不过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元素而已。纵观整部小说,每个章节的核心故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亲戚朋友来写的,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史小说;再看故事中,对北上后父亲角色的消失,母亲虽然也有与父亲以外的人有情感纠葛,但是从未抛弃“我们”,“我”作为一个女性的视角来看、听、感受这个世界,都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对于故乡土地河水等自然环境的依恋与喜爱,对于社会环境的破坏的忧虑,让这部作品带有浓浓的台湾本土气息,让读者闻到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上打拼的人们之间质朴的人情味。
从这方面来看,“新乡土小说”虽然扩大了小说题材和内容的范围,但是也由于兼容并包过多,可能失去了文本的深度,遮蔽了一些社会现象、事物的本质。但就艺术方面来说,《在河左岸》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王杰泓.原乡情结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2):158-162.
[2]钟文音.在河左岸(海峡两岸“这世代”书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
[3]唐小兵. 英雄和凡人的时代[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51.
[4]吕正惠.七、八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与变迁[N].联合报·副刊,1993-12-17.
[5]翟文.70后一代如何表述乡土——关于徐则臣的“故乡”系列小说[J].南方文坛,2012,(5).
[责任编辑:舟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5)01-0093-05
[作者简介]郜淼(1991—),女,江苏徐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