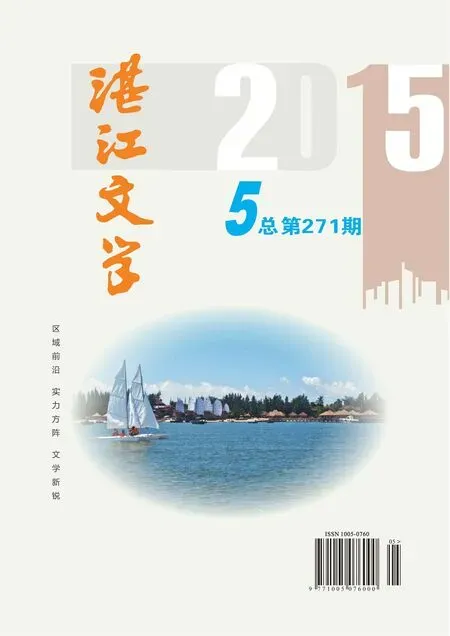诗纪·80后
2015-12-18主持人赵目珍
※ 主持人:赵目珍
诗纪·80后
※ 主持人:赵目珍
【主持人语】
丁成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文学史的,二是先锋的。所以“诗纪·80后”的开篇人物,想都没想就定了丁成。当然,这两个意义在丁成那里,不知是否有轻重缓急之分。在我看来,这两者可能是并重的。比如,他谈先锋诗歌的重要意义:“时间不老,先锋不死。正是先锋褒有了诗歌存在的意义,以及不断生长的可能。”丁成一直在渴望着写作上的突破、冲锋和一骑绝尘!这让他赢得了精神领袖、天才、异端等诸多“先锋性”的称谓。读他的诗,我们对他的“先锋”将更有体会。对于史的概念,丁成曾有一句话:“我不要历史过几年才来找我,我要历史现在就找我。”这看起来有点近乎狂妄的“大言”,在很多人眼里也许视之为“狂狷”之语,其实就史才层面而言,它正体现出一个人对诗的无比自信和承担的勇气。

几年前,我还比较反感看起来有点狂妄的人,甚至对那些过早地为80后诗歌下断语、作总结的人颇有不屑。最近,突然转变了这种看法。至少在丁成这里,我由反感与不屑一变而为敬佩和尊重。值得敬佩的是,他以先锋和异端的姿态替“80后”一代中的诗人率先冲击了诗坛,开启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八零后诗歌运动”从此蔚然而兴;值得尊重的是,他在不尽然的“狂妄”中实现着个人强烈的自信。他首先在诗歌上耀示出两个“先锋”(一是时间上的,二是文本上的),其次也向理论批评发起猛攻。他以历史的眼光构筑着属于“80后”诗人自己的文论和文学史,他主持编纂的《蓝星——80后文论卷》以及《80后诗歌档案》等在“80后”文学史上至少有着“领一代风气之先”的地位。就算撇开属于他个人的一切实绩,“80后”诗歌史也要为他写下隆重的一笔。更何况,他个人的创作实绩还不是一般的“突起”。
丁成似乎是一个因富有强烈自信而近乎“狂狷”的人,但其“才”与其“狂”相得益彰、互为表里。丁成不是一个因“狂”而被“轻”,相反,他恰是一个因“狂”而“重”的人。
【丁成诗选】
广 场
曾经布满绞刑架和刺刀的地方
曾经无数反革命被剿杀的地方
现在摆上了鲜花
地面被反复打扫和清洗
对于广场
环保工人比历史学家更有发言权
那些历史的血污和真相
是他们赖以寄生的本钱
游人来自四面八方
那些黑的、白的、黄的、棕色的
那些高鼻头、蓝眼睛、矮的、高的
在祖辈拼杀过的地方学会凑热闹
喊杀声并未远去
那些在内心深处紧锁着的硝烟
从曾经的广场撤了出去
它们都学会了世故和老练
在滚滚流过的时间背后
它们磨刀霍霍
准备随时砍向每一个翻开历史书籍的
人们
广场没变风雨没变
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牌
那些肥臀丰乳的女郎
那些快速流动的高架路
那些随地吐痰的民工
那些政客那些小偷
那些匍匐在地上的乞丐或者骗子
夹杂在一起,对着广场指指点点
早上经过的年轻人
天晚之前就已老态龙钟
或者换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孩子
或者永远都不再回来
广场的四周竖起了巨大的塔吊
一幢幢高大的建筑物开始围着广场兴
建
物质把这个城市养得脂肪丰腴
广场的人群越来越多
目光越来越陌生
新兴的事物正在塞满我们生存的空间
“我是另一个”、“我不是另一个”
夜晚的广场,各种花哨的灯光
开始分裂我们
影子由一个变成两个再变成无数个
站在广场上看着周围无数个陌生的影
子
我们不再认识自己
不再认识这个曾经的广场
时代变老我们变老
广场上的石头变老
年轻就是悲哀
就像广场上的新石头一样毫无价值
时代的心壁正在一寸一寸地变得薄弱
我们不知道还能以年轻的名义坚持多
久
物质的力量像砂轮一样
先是把我们打磨得非常锋利
然后是锋利着
并悄悄地损耗
曾经的高度现在是多么的虚幻啊
一代人的广场带走了一代人的年华
现在,广场屹立着
装点广场的鸽子飞来飞去
时代变老
我们变老
广场上高大的纪念碑正在日渐矮小
那些物质的蒙尘
就像额头的皱纹一样悄悄爬满
一个时代的脸庞
曾经象征自由的广场
正在被一寸一寸地掏空
剩下一具苍老的尸壳
人们争先恐后地填充进去
那些肥头大耳的刽子手们坐上了高档
轿车
在高架上对着红灯前拥堵的人群指指
点点
人群里的我们彼此陌生着、孤独着
激烈的、锐利的、闪着寒光的我们
正在听着自己被蚕食的声音
细小的微弱地
挤在漫天飞舞的扬尘中
就像得了绝症的人们
每日狭路相逢同一个噩梦的困扰
陷阱朝着我们,朝着一代人
张开了充斥着繁华的、文明假象的大
嘴
我们被物质的力量挤着、推着拥上广
场
此刻,我们清醒地意识到
面对广场,面对时代
我们都已无药可医
2004悼词
流血断头飓风海啸强力地震的2004过
去了
血洗的战场、冰冷的海面被大雪覆盖
凶手和受害者签字的和约幻化成雪
成排的尸体衣衫不整,丧失呼吸和脉
动
安静的仪态,是这年最后的灾难。悲
痛
像一只鲜活的生命体,蜷縮、抽搐、
慢慢剥开
从皮肉里显现的五彩泳衣,布成炫目
的地狱
万里之远,消失的村庄,下落不明的
人群
受惊的水蛇和吐着泡沫的鱼,这些先
知
浮上咆哮的浪尖,尖锐的风,响彻高
空
大片大片轻声的啜泣,低低地回荡
像持续的震波,扩散——扩散——扩
散
激烈抖动的地壳,海水从大洋上席卷
而来
像神秘的人为熟睡的孩子轻轻地拉上
棉被
激烈地舞蹈,在疤痕上撒盐的快感
沿着轴心位移的岛屿撕开一条深幽的
悬崖
最后的海滨,消失在每一具遗体的身
边
走失的钥匙,再也没能找回锁孔
就像迷路的门扉再也遇不到夜归的人
2004批麻戴孝地走在我们眼前,走在
身后
雪。从30日一直持续到31日,夸张的
白色
掩埋了在战死沙场的和平和反和平的
大兵们
掩埋了命丧海啸的富人和穷人们,眼
泪平等
掩埋了审判席位上的大胡子战犯,掩
埋了血统
封江警报顺着大水一路回溯到上游,
急促的呼啸
闪着红光。在雪景的反光里苦苦乞讨
的人们
一步三滑地寻着前路,他们要在新年
的钟声里
找到大雪后的阳光,找到人间残剩的
温情
乡村屋檐下的冰柱,泛着良心冷却的
寒光
永不冰结的悲伤像坚持一秋的树叶
从枝头跌落下来,转眼之间失去亲人
的可怜
让人来不及悲伤,来不及痛哭,像过
电一样
拿起扫帚,在无人经过的清晨,清扫
积雪
从门前直到马路,昨夜的积雪凝成冰
花
有人跌倒,再也没有站起来,伏在路
面上
像一张遗像,慢慢显现出年代久远的
灰白
每一口呼吸,冒着新鲜的热气,声音
从海底
发出幽蓝的音泽。深深掩埋的遗体上
方
摄氏零下的温度中,摇曳着一朵颤巍
巍的小花
一夜之间,他们看着自己的白发一根
一根变白,
覆盖了整整一条生命通道。人是如此
的容易苍老
光从高处撒下来。垂直升起的烟柱在
雪地上
投下孱弱的阴影。电话的盲音久久回
荡
像葬礼上空的哀乐,始终没有降下
四个方向的迎新倒计时,已经掐下秒
表
成千上万张脸上洋溢着新年的光泽
封江警报撤除,高速公路业已重新开
启
每一条路、每一条航道都通向2005
后视镜里越走越远的2004闪着灰蒙蒙
的光
大雪悄悄融化的夜晚,罹难者轻轻翻
身
悄无声息的时间,掀开新的一页
跟刚才还是积雪覆盖的道路一样干净
逐渐显露的暗黑色屋顶,在阳光下
像一块陈年的斑点,它们低矮的骨架
在现代都市的高楼大厦间坚定地
闪烁着苦难的光泽,永恒的风景
一群越冬的鸟,从一侧俯冲而下
像占卜者一样,翅膀扑腾之间
将时间远远地拽进一本崭新的日历
不可预知的灾难或者幸福像幽灵一样
深深地隐藏着。生命的游戏规则
决定我们必须按部就班地跨越时间
按部就班地跨越苦难、战争、瘟疫
一生苦苦寻找幸福,在不知所终的路
上
葬身未知的灾祸,就像刚才,和什么
都没发生一样
火 祭——写给自己
这一刻火苗升起,人世向下弯去
这一刻火苗降下直至熄灭,到零
我裂开嗓子啼叫,一个得了精神病的
婴儿
百经周折,哭出了声音,火苗从嘴里
大口地吐出
燃烧的长夜啊,栅栏、丛林和城市
在苍白的纸面上显出了暗黑的灰烬
浮动的火,大片大片的游荡,上升和
下降
在长空里它们是没有根须的灵
它们烧着了恐惧的眼帘,细长的睫毛
和那些雕花栏杆整整五年没有油漆了
一夜之间,从锈迹里探出一丝光亮
抬头,白色的天花板上布满日月星辰
无底地深邃在这里显现,像我永远填
不满的沮丧
那些正在试图飞翔的水和未曾熄灭的
寒冷
酝酿着一场燃烧,冰冻的世界开始下
雪
伴和着我的赤膊,清瘦的笑容
已经没有词汇的语言,开始向下流淌
但我早已深深地被冰层掩埋,顽固不
化的火尚未成形
没有出口,无边无际的遥远直上西天
火焰在悄悄地往回撤,缩回内心
我的偏执,让我的舌尖再次碰落牙齿
贝壳一样撒满深浅不一的房间
在天际,在厚土之下,我用三尺三寸
的距离赎回肉身
一个声音像弹片一样肆无忌惮地撞毁
一切
我重新回到业已冰冷的躯壳
寻找冷热均衡的法则,寻找一个飘渺
的梦
我翻身落马像一个被苍生诅咒的君王
一样蒙羞于世
是的,我燃烧过,也熄灭过
但,火苗的中心,已经被再次抽空
这是我的降生之日,你们看见闪电和
云层
以及望不穿的黑正在覆盖这流火之后
的世界
一束空洞的火发出光,万丈深渊
注定属于悲剧席卷的一切
谁来和我一起演奏哀歌呢,向深深端
坐我心头的神灵
祷告苍生的苦痛尽早消逝,然而
你正尝试着用你的绝情和孤傲将我远
远地赶走
我沉重的肉身已经绑满石块,在火焰
中沉下去
义务反顾地直到底端,生活无端地将
我耻笑
我望穿了世界,尽头空得可怕,什么
也不能令我镇定
是什么在让我们互相背弃呢
同样激烈却不曾让我感受温暖的火焰
还是一颗早已低下头去的冬日的香樟
树
相比之下,在这一天我愿意缩回坚硬
的内壳
让我变得柔软的躯体接受敲打
把曾经的一切从我身上打散吧,前世
和今生
之间的距离和阻隔,已经把我折腾得
精疲力竭
岁月的印痕从头到脚,在降生的一刻
戳满我的全身
我备下了另一处行宫
花朵翻飞,离开身体的舞蹈
它们的节奏让我彻底心碎
十五平米的房间里摆满空的座椅
我放弃了飞行,放弃了喷薄而出的烈
焰
我生于这一天,一年之中最后的绝望
面若死灰
我获得了自己冰冷的意志
颤抖的灵肉啊,沧桑过早降临
像火一样坐化是我的选择
从小我就学会通过火苗去端详自己
空洞的时间来到我的面前
那些修长的指针,正在自行弯曲
内脏失去光泽,日复一日地病变
使我们无法读懂的紊乱缠绕着
我可爱的妻子,六百年前
她自行爬上供桌,在佛堂里拈花微笑
手拿净瓶,这累世的差错在香火之中
在香火之远早早覆灭
随着笑容,我坚持到了最后
一束隔冬的三叶菊重新开放,这最后
的花期
来得漫长而又无望
诅 咒
橘黄色的聚脂纤维,黑色的蝌蚪
我想象完全偏离的味道,没有必要的
担心
这是一次机会。粉碎不切实际的幻想
怪物的嘲弄,你苍白的眼袋
我们无法达成一致,你是少女,你是
被诅咒的蜜汁
若干年前我们相识。认为一次全城的
演出
关于商店,她们把解雇的合同放到高
处
祈求吻,祈求家具和口号,你们熟悉
的秩序
颧骨和爵士乐,这一生,他们无聊地
生活
搬上粉白的肚皮,或许因为快感,或
许因为无知
红色的光晕和幕布开始谢去。你们的
命运
在这里是必须的,是注定的。这将是
一场高雅的艺术
疯子们!我们允许平民中的灰姑娘变
成旅游项目
允许女人变成木头,顺着雨水变黑,
腐烂
很多人说起,很多人见过——尼斯湖
的庞然水怪

丁成:诗人、批评家。1981年12月5日生于江苏滨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后兼事批评理论。主编《80后诗歌档案》。作品入选《1978-2008中国优秀诗歌》、《中国当代诗歌前浪》、《当代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等重要选本。2002年发起中国80后诗歌运动,在中国诗坛引起巨大反响。2010年获首届汉江·安康诗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