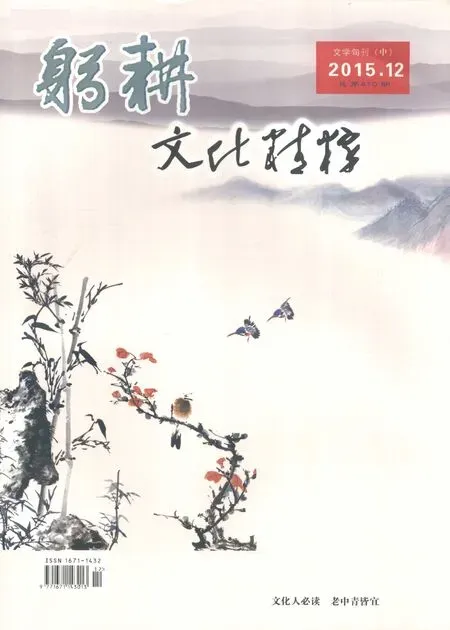杨维永作品印象
2015-12-17◆刘军
◆ 刘 军
地方性写作框架在当下文学实践中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这一概念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地方性写作,指向相对广阔的区域,出于传统礼俗、民俗、信仰、地缘文化观念、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趋近,在水土风貌、人伦法则的共同渗透下,诸多作家作品呈现出近似的文脉和气息。就全国范围而言,地方性文学群落中,作家众多,代际构成充实,影响最大的当属南阳作家群。这一作家群被誉为“中国当代最有名的地市级作家群”。
南阳作家群在各个体裁领域皆取得丰硕的成果,小说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周大新、二月河、乔典运、田中禾、行者等,诗歌方面有汗漫、一地雪、张永伟、魔头贝贝等,散文方面有周同宾、廖华歌、祖克慰、水兵等,评论方面有何弘、梁鸿等,影视方面则有柳建伟等。世纪之交,部分专家学者就南阳作家群创作现象召开了研讨会,在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作家主体三个层面,透视南阳作家群的成因及写作走向。
来自南阳社旗县的杨维永即为南阳作家群的一员。其创作历程,凸显底层写作者执著、坚韧的写作信念,以及缓缓向上攀登的曲线。杨维永的人生曲线经历过三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为身份上的突围,中学毕业后落榜的他经历过四清运动、文革、包产到户前极度的物质贫困,作为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的青年农民,他通过自学、函授、学习班形式,成长为乡村知识分子,并在自身努力的情况下,进入城市,吃上了商品粮,由临时工转换为拥有正式城镇户口的工作人员,进而完成了身份的转换。第二个节点为公共文化事业的付出,从县志办秘书到主任,再到文化局,因地方志编纂及地方传奇故事的整理工作获得国家社科奖。如同笨牛拉车,一步步向着文化事业的高地前行。在人浮于事,投机主义盛行的文化环境中,其老黄牛般耕耘精神,以及农民本色的立身处世方式,所划出的恰是“愚笨者”之成功之道。第三个节点为其对文学的一往情深,过知天命之年,一片痴心不改,且更上一层楼。爱因斯坦曾指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放在杨维永身上,恰到好处。
杨维永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评论、散文等体裁。从其创作履历来看,中间二十年的公共文化事业的爱岗敬业,制约了其小说创作上的数量积累,无疑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并非不可弥补。杨维永的小说写作,在主题发掘和价值取向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介入现实的写作立场以及批判乡土世界愚昧、封闭、落后的主题发掘。马尔克斯曾言:“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杨维永的小说创作素材,基本取自其自身的经历。如短篇代表作品《油坊挽歌》《疯子》《一袋棉花》《婚孽》《玲的婚事》,从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来看,大多来自50-80年代的农村大集体生活的记忆,偶有涉及民国及晚近的乡村现实,也仅仅承担情节的铺垫功能。这些素材涉及到家长制下的男女婚恋问题,人伦关系中的利害算计,畸形的情欲关系等,人物及其行为往往隶属于乡土文化中处于边缘的区域,与传统礼俗以及现代文明的理性法则构成对立或者挑战关系。《油坊挽歌》(《莽原》2012年2期)中刘堂黄做人并不堂皇,他与其父亲刘大炮一道扮演了“老赖”的角色。因眼红王致富的油坊生意,父子俩上演了死缠烂打的好戏,风烛残年的刘大炮闹到县法院,遇挫后当场气绝身亡,两家之间的“梁子”愈发趋于死结,刘堂黄对王致富家接连下起了黑手,先是用利刃刺断王家母牛的脚后筋,后纵火麦秸垛,砸烂油坊机器,一番折腾下来,王致富最终服软,屈服于乡村恶人的淫威,由精明能干的农人,回到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行列中。小说揭示了存在于中国式农民身上的另一面,即攻击性、破坏性、占有欲。这种从恶的心理有着深远的心理渊源,历史上均贫富口号具有极大的杀伤性,强化了底层人们身上的仇富心理以及盲动性,每逢乱世或者末世,这种戾气就会集中爆发,对于社会秩序及文明积累具备了强大的杀伤力。而作为人物生存背景的农业大集体生活,无疑强化了底层百姓观念里的均贫富思维,这也是小说中王、刘两家悲剧的深层原因。仓廪实而知礼节,一旦遭遇物质上的匮乏期,诸多反礼节的行为则密布于乡村的人伦关系之中。有过贫困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对于这种嫉妒心理和算计行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一袋棉花》(《草原》06年5期),年青时期的秀云和刘胜本两厢情愿,情投意合,两人的缘分却因为秀云母亲治病缺钱,而被其父亲生生拆散,家庭的利欲关系超越于子女的婚姻之上,秀云作为一个交换品嫁给了王二呆。事情还不算完,婚后的秀云认同了家长的安排,为了谋划自己儿子的婚事,竟然算计着与刘胜的重新“结合”,这里并非两人的旧情复燃,而是出于家庭厉害关系的肉体交换。子承父业,到了秀云这里,却是别一种病态的形式。费孝通先生曾以差序格局总括传统的乡村社会,在他看来,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此,传统的道德里找不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所以,在这种极富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但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即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当私欲越过边界,礼法之治无法约束之际,自然会泛滥为恶。《疯子》(《青年文学》09年1期)则讲述了集体主义生活的强制性掏空了一个人的思维的故事,做生产队会计的小张因账目上出错两毛钱而被正在铺开的四清运动抓住了小辫,从此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逐渐演化为管理村民小组财务上的过度洁癖习惯。改革开放后,小张成了老张,自己的会计角色也被更换,更换者利用政策的漏洞,大肆贪赃,老张于是走上了上访之路,并以几十年前的账本作为逻辑主导,诉求于信访系统,遭到否定后行为也变得失常,成为路人眼中的“疯子”。老张的悲剧在于个体的软弱,在强有力的集体主义面前,思维由僵化步入固化的状态,成为“化石”般的人物。
婚恋关系的审视是杨维永小说的另一个重点主题。钱中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现象并存的社会。中原厚土作为农耕方式持久性存留的典范代表,这一区域文化下前现代性的遗留特别突出。而故事发生地——南阳盆地,因其自身的封闭性,自然会强化这种前现代性。表现在婚恋关系上,则为某些陋习的习惯性存在。《难忘的那声“姨夫”》中瑞姨为了满足家中长辈换亲的要求,不得已和“二叔”分手,婚后再相见,悲痛欲绝。香火承续和重男轻女的思想,乃传统乡土文化的病根,这一病根依然固守于人的观念之中,让人哀叹。《玲的婚事》(《江海文艺)07年1期)中家长制下的包办婚姻摧毁了玲美丽的青春,面对婚约关系的变动,最后以个人的身死以示绝望之悲。《采访纪实》中困顿的现实和情欲的张力,使得狗剩和二蛋这两位共患难的兄弟竟然订下了“共妻”的契约,作为二蛋的媳妇,翠花居然半推半就地应承下来,成为这出荒诞戏剧的共谋。除了换亲、共妻这些前现代遗留下来的丑陋习俗之外,杨维永的诸多短篇,不经意间就带出了婚内家暴的直接性和普遍性。总之,男权意识,家长制,以及恶俗,成为其短篇小说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入和出涉及到写作主体写作能力和思想能力的整合问题。对于杨维永的短篇创作而言,入之深层面,并不存在问题,关键是“出”的因素尚有缺失,这也导致了其小说在精神主题的开挖方面仅仅停留于批判和审视层面。阅读其小说,常常有这么一个感受,即小说到故事而止。讲故事的能力是小说家的基础能力,当然,讲好一个故事也相当不易,需要细节的勾勒、场景的铺陈、氛围的烘托、知识考古学的体系性,以及语言的生动、准确与简洁。故事之外,尚有更纵深的空间等待写作主体去探寻,这一空间涵盖了历史走向的把握、时代心理的审视、人性的多重维度等等。
乡土写作,最终要落定到现代性的层面,即现代性的诉求或者展开。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就是一种以全球化为本质的社会生活或者组织制度模式。在传统题材的新开掘之外,新世纪乡土小说拓展的最新题材领域是“农民进城”和“乡土生态”,前者将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向城市拓展,后者则向荒野展开,二者都是中国乡土小说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尤其是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乡土小说自身转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如何及时地介入当下底层农民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人伦规则的变异性,是摆在每个乡土小说作者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