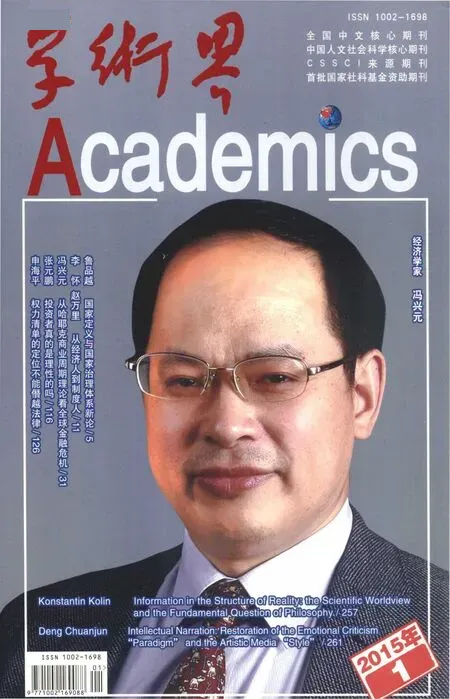从经济人到制度人〔*〕——基于人类行为与社会治理模式多样性的思考
2015-12-16赵万里
○ 李 怀,赵万里
(1.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25;2.大连海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拂开经济学的历史长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另一幅画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代刻度。科斯和诺斯的获奖表明了制度经济学已经踏上了主流经济学的门槛,而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的获奖则标志着制度经济学已经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当主流经济学在起劲卖弄“经济人假说”这一招牌的时候,不知始终没有自己的招牌和旗帜的制度经济学陷入何种尴尬。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在于“经济人假说”,由此说来,制度经济学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基础,仍然固守“经济人假说”,就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至多沦为经济学的附庸。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愿将此文奉献给经济学界特别是制度经济学诸位同仁。祈求斧正,共振学术。
我们知道,人总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内活动,而维系这个秩序框架的就是制度。离开制度,社会就失去秩序,人类也将难以生存和发展。比较而言,人类的经济活动更需要制度,既要禁止那些不可预见的机会主义行为,又要为经济活动的运行提供激励机制。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经济关系,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关系中特定利益的集合点。一直以来,经济学赋予人以“经济人”的属性。“经济人”假说为了追求理论的完美,有意避开一些复杂的变量,从而使数学分析容易操作,理论分析更加严谨,逻辑性、严密性几乎无懈可击。然而这种假设形式使“经济人”演化成完全理性的最大化选择工具,这样做虽使数学化处理变得容易了,却使“经济人”更加非人化了,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的情况下更容易走向极端化。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指出了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1〕尽管有这一“疏忽”,现代经济学仍在着力于为制度变迁寻找理论支持。不过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是,他们在考虑制度问题时,分析的橱子里是空荡荡的,里面只有几个被视为无用了的标有“制度经济学”的旧盒子。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3〕由此可见,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人,而对人的分析应以人性为基础。
一、人性理论
人性,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关于人性的讨论多集中于人之所以区别动物或者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上,也有一些是从广义上定义的。休谟在他所写的《人性论》一书中,把人性归结为人的知性,而这种知性是动物所不具有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段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描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笔者认为,人性即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类区别于他物的特殊性,广义上泛指人的一切行为与特征。人的行为特征是指与人的行为相关的一切表现形式,比如人的情感、意志、生理、心理、伦理道德以及人际关系等等都可以表现出某种行为特征,因为它们都影响着人的行为。
1.人性的善恶
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西方对人性问题的讨论自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柏拉图曾指出“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4〕中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以神学统治哲学、以神性否定人性为基本特征的。到了近代,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对权力限制和监督的法治思想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仍旧沿袭并发展了性恶论的人性假设,以此作为制度设计的依据。新古典经济学里的“经济人”假说也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这种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虽然能较好地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也存在很多缺陷:①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②忽视人的能动作用;③极易导致人们片面地追求自我利益,从而引发利益矛盾和冲突。人性有其善的一面,而“性恶论”的人性假设则没有包含人性真谛的全部内涵,忽视了人们之间的个体差异,易导致人的自私、冷漠和相互不信任。
中国的制度设计是以性善论作为基础的。在中国历史上,人性论尽管多种多样,但总体上以性善论为主。三字经主张:“人之初,性本善。”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生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人们只要不断地扩充发展善端,就能成为圣人、君子。他还认为,国家法度的捍卫只能依靠有德的圣君贤臣,由于他们有德,所以能施仁政。董仲舒综合了孟子、荀子及韩非的人性论,既承认人性有善的一面,又承认人性有恶的一面,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性善论,所以在治国策上倡导德主刑辅。西汉以后,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性善论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性恶论。这种建立在性善论假设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能够崇尚社会道德风气,弘扬人的奉献精神和社会正气,能够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不可否认,这种建立在性善论假设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也存在着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某些不法利己行为的不设防和弱设防,缺少制度约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人的诚信意识的缺失、尔虞我诈、坑蒙拐骗、造假售假,增加了社会上违法乱纪的行为及其治理成本。第二、期望于当权者的仁政,对当权者缺乏权力制衡,结果导致当权者权力的滥用和权力垄断,形成特权阶层或特权集团下的集权统治。这样既加剧了社会的腐败,也容易产生“拍脑门”式的发号施令,使社会发展一旦误入歧途而难以纠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性善论并没有在经济学里找到立锥之地,其原因可能与主张性善论的中国在经济学领域的落后直接相关。
除了性恶论和性善论之外,人类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属性,比如中性论。这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2.人的类属性
人的类属性是多方面的,既有将人作为“类”这一整体所具有的类属性,也有建立在个体差异基础上的不同群体所具有的类属性,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刻画人性。
(1)“生物人”。具有和动物同样的属性,其行为受本能的驱动,能够自发地趋利避害。生物人所追求的是生理需求。
(2)“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遵循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规律,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吐故纳新、新陈代谢、优胜劣汰的规律与人类伴行。“自然人”时刻与自然环境相互交融,顺应自然规律则有益其发展,违背自然规律则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3)“经济人”。当代西方经济学将人视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假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泛经济人”阶段。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4)“社会人”。“社会人”假设的理论基础是人际关系学说,“社会人”又称为“社交人”。该假设最早来自于梅奥(G.E.Mayo)主持的霍桑实验,后经一些学者不断丰富。他们认为人是“社会人”,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受集体的制约。他们除了物质追求外,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爱、道德、归属感、荣誉感等。“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就是:①从根本上说,人是由社会需求而引起工作动机的,并且通过同事的关系而获得认同感。②工业革命与工业合作化的结果,使工作本身失去了意义,因此要从工作上的社会关系去寻求意义。③员工对同事们的社会影响力,比对管理者所给予的经济诱因控制更为重视。④员工的工作效率随着上司能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的程度而改变。
(5)“文化人”。这是“社会人”理念的进一步延伸。其主要特点是:强调人的知识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将人的本质属性提升为一种文化抽象。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高度主体性和自觉精神,不断学习、持续进步、自我超越的文化精神,使他们产生竞争和创新的欲望。“文化人”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默契合作,相互关心,相互尊重;在生产中要提升组织的文化精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6)“理想人”。他追求理想、信念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如对意识形态、宗教等的虔诚信仰者。
(7)“道德人”。追求道德至上并认真履行道德规范的人,当他们的利益与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道德,而不是利益。
在诸多的人性假设中,“经济人”假说在主流经济学里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它采用严密的数学推导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它的人性假设则相形见绌,没有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可。那么,我们一直所推崇的“经济人”假说真的完美无瑕吗?
3.“经济人”假说及其缺陷
“经济人”思想是重商主义者首先提出来的。如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海尔斯(John Hales)在1549年著的《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中,就已提出了“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看法。近代西方哲学家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人对“经济人”做了大量的论述。在经济学说史上,亚当·斯密可能是最早明确地把自利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确定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5〕“经济人”是斯密《国富论》理论体系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斯密经济思想的核心。在斯密看来,“经济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6〕
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所谓“经济人”就是在对经济行为者的许多不同描述中,“经济人”的称号通常是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具有理性的人的。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理性的经济行为者总是在寻求讨价还价,选择那些能够比其它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法国经济学家保罗·阿尔布(Paul Albou)将“经济人”的基本特点归纳为:
(1)“经济人”的行动只受个人利益的驱使;
(2)“经济人”只服从理性,他不会想入非非和心血来潮,他只想以最小的牺牲来满足自己最大的需要;
(3)“经济人”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笼统的人,是具有完全信息的人;
(4)“经济人”没有历史,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
(5)“经济人”完全是独立的和自由的,他独立于任何其他人,可以说是生活在孤岛上的鲁宾逊;
(6)“经济人”有三大主要哲学来源: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感觉主义。
“经济人”假设是一个在争论中逐步演化的假设。最初它可以称作是“自利人”假设,即强调经济主体的完全自利的行为目标或效用函数。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人”假设受到不少人(主要是美国早期经济学家凯里,德国历史学派的克尼斯、施莫勒、布伦塔诺,美国制度学派的凡勃伦等人)的指责,〔7〕其理由是人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自私自利的,而是也有利他的一面。总之,对于“自利人”的假设,通常存在着三种指责:一是认为该假设强调人们只追求物质利益的满足,忽视了对精神满足的追求;〔8〕二是认为该假设忽视了人们的利他主义行为;三是认为该假设是鼓吹和主张自私自利。针对这些指责,“经济人”假设逐渐修正和演化为“理性人”假设,强调经济主体总是追求其目标值或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至于这种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则不作具体的界定。“理性人”假设强调个人总是追求自身目标值的最大化,它涉及到个人的行为动机及其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许多人在使用这个假设时往往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认为个人的行为动机可以是利己也可以是利他的,是追求自身目标值的最大化;二是认为行为结果必定实现行为动机。这两种含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受到人们(主要是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赫伯特·西蒙、莱本斯坦等)的两点质疑:一是个人未必一定追求目标值的最大化,很可能只追求令自己满意的目标值;二是个人受有限理性的制约,很可能并不了解最大化的目标值究竟是多少,也很可能并不了解实现目标值的最佳方法是什么。〔9〕从逻辑上讲,基于引入效用概念这种当代经济学的扩展来说,“经济人”在主观上的利己也可能在行为的结果上利他,特别是在分析具体经济行为时则往往假设经济主体的目标或效用函数的自利性。所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最基本的含义是“理性人”,更常用的含义是“自利人”,只是其行为结果存在着利他的可能性,但这改变不了“经济人”主观目标的利己性宗旨。
“经济人”假说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古典“经济人”主要是由亚当·斯密建立的,认为“经济人”是有理性的,他在各种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己的最大利益,因而“经济人”是自利的。“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10〕“经济人”必须与道德相统一,并结合外在制度的强制以约束人的行为。“经济人”的利己性并非对社会有害,“经济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处于本义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1〕斯密以“经济人”作为其思想的立足点,以“自然秩序”作为其思想的出发点来推演自己的整个经济学体系。另外,边沁的功利主义也对“经济人”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按照边沁的定义:“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一种行为予以赞成和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功利原则的直接引申就是对行为的规定,内容有两点:其一,行为目的的规定——追求幸福;其二,行为对象的规定——追求那些能够产生幸福的外在物,也就是利益。边沁认为,功利原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是经验中的事实。古典“经济人”假说能够从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比较中来阐释“经济人”假说,对经济学学科的独立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没有具体的、历史的从人与制度的关系中分析“经济人”,在论证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中模糊不清,认为“经济人”的逐利行为在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即便这种事实存在,这种观点也没有在理论上阐述清楚。而“无形之手”定理也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人”之间、“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制约,从而对市场调节过程的描述存在着很多遗漏和缺陷。
新古典“经济人”假说是在古典“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人”假说抛弃了古典“经济人”假说中的制度因素(道德伦理)及主观心理因素,转向理性选择,并用偏好代替了自利。它只考虑经济因素,试图对“经济人”做出严格的数学和逻辑上的形式化证明。这一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杰文斯认为经济学如果要成为科学,必然且必须是一门数学性质的科学。帕累托认为经济学只需考虑“经济人”的最大化理性行为,而无须考虑其背后的心理欲望。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假设个人在他的全部经济关系中,完全只受一种开明的自利欲望所激励,而且凭利益所在而自由活动,只要不妨碍旁人的自由。由此得出“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人的结论,但绝非是主观的、随意的抽象。“经济人”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达到最大的财富,付出最小的劳动代价,而且仅就这一直接目的而言,我们才说他是完全只依自利行事的。〔12〕弗里德曼将新古典“经济人”模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不问欲望,只论效果的阶段。弗里德曼认为不要过多注意假设的好或坏,而要看在这一假设条件下得出结论的真与伪;由结论的真,反推假设的好,反之,就不是好的假设。为适应数学方法使经济学严格形式化的需要,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人”进行了理想化的假设,即假定“经济人”在诸多的选择方案中,总能找到一种最优的选择方案,能够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为保证这个假设能够实现,他们又进一步假定制度既定不变,人的需求偏好是单一、稳定和可计量的,人们面临的是一个资源稀缺、完全竞争、只有单一价格信号的市场环境。在这种确定、简单的环境里,产权可以得到无成本的界定,信息可以无成本的获得,交易是个无摩擦的过程。新古典“经济人”假说避开了一些复杂的变量,能够较容易地引入数学分析方法,理论严谨而周密,因此,在经济学中处于明显的中心地位。数学结晶体在数理逻辑上确实是无懈可击,但这一系列苛刻的假设条件把现实经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某些因素(如制度背景、规模经济、外部效应、不确定性等)排斥在分析范围之外,而这些变量对人的行为以及经济世界的影响是极大的。因而,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称新古典“经济人”假说为“脱离真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13〕。
“泛经济人”假说将“经济人”假说广泛应用于非经济领域,同时扩充了“经济人”的最大化目标,引入了非货币收入因素。这主要是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和次优理论,以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贝克尔的经济理论等。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由于受到信息、心理、生理和思维的限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准确地求得最优解;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不是最大化的追求者,而是要同真实世界的各种复杂事物发生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影响着“经济人”的决策。布坎南将“经济人”的分析方法拓展到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将“经济人”与制度联系起来。加里·贝克尔也拓展了“经济人”的空间范围,认为“经济人”之所以是经济的,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就是因为他是在对包括经济利益带来的效用和成本比较及道德、法律、伦理、心理感受等多方面的效用与损失比较的综合考虑后而做出某一行动或不行动的决策选择,因而可以肯定其行为是基于总效用最大化目标的,进而得出结论即现实中的“经济人”具有社会普遍性。在“泛经济人”假说中,经济学家们看到了社会制度对“经济人”偏好和动机形成的影响,把它作为内在因素纳入了经济分析之中。随之,个人利益的范围也被扩展到纯经济利益以外的名誉、地位、尊重等精神价值,从而使“经济人”假说变得更有说服力。“泛经济人”假说从不同的领域提出了人性的假设,反映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力求使人性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但是,它还是忽视了在制度等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人的精神追求的巨大作用,忽视了制度在控制人的物质追求、决定人们在各种利益之间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重大作用。他们只是妄想用纯经济成本分析法来囊括所有的精神价值,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泛经济人”假说缺乏说服力的根源所在。“泛经济人”假说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对新古典“经济人”的继承和发展,缺乏对“经济人”背后的历史和环境的考虑,更没有从制度的角度进行详尽的分析。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稀缺性”假设一起构成经济学主要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最基础的两块拱石,它们几乎遍及于经济学的所有分支领域。“经济人”假说的构建实际上应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剔除掉。现有的大量增长模型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掉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它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的动态变量。第二种方法是视制度的变迁为给定的。这种方法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重要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无关。因此,制度被视为外生变量。
虽然“经济人”已构成主流经济学的基石,但是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对“经济人”的批判及争论一直悬而未决。19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关于“经济人”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尤其是凡勃伦)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进行了批判,19世纪后期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展开了“经济人”之争。此后还有20世纪40-50年代关于“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争论,以及20世纪后半叶关于“理性行为”问题的争论。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分支越来越多,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经济人”假说不断地被修正和完善。Janet T.Landa,Xiao Tian Wang〔14〕分析了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决策受到生态、社会及制度的限制。他们认为在一个给定的决策任务的环境下,人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大脑认知的限制,还受到既定决策任务环境下行为策略与生态、社会及制度的适应性关系的限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人”的决策行为必然受到制度的约束和限制。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开始,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研究经济问题越来越注重人的行为。在研究人的行为中,贴现因子作为影响人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特别是laibson的双曲贴现因子(Hyperbolic discounting)备受关注。laibson〔15〕给出了双曲贴现因子模型,Palacios-Huerta〔16〕利用该模型讨论了消费和证券组合问题,Krusell和Smith〔17〕利用拟双曲贴现效用在Ramsey模型中研究了消费和储蓄问题。这种改变贴现因子的方法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自此,经济学逐渐侧重于从人们的偏好、禀赋方面研究经济决策。行为经济学修正了“经济人”是完全利己的这一假设,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的动机。类似的,实验经济学则通过诸多实验证实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行为,由此批判了理性“经济人”假说。信息经济学揭示了现实世界中的信息具有不充分和不对称的特征,直接摈弃了理性经济人拥有完全信息的假定,描述了经济行为主体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的情况下是如何进行经济活动的真实情景。
实际上,“经济人”最初的基本涵义就是人的利己性,如果按照这种理念则很难解释人的主观利他性。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社会生物学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的利他行为。以Herbert Gintis和Samuel Bowles等为代表的桑塔菲学派运用群体选择和演化博弈等理论解释了人的利他行为的演化,他们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最后通牒博弈(the ultimatum game),公用品博弈(the public goods game)等诸多实验研究证实了人的主观利他性,他们关注于合作与惩罚以及制度、文化与社会的共同演进。Gintis〔18〕,Henrich等〔19〕的实验研究揭示了无联系的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无法用“经济人”的利己性进行解释,他们把这种相互作用关系称为强互惠,它是一种超越或突破“经济人”假说的人类行为模式,即超越利已动机而导向利他的行为动机。他们认为个人愿意付出成本与他人合作并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则的人,而且这些个人并非指望付出的成本能够在将来得到回报。Henrich等〔20〕在世界范围内利用数百个实验,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对“经济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发现研究结果与建立在“经济人”自利性上的标准模型的预测是完全相反的。他们采用跨文化的研究方式在最后通牒博弈、公用品博弈以及独裁博弈中研究人的行为,通过不同社会的局部展示了世界领域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广泛不同。他们发现:①建立在自利性基础上的标准模型在所有社会的研究中都失败了。②在跨社会群体情况下,人的行为差异比以往的研究更加明显。③经济组织和社会结构中群体层面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跨社会的行为差异:社会市场化程度越高,日常生活中用于合作的支出成本也就越高。④可利用的个体层面上的经济和人口统计的差异不能完全一致性地解释群体内或群体间的博弈行为。⑤许多实验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遍联系方式。
可见,基于人的活动目的的复杂性和行为选择的多样性,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人们也不满足于仅仅从利己角度出发的“经济人”假说,而试图从多个角度给予人的不同行为以新的解释,从而期待新的理论的出现。这就告诉我们,对于人的复杂性来说,仅仅从自利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其他角度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有这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才可能是具有多样性的丰富的活生生的人。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在“经济人”假说赖以建立的深厚的经济学逻辑背景下,任何试图通过引进“效用”、“偏好”等概念来将“利他”理念强行塞进到经济学里的所谓拓展性研究,都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行为,直接违反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同一律,混淆了性恶论和性善论的逻辑起点,最终导致经济学内在逻辑的混乱,尽管他们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并做出了辛勤的努力。因为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经济人”假说只能将人的利己性作为逻辑的起点,而假定需要建立一个以同样具有存在合理性的性善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它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毋庸置疑,利己与利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价值理念与行为的出发点,如果硬性地将其二者放入一个逻辑体系中,设定二元的逻辑起点,只会引起逻辑矛盾,而于事无补。
其次,引进“效用”概念的解释仍然没有逃脱经济人对利己目标追求的阈限,只不过用“效用”代替“利己”,没有反映出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主观上利他的动机。严格地说,效用概念的引进并没有走向“中性”,只是把主观上的利他篡改成主观上的利己,并没有得出人也有利他动机和行为的客观假设。事实上,人类有3种行为。其一是基于生物本能的利己行为;其二是具有利他动机的利他行为。前者属于生物的类本能,后者完全超越了类本能意识,达到了精神层面的理性升华。其三是在制度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利益中性”的行为选择。该行为主观动机中不存在利己和利他的主观故意,“规则”既是其行为的出发点,也是其行为的落脚点。即完全彻底的制度主义者,宗教主义者就是例证。因此,从利益的角度看,利他、利己、价值中性这些人类行为的动机都是客观存在的。可是,作为经济学扩展出来的效用概念,却试图把人类主观上的利他动机变成了“追求效用的利己动机”,把利他行为变成了追求效用的利己行为,从而磨灭了人性中存在的崇高与伟大光辉的一面。不可否认,把自利的经济人作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人类社会日益成熟和发展进步的过程中,随着生物人→知性人→理性人的社会进化和精神升华,行为决策中的本能意识逐渐消减,为社会理性所代替,超越于利益关系的利他主义与价值中性原则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向主流经济学发起挑战。在正义与科学的殿堂里,摆在我们经济学人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接受和包容利他主义与价值中性原则并能够将利己和利他同时融合在一个范畴之中的、逻辑上具有自洽性的经济学体系,而不能在一个利己型经济学体系内搞多元化矛盾。除此而外,别无他途。
二、“制度人”假说的提出
在“制度人”假说提出之前,我们先探讨一下制度的含义。凡勃伦认为,制度根源于人们的思想和习惯,所以制度归根结底是受本能支配的。但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类行为产生约束力,并且制度也会在人的生存竞争中不断演化。康芒斯将制度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21〕而诺思认为“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对各种组织的行为产生一般的限制,同时也给各种组织带来机会并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舒尔茨关于制度的观点与诺思基本一致,〔22〕他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青木昌彦把制度定义为均衡导向的(the equilibrium-oriented)或是内生的博弈规则。我们认为制度是规范和约束(激励)人的行为的规则。它以三种形式存在着:一是在人们思想观念形态上存在的规则,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伦理观念等;二是形成文字的各种规则和契约;三是各种风俗、习惯等约定俗成的隐形规则或潜规则。
影响人的行为选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种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宗教信仰。这在西方一些宗教信仰较强的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利益驱动。这是“经济人”假说建立的基础,因为“经济人”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形成经济人机制;三是制度约束(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即行为选择遵循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以循规蹈矩为满足,从而形成制度人机制。受利益驱动的影响,人们会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要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就需要宗教信仰和制度的约束。而在宗教信仰缺失的国度,制度就极为重要了。
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等制度安排会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有效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不仅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即“制度决定论”。诺思之前的西方经济学家主要将某些生产要素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却被排除在外,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诺思于1968年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各方面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尽管这一阶段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海洋运输生产率却大大提高了。原因何在?主要是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他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制度变迁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呢?对此,诺思分析了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构造了一个制度需求分析框架:在现有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会应运而生,并使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诺思认为,经济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创新是因为在社会中的个人或集体看到了承担这些变迁的成本是有利可图的,其目的在于创新者能获取一些在旧的制度安排下不可能得到的利润,从而使得一项制度(或一种产品)贴现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的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纳入其分析框架中。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理论必须包含三大理论柱石:(1)描述一个体制中个人和集团激励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做出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3〕
制度何以决定经济增长?如何使个人的努力达到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水平呢?这就在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即对人的激励,包括正激励和负激励。好的制度对人有正激励的作用,能够使坏人做好事,制度富有效率;不好的制度对人具有负激励的作用,使好人做坏事,制度处于低效率。对于制度的研究,离不开人,人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制度脱离了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经济人”假设由于忽视了制度分析这一视角,没有找到人与制度互动的真正机理,从而始终没有找到良好社会秩序形成的密钥,不能对现实给予全面的合理解释。人的行为是复杂多变的,人性的假设应该符合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人的行为。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治高于法治的国度里,对人的研究更加重要。严格来说,作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置身于制度中的活生生的人。因此,制度与人,谁也离不开谁。制度是与人相联系的制度,人是生活在制度空间里的人,二者融为一个整体。特别是当人治高于法治时,制度的作用是因人而异的,离开具体的人的制度实际上沦为“摆设”。即使在法治社会里,制度的设计也要以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规则的关系。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揭示了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但却没有将这种研究深入下去,仅仅停留在抽象层面上。人类在合规律、合规则的自然改造过程中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突破旧有制度下路径依赖的桎梏,推动着制度的变迁。
有鉴于此,面对长期的经验积累,经过严谨的思考和逻辑推理,笔者提出“制度人”假说。“制度人”总是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中,以追求制度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行为方式以合乎规则为出发点,体现为一种循规蹈矩的追求制度效用的满足,达到人与制度合一的均衡状态——“制度人”。它是人与制度交互影响的产物,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所谓制度效用最大化是指在复杂的制度结构中,当修改或增加任何一种制度安排时,都不能使行为人获得额外的满足,此时制度供求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均衡点,该均衡点给循规蹈矩的人带来最大的效用。也就是说,“制度人”出于对制度的敬仰和畏惧,在“合乎规则”这一理念与其他行为理念(如源于类本能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断发生碰撞的过程中,基于人性、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作用,逐渐战胜了类本能,摒弃了利益机制,经过人性的长期修炼,逐渐成为一些人的行为选择。久而久之,人们的思维及其行为模式便形成一种惯性,逐渐沉淀为一种潜在模式,对人的思维及其行为起到了某种固化作用,最终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面对极为复杂多样的人类群体类型,“制度人”假说不否认有的人类群体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但也同时承认某一群体(如虔诚的宗教信仰者、高尚的道德追求者)或某一个体在特定的时空点上存在着追求制度效用最大化的一面。即使“制度人”在追求制度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也未必导致利益最大化,甚至存在不问利益只求遵循规则的满足。历史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中确有一类人崇尚制度与伦理,终生追求制度效用的满足,但也不排除有一种人虽然在其生命大多数时点上表现为一个十足的“经济人”,仅仅在其生命的某一时空点上成为追求制度效用满足的“制度人”。可见,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具有多面性的矛盾体。因此可以说,“制度人”不仅是指一个特殊的群体及其特征,而且也是一类个体在其生命某一时空点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现象。“制度人”在长期的社会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社会契约”型的思维模式,崇尚超越于利益诉求的中性价值理念,需求结构达到了人类价值理念的升华。在人类社会最崇高的价值理念的主导下,“制度人”既受到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又不断设计、修正和完善着制度,从而促进了制度的文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升华。这类制度人属于崇尚理念型,他所获得的制度效用是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自我完善、自我演进、自我进化的机制作用下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的。还有一类制度人属于低成本型。他们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喜欢简单、平淡、朴实的风格和生活模式,不愿意过“精于心计,精于算计”的费力人生,更不愿意去“折腾”。对于他们来说,照章办事,循规蹈矩,一切按照制度规定行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确实是一种最简单、最省力、最平和的生活模式。该种类型的制度人所获得的制度效用是成本最小化、生活简单化、人际原始化。
“制度人”假说与“经济人”假说究竟有何区别?第一,“制度人”假说增加了利益中性这一分析视角,弥补了“经济人”假说对于多样性人类群体行为分析的遗漏,从而使经济学理论分析回归现实。第二,“制度人”假说建立在利益中性行为理念的基础上,而“经济人”假说则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之上。第三,“制度人”假说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而“经济人”假说则将制度作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或将制度剔除。第四,“制度人”追求的是规则,以制度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其行为方式长期受惯性的影响而逐渐固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只要按规则办事就得到了满足;而“经济人”追求的是利益,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行为方式是否依据规则,则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因此,制度至上还是利益至上,这是两种假说的本质区别。第五,“制度人”很少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受制度约束的作用较大,因此能够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而“经济人”存在很多机会主义行为,其逐利行为往往会冲破制度的限制,因而会加大社会管理成本。特别是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制度往往沦为权力意志的玩物,形同虚设,导致社会维系成本过高。第六,“制度人”在追求制度效用时可能获得利益,但这只是该行为的“副产品”,同时也未必能够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可以推导出“制度人”在遵循制度规范的情况下,其行为方式会产生四种结果:(1)利益最大化;(2)利益次优化;(3)收益为零;(4)利益受损。人的需要有多层次,我们通过观察发现,人们并非总是追求利益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或基于某种理念,或基于对制度的笃信,或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只要得到此类满足,就不再介意利益是否受损。比较而言,“制度人”比“经济人”拥有更高的追求目标和思想境界,因而社会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制度人”假说构建的目的是创造合理的制度体系,科学规范人的行为,优化制度结构,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为更加合理地解释人的所有行为提供一种新的逻辑。当然,“制度人”假说的建立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制度应该是正确合理的制度。
“制度人”具备以下特征:
(1)“制度人”作为主体创造并修正和完善着制度,作为客体又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人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行事,人与制度是互动的,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体现着制度演进中人的行为选择以及对世界的改变。正是缘于人与制度的互动机制才推动着制度变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2)“制度人”把追求制度效用列为第一要义。由于“制度人”以追求规则为出发点,当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制度最富有效率,交易成本也最低,制度效用满足的程度也是最高的。
(3)“制度人”的行为方式受惯例的影响而容易产生某种路径依赖。“制度人”在长期的潜规则影响下,一旦形成某种行为习惯则难以改变,导致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存在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良性的,表现为积极上进的行为方式;一种是惰(恶)性的,表现为消极堕落、不思进取的行为方式。这取决于制度路径的优劣与好坏。
(4)“制度人”的偏好和禀赋是影响其行为的内生变量。制度通过激励与约束影响人的需求和欲望,进而影响人的选择。人的需求结构和动机结构的结合形成人的偏好结构。制度对人的偏好具有塑造的功能,人的行为选择又受到偏好的直接影响。
(5)“制度人”的行为过程是个体偏好与制度博弈的结果。制度影响着人的个体偏好结构,而人受个体偏好结构的影响又修订或变更着制度。
(6)“制度人”不仅遵循正式规则的安排,同时也按照一定的“潜规则”行事,这种“潜规则”被称为“个体行动法则”(law of individual action)。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实践和研究的深入以及新的教育思想的渗透,大量基于技术的教育教学模式不断涌现,现代教育技术成为现代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4]。
那么,什么是“个体行动法则”呢?现实社会中的人并非单纯按照“经济人”的方式行动,而是在制度、生理反应、环境甄别、个体偏好的博弈均衡中做出行为选择。“个体行动”(individual action)是制度(institutions)、生理系统(physiological system)、环境辨识(environment recognition)及个体偏好结构(individual preferences structure)的函数。其中制度是核心变量,对人的行为起主要作用,其它三个方面是辅助变量,对人的行为起次要作用。在这里,制度又是时间的函数,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演进,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IA代表个体行动,I、Ps、Er、Ip、t分别代表制度、生理系统、环境辨识、个体偏好结构及时间。这些要素是如何影响“制度人”的行为呢?
1.制度。Hodgson认为制度对人的潜规则的影响体现在与信息相关的认知性功能上。这种认知性功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制度能够为个体提供信息,包括其他人可能行动的征兆,从而使个人做出相应的策略性行动。其次,制度的认知作用也包括对人的悟性的影响,即人们如何选择信息并解释信息。再次,制度对人的行为的诱导作用。制度以其限制性的规范诱导人们的行为目标。对于制度与信息有关的认知作用,Demsetz,Schotter,Langlois,Knight和 Kiwit都做过一定的研究。诺思认为制度的认知功能与制度的限制性功能有一定的联系。Knight在研究人类文化学过程中提出社会制度对人的认知包括两种机制:一是社会文化的影响作用,另一个是文化、社会环境及历史的交融性的影响作用。Streit等认为制度不仅可以加速人的认知过程,更重要的是,制度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领悟。他们提出人脑创造解释环境的认知模型,这些认知模型像过滤器一样筛选信息,同时受接收到的信号刺激的影响,人脑的认知模型乃至于人的脑神经元系统会发生相应变化,进而影响人的悟性。Clark认为语言文字和社会经济制度是人的外在行为结构的一部分。Denzau和诺思提出一个文化上共有的精神模型对于人们学习过程的重要性,这个文化领域共有的精神模型能够加速人们直接地从经验中获得认知,促进人们之间的交往,并且将这种从经验交往中获得的认知世代传承。Williamson在强调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了准则、风俗、传统等对认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认知功能最终影响着人的偏好及环境辨识,也对人脑的认知模型产生一定的影响。
制度影响人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制度的共用品特征(Public Goods)。共用品是指整个社会可以共同享用而不必付费的物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共道路和公共卫生等。共用品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二是利益上的非排他性。共用品包括纯粹的共用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及俱乐部物品(具有排斥性而不具有竞争性)。制度的共用品特征缘于制度的普适性。人人可以利用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反对那些违背制度或破坏制度的人,以渴求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制度的共用品特征又经常被机会主义者所利用,出现“搭便车”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制度下的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况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下社员的“磨洋工”行为都是“搭便车”的典型。好的制度对人起到激励作用,能够有效地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好的制度恰恰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往往随时间而改变,即存在着“制度悖论”。在成熟的制度下,行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遵守制度规范是一种常态,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和国家制度规范相一致,这就符合了激励相容原理;在不成熟的制度下,行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往往违背制度规范,破坏制度成为一种常态,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与国家制度规范不一致,往往呈现出激励不相容的现象。我国做官、经商都有其不符合制度常态的潜规则,循规蹈矩反成为迂腐的表现。
2.生理系统(脑神经元系统)。随着近年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发现人的行为偏好受到人的生理系统的影响,其中受脑神经元系统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大脑存在一个分区叫做信息集结区,如果把大脑皮质去掉,那么就是中脑系统,它是负责情感记忆、情绪波动和一些本能的反应。中脑系统再下来就是脑干系统。中脑和大脑皮质之间有一个中介神经元构成的圆圈,这个区域叫做ADC,它是目前一部分脑科学家认为的自我意识的发源地。当情绪冲动时通常人们认为是非理性的,但后来发现情绪波动的时候控制情绪的神经在中脑和脑干之间,它发出的信号一直到ADC,然后ADC控制人,一些科学家由此推论理性和情感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分开。贝彻拉(Bechara et al)等人通过实验观察到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是认知和情感一起决定行为的。
3.环境辨识能力。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人对环境的辨识源于人的理性、知识、信息及经验。人可能因缺乏知识经验和信息而同时追求互相冲突的几个目标,从而导致人的非理性的存在。人所处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不同的人对环境的辨识能力是不同的。西蒙认为,建立在对现实的主观感知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决定人类选择的重要因素。西蒙通过引入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完备性来分析人类行为。在《可预期行为的诸种起源》一文中,罗纳德·海纳(Ronald Heiner)指出:存在于代理人辨识问题的能力与选择最佳方案的困难之间的差距,即CD差距(CD gap)是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CD差距越大,则代理人越有可能采用常规性的且十分局限的模式来应对与这种差距相联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海纳指出,事实上,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产生了可预期行为,而且还是制度的根本来源。人的理性反映在个体行为与集体策略的博弈中。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其他人的选择。在群体策略中,理性难以成为共识。
个人的认知能力与知识积累有关。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制于知识的限制。表现在:(1)关于未来,人们只有不确定的知识(未来的不确定性),但他们必须猜测未来以便行动。人们喜欢获得减少不确定性和鼓舞信息的帮助;(2)人们在了解资源、潜在交易伙伴以及它们的精确特征上具有“横向不确定性”。特别是当人们需要让别人为他们做事时,他们常常不清楚那些代理人究竟是忠诚、可靠、尽其所能,还是玩忽职守。〔24〕由于环境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个人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有限能力,个人在制定决策时所依据的一般知识和具体知识的存量都不可能是足够的,而是有限的。个人的知识水平及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其认知水平,因而也极易产生认知障碍。有时候,人的理性容易被情绪所替代,产生了我们称其为情绪对理性的“替代效应”。在情绪替代理性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往往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人们在风险条件下的决策,经济学家有两种观点:一类是坚持传统的偏好选择法,认为应当推广期望偏好,以发现适应实证数据的、可以作为个人特征的、独立于选择环境的偏好;另一类认为偏好不是一种个人特征,而是由更基本的因素在不同的环境下构造出来的、能够反映环境特征的产物。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着缺陷。观点一无法解释偏好逆转等现象,观点二缺乏实证研究的分析基础。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人们在实验室中观察到的数据。这种解释充分考虑了实验室的特殊环境,其理论通常被冠以“被发现的偏好”。普洛特坚持认为人们具有一个不随环境等因素改变的、可以以之作为个人特征的偏好。但是这些偏好对于当事人本身而言可能并不清楚。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后,人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偏好。在普洛特看来,偏好不是构建的,而是有待发现的。这个发现过程完全不同于偏好的演化过程,偏好本身并不变化,只是有待发现而已。〔26〕这二者的关系也许是相互补充的。
三、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形态
目前,人类社会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
1.以暴力等高压手段为特征的压力型社会治理模式。该治理模式强调通过强制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重点在于依靠强力对社会实施管控,它建立的是以统治者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该治理模式表现为“我命令,你服从”。一般来说,这种治理模式较为原始、简单、粗暴,既无人文色彩,也无科学与理智的含量,操作简单易行,实为人类本能中“恶”的显露。人类社会初级形态或不成熟的社会特别是集权社会往往采取该治理模式。因此,这是判断人类社会是否文明和发达的主要特征。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对人具有负激励性,使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抑制创新,因而无论多么富有,社会福利制度多么完善,人们心里总是感到不满意。特别是当人们的不满、怨恨达到临界点而无法疏导、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时,便意味着以暴力等高压手段为特征的压力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终结。因而,以暴力等高压手段为特征的压力型社会治理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为它的社会成本最高,任何社会都无法长期承受下去。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至今尚无一例靠暴力统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2.权威型社会治理模式。该治理模式主要是基于心理、思想、价值理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通过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一般会把社会治理引向道德自律、英雄崇拜或宗教信仰的方向。这种治理模式表现为精神或意识形态统治,无论社会制度是否合理,亦能使人们臣服于某种思想理念或宗教信仰而长期维持社会统治。这种治理模式易形成错误的初始制度设计而使制度变迁处于恶性的制度依赖过程中。一般来说,这种社会治理成本较低,但容易产生畸形的社会发展模式。
3.激励型社会治理模式。在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治理结构中,激励型治理模式显然属于胡萝卜类型。它对人具有正激励性,符合人性特点,因而容易激发社会正效应,提升社会正能量。然而,由于资源总是有限的,激励的手段、范围、程度总是要受到各种限制,加之人们的愿望虽说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常常满足于“小富即安”、“安贫乐道”,即不再追求收益最大化,而是满意的收益。因而激励对于人的行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逐渐满足和不断递进,以满足低层次需求制度的激励效应会失去作用,而最高层次的需求则对多数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
4.制度型社会治理模式。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该治理模式。这是在一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自我利益的社会演进与治理逻辑。在该社会治理模式下,利益仍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制度仅仅是规范人们追求利益行为的工具,用来规范和限制人们的越轨行为,调节人们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旦目标和制度发生冲突,人们就会面临着是通过修改制度来满足对目标的追求,还是放弃目标而保留制度的选择。因而,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不稳定的,经常处于利益碰撞和冲突之中。
5.“制度人”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利益中性。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利益目标,而是制度目标,只需按照制度去做,不问收益如何。当然,其前提是一个社会的制度设计必须是合理的,制度合理的根本标志是制度收益均衡化,即只要按照制度规范行事,每个人都会取得合理的收益,否则就不具有可持续性。该模式的最大优势是诉诸暴力被诉诸制度所代替,大家都信奉同一价值理念,遵守共同制定的规则,因而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具有稳定性,社会治理成本最低,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
四、结束语——本文的贡献:价值与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不是用制度人假说来代替“经济人假说”,而仅仅是承认在极其复杂而又呈现出多样性的人类各种群体面前,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以及不同类型的行为,这两种假说都能够找到其适用的特定群体和特定行为,都能够有效地解释特定群体的特定行为,因而他们都有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进一步说,他们的存在对于解释不同人类群体的行为差异具有互补性,从而增加了研究的视角和经济理论的丰度。
“制度人”假说的提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一是实现了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对制度的研究的有机统一,将附着在“制度人”身上的制度作为内生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变量,克服了经济人仅具有外部约束的狭隘性,使经济学的研究真正回归现实,而以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存在着一种把制度加以剥离或抽象化的弊端,隔离了人与制度的内在联系。二是提出了“个体行动法则”,并认为“个体行动”是制度、生理系统、环境辨识、个体偏好结构的函数,从而深化了对人类行为的认识。三是从“制度人”的视角阐述了制度与人的互动机理,将人的行为选择与制度的设计有机地统一起来。四是给出了人类行为和社会治理模式多样性一种全新的解释。毋庸置疑,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超越于人们利益之上的行为和动机,即行为中性。完全基于规则来决定行为,属于制度理性,无论其个人成本还是社会成本都是最低的,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是制度合理。越是成熟的社会,制度理性就越强。五是对经济学中利他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从而真正解决了“斯密问题”的争端,弥补了以往经济学通过效用概念对利他行为的解释而无视人们主观上存在利他动机的缺陷。斯密曾在《国民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凡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无不心怀“自利的打算”,即“经济人”是利己的。同时,斯密又在《道德情操论》一文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认为“同情心”是利他行为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这个悖论引发了“斯密问题”。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这种客观存在的利他行为如果用“制度人”来解释,就显得合情合理。由于“制度人”把遵循制度规范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利益中性价值理念的作用机制下,其行为方式必然受到规则、道德、习俗、惯例等因素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利他性。总而言之,“制度人”假说进一步明确了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扩展了经济学的理论空间,弥补了当代经济学理论解释的不足。
从总体上比较而言,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更愿意遵守规则,更接近于“制度人”类型。在战争政策的主导下,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毁灭了这两个国家;而在和平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下,这两个民族又很快居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前列。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强盛,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更需要严格遵循制度规则的行为模式。
此外,制度人假说还为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基点。为什么有了制度,人们却不按规则行事,盛行潜规则,喜欢“闯红灯”,“人治模式”依然我行我素?众所周知,由于人们在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某些缺陷,仅仅依靠利益机制则产生严重的机会主义和社会问题,导致我国目前社会问题乃至暴力事件不断。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宗教色彩并不浓厚的国度里,有必要建立起“制度人”机制,将制度规范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从小培养人们的“制度人”理念,弥补建立在“经济人”基础上的人治模式的缺陷。
建立在“制度人”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经济人需要精于算计,权衡利弊,活得累,成本高。而制度人只需按规则行事,超越于利益得失,由此节约了信息费用和思考与计算的成本,消除了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
总之,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制度是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终根源。因而本文预言,未来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取决于制度文明的实现程度,而制度文明实现的程度又取决于“经济人”向“制度人”转化的程度。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成为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阶梯。
注释:
〔1〕〔22〕〔美〕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于〔美〕科斯、〔美〕阿尔钦、〔美〕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2-253页。
〔2〕〔美〕R·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225页。
〔3〕〔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页。
〔4〕〔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6页。
〔5〕程保平:《斯密“经济人”假定思路及其给予我们的启示》,《经济评论(武汉)》1998年第4期。
〔6〕〔1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90-213页。
〔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8〕郑也夫:《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之批判》,《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9〕徐清安、高洁:《经济人行为悖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1期。
〔10〕〔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2页。
〔12〕〔美〕J.N.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0年,第78页。
〔13〕〔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科斯:制度经济学家和制度建设者》,载于〔美〕科斯等著:《制度、契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14〕Janet T.Landa,Xiao Tian Wang(2001)Bounded rationality of Economic Man:Decision making under ecological,social,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s,Journal of Bioeconomics,3,pp.217-235.
〔15〕Laibson,David(2001)A cue-theory of consump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6,pp.81-119.
〔16〕Palacios-Huerta(2001)Consumption and portfolio rules under hyperbolic discounting,Working Paper,Brown University.
〔17〕Krusell,Per& Smith Jr.,Anthony A,(2001)Consumption-savings decisions with quasi-geometric discounting,Econometrica,71,pp.365-377.
〔18〕Gintis,H.(2000)Strong reciprocity and human sociality,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6,pp.169-179.
〔19〕Henrich,J.,Boyd,R.,Bowles,S.,Camerer,C.,Fehr,E.,Gintis,H.,& McElrcath,R.(2001)Cooperation,reciprocity and punishment in fifteen small-scale socie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pp.73-78.
〔20〕Henrich et al.(2005)“Economic man”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ll-scale societies,Behavioral and Briain Sciences,28,pp.795-855.
〔21〕〔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9页。
〔2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页。
〔24〕〔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52、64页。
〔25〕〔德〕石里克:《伦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页。
〔26〕刘凤良等:《行为经济学——理论与扩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92、97页。
猜你喜欢
杂志排行
学术界的其它文章
- 儒家文化命运辨析——全球化时代几种儒家文化归宿理论的实证检验
-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双重风险〔*〕
-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of Semiotics and Ecological Aesthetics
- On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Silo in the E-government Construction in China
- Primary Sources of Job Burnout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 New Interpretation on Old Turkic Writ from Tun - huang 17th C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