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笼
2015-12-15王雄
王 雄
背笼
王 雄

王雄,1982年出生于三峡江畔,2000年因三峡大坝蓄水,移民搬迁至沙洋县沙洋镇。体验了从峡江到平原的地理落差、生活习惯后,提笔写了许多围绕“峡江”和“平原”的散文和歌词。有作品发表于国家、省市级报刊;亦有作品获奖。系沙洋县作协会员,自由职业者。

父亲那一代人,都是用背笼来搬运东西的。
说起这背笼也有好几种称谓,每一种称谓都对应着相应的类型:背篼是一种有着很大一个“篼”的背笼,可以直接将东西放在“篼”里,一般装一些较轻的东西,或者逢年过节的鞭炮礼品,出门、走亲戚比较方便;背篓是一种编织得比较苗条一点的背笼,有的会在其腰部涂上彩色的颜料或者描上图案,应该说是一款比较女性化的用品。其中的一项功能在歌曲《小背篓》里,唱得人人皆知。当然也让相当一部分人对“吊脚楼”充满了向往;真正意义上的背笼,是男人专用的。这专用品又分为两种:一种背笼口比较大,用来在上面放上竹筐,竹筐容积比较大,能装载的东西也就比较多。此背笼被称为“大背笼”;一种背笼口比较小,一般用来背麻袋或者箱装的东西。此背笼被称为“脚背笼”。
还有一种背笼不是用竹篾编制的,是由两根“Y”形的木方平行的连接起来,再由两根竹篾编织的背带组装完成的。这种背笼被称为“杈背”,主要用来背牛草、猪草等可以直接放入其“杈”中的东西。它比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背笼都要轻便的多。只是与背笼有点擦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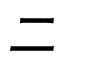
父亲是祖传的篾匠,尤其擅长织背笼。在农闲的时候,他经常用一个背笼背着一个长方形的工具篮,为村里人上门织背笼。他织得很慢很仔细,织出来的东西很耐用很好看,很多人都慕名前来请他。
也有人的背笼坏了拿到家里来,请父亲修整的。修整的最多的是背带。背带的编织是门技术活。从选料到编织每一项都不能马虎。父亲通常是换一副背带要花上半天光阴。人家满意了都不行,非得他自己满意才行。
还有男人背笼的戕坏了的,父亲会把坏了的用钳子费劲地抽出来,仔细地看看原本的戕是何质地,厚度,长度等等,为而后的替换工作做准备。
父亲用来换戕的工具像一片细长细长的叶子,中间拱起来,把手与“叶片”垂直成90度。换戕的过程父亲一直都是大汗淋漓。更不用说织新背笼上新戕了。一个结实牢固的背笼通常是横戕竖戕里戕外戕,把所有的席篾都膨胀到百分百。席篾与戕的相互交融,还需要桐油的点滴润滑。
这点滴之中有父亲汗水的融入。

在我的记忆里,乡村的男人们几乎是天天背笼不离身:忙种的时候,大筐大筐的农家肥往地里背,种子、工具等等,每一样都在背笼之上被搬来运去;忙收的时候,大捆大捆的稻穗被背到稻场,成熟的瓜果也一样靠背笼输送。闲的时候,男人们卖苦力挣钱补贴家用、供孩子上学。所谓苦力无非是为供销社或者私人老板,把东西从船上背到他们指定的地方。这些东西涉及的方面很广,几乎无所不包。
卖苦力的男人们除了要有一个好背笼外,还要有一个好的让背笼停歇的工具。这工具乡亲们都叫它“打驻子”。其实就是一根“T”形的木头做成的。根据人的身高,背笼的长度,“打驻子”的高度也不一样。
当男人们觉得肩上的负担有点让自己吃力了,就用“打驻子”的横面去支撑背笼的底部,让自己的肩膀得到暂时的休息。当然不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用来当拐杖,以减轻身体的压力。但百分之九十的男人不会有这样的举动,他们有劲,不怕压力。

父亲曾给我量身订做了一个背笼,那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为了背生活用品和书籍到很远的镇上住读。那个背笼我用了一学期就换成了背包,一是怕人笑话,二是学校的宿舍没有地方放。后来被父亲送了人。
我和妹妹的学业让家里没有太多的零花钱,有时候学费都成问题。于是瘦弱的母亲也加入到卖苦力的行业中。她通常是把船上的货物背到码头屯起来,等屯到估计一天能够背完才收手,再慢慢从码头往上背。她屯的货是她的,没有人跟她争着背。经常是别人一两个小时背完了回家,她却要背一整天。老板等着她最后一个结算工钱,然后关门。
我偶尔会帮母亲背她背不完的东西。她总是把我背的那部分钱给我,不然就是给我买几袋子方便面,回到家里煮给我吃,当然还会加两个鸡蛋。那是我吃到的最美味的方便面。
在我帮母亲背东西的时候,乡亲们会说我长大了,还有一句我今生都不会忘记的话: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力气去了能再来。
现在迁了居,远离了背笼,远离了苦力,母亲偶尔会对我说:想想以前靠苦力供你们兄妹上学,看看现在,就知足吧!
或许只有到了母亲这个年纪,我方能体会什么是苦尽甘来。只是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我是否有足够的经历可以珍惜。

父辈们的清贫、朴素让他们与人相处起来显得简单、热情,没有太多的心眼。卖苦力的时候想着背完东西换来的钱,可以度过暂时的难关。在背负重物前行的过程中,想着坚持就是胜利。在这些都得以完成,稍稍空闲之时,他们放下背笼坐在上面,玩玩纸牌,输赢不过是几支纸烟而已。
当他们挥动衣袖,重新背起背笼各自散开之后,谁又会记得彼时谁在谁的对面,谁又白抽了几支烟。
父亲的不善言语,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他没有生活的目标。后来父亲的一位友人的话让我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他说:其实最重要的目标是做好眼前的事。你父亲脑筋有点笨,但他认真,对手上做的每一件事都认真,他不和别人多说是怕分了神,影响了手上的工作。
也许这就是朋友与儿子的区别。

童年的时候,经常有人找父亲帮忙,帮忙背石头、背沙背水泥盖平房。父亲总是很乐意帮忙,在他眼里盖平房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峡江盖房子讲究看风水,依山傍水是第一要素,所有的原材料都靠背,人力很是关键。经常是几十号人上上下下的忙碌。赶上夏天,中午时节各人睡在各人的背笼上一字排开,很是壮观。几十号人几十个背笼,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乱丢乱放而搞不清自己的背笼。每一个背笼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记号。
闲暇之余几十号人三三两两的谈起自己背笼是谁谁织的,在哪砍得竹,都用它背过什么,用了多久,坏了几次,谁给修的等等。
谁说一个个背笼不是一个个故事呢。
父亲给乡亲们帮忙盖了很多平房,自己却因为搬迁没轮得上乡亲们给他帮忙盖平房。倒是有位父亲的友人在搬迁之后来家小住一段,帮父亲犁了很多地,临走的时候说:平原的地就是比山区的好犁。房子也比山区的高。
我知道他是从心眼里为父亲的迁居,感到高兴。

刚刚移居平原的时候,父亲用背笼背过土、背过红薯、背过秧苗,他不怕平原人笑话。他继续着峡江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他知道眼前的目标是,挪了一个地方得先活着,方式并不重要。
后来他学会了骑自行车,再后来学会了骑三轮车,并用它们运输东西。这时他的目标是活下去。再后来他学会了骑电动三轮车,省了力气还拖得更多。我知道他现在想的是好好活着。
这期间他始终喂养一头牛,用它来拉板车、给自己家耕地,也给人家耕地。在峡江给人织背笼、卖苦力的运作方式,到了平原换成了给人耕地、种植。他把峡江的“人背”转化成平原的“牛背”。转化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充实的过程。
而这种充实越来越背不起他的年龄之重。

如今的家里已经看不见背笼,而峡江的背笼时代不知道还会维系多久。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峡江,熟悉的或将变得陌生。但与背有关的方方面面,似乎已成为我心头的烙印。
故乡没有名山,但故乡的山,一点也不比所谓的名山矮小。童年的我到山顶是一气呵成,中间没有停顿。而今爬名山走不了几步就开始喘气,加上肩上的背包,没有儿时乡亲们鼓励的话语,没有眼前母亲卖苦力时的坚韧场景,没有十七岁以前的山区生活经历,没有发自内心的坚持就是胜利信念,我恐怕也要选择在半山腰,坐两人抬的轿子到山顶了。但越是看到抬轿子的轿夫我越怕想到了我的父母,想到我童年里与背笼有关的点点滴滴。
没有什么比坚持更可贵。

父亲的篾织工具被他用一个木箱锁起来,尘封。但偶尔也会拿出来用用,比如他把喷雾器的背带换成了背笼上用的背带。为此可以忙活一整天,看了改,改了看。我宁可绕道而行,也不去打扰他,我怕打断他。打断他的灵感,打断他的回忆,打断他的……
背笼在我们这个整体迁移而后又整体新建的村庄,慢慢消失。偶尔会看到一两个戴着草帽背着“杈背”骑着自行车的村民,迎着朝阳去向田间地头,回忆向潮涌一样奔来。
我的峡江方言在不知不觉中被平原话语同化,若干年后我操着自己也说不清是哪的方言跟人说起:我曾经背着背笼下过苦力。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相信。
在网上与友人说起此事,友人说:信与不信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总不是背着生活的重担在奋力前行!
是呀,我们背上都有一个无形的背笼,坚持得越久,胜利的过程越耐人寻味。
责任编辑:郑 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