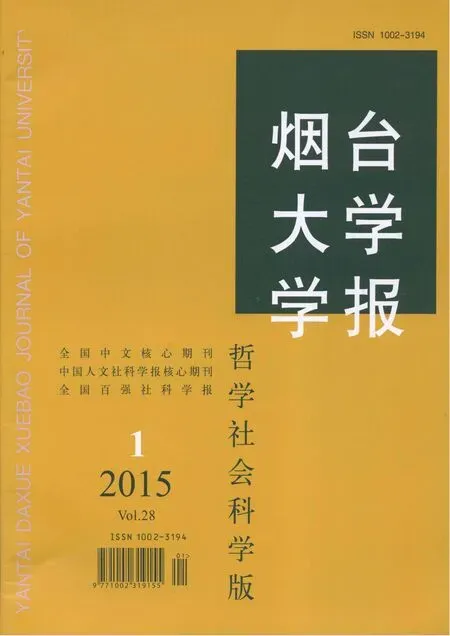庄、孟“辟杨墨”新探
——兼论儒道身体观之差异
2015-12-09石超
石 超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庄、孟“辟杨墨”新探
——兼论儒道身体观之差异
石 超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意识性取向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始终以修身为本。对该论断的佐证,在先秦儒道两家文献中比比皆是。单就身体本身来说,道家身体观将其视为“道”之直接体现,故主张“顺性命之情”、“安时而处顺”;儒家身体观视其为人文化成之展示场,故主张“克己复礼”、“修己以敬”。有趣的是,儒道旨趣虽然不同,但在成书时代接近的《庄子》、《孟子》中,皆有“辟杨墨”之文字被保存下来,所论皆与身体之对待相关。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窥见两家身体观之差异与各自特点。
身体观;孟子;庄子;辟杨墨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1.002
孔子殁后,儒家受到各方挑战。鉴于此,孟子举起“辟杨墨”之大旗。在他看来,除孔子创立的儒学外,一切与其学理相背、相异的学说都应归入异端并予以驳斥、肃清。其中,尤以杨朱“为我”与墨翟“兼爱”为最。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①《孟子正义》卷二十七《尽心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下册第915-918页。据此可知,杨朱珍爱身体,即便以“利天下”诱之,亦“不拔”其“胫”上“一毛”;②《韩非子·显学》:“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按“胫”指小腿。见《韩非子集解》卷十九《显学》,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9页。墨翟舍己为人,若能“利天下”,即便“摩秃其顶”,③《孟子正义》引赵岐注,《孟子正义》卷二十七《尽心章句上》,下册第916页。“走破脚跟”④《孟子译注》杨伯峻译解,《孟子译注·尽心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13页。也在所不惜。不难看出,二者恰好构成相互抵牾的两个极端。与之相反,孟子则持“执中为近之”的态度。“执中”,即执“一毛不拔”与“摩顶放踵”之中,正是“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之身体观。⑤《孝经注疏》卷一《开宗明义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页。可见,面对珍视与轻视身体的两个极端,儒家表现出“执中”的态度。表面上看,此说与杨墨皆相抵牾,然而有趣的是,古儒亦有“全受全归”之主张,其“守身”之宗旨与杨朱“不拔一毛”颇可相通,只是程度不同。而且,孟子还指出:“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正义》卷二十九《尽心章句下》,下册第997页。该论点,明确表达了“杨近墨远”的判教立场。而孟子这种对道家身体观既打击又拉拢的理论立场,明确显示出儒、道身体观异中有同。对这种异同之研究,或可为解读先秦儒道关系提供一新视角。
一、“气之聚”:道家身体观
除孟子以“为我”二字来概括杨朱思想外,还有其他几条材料亦被论者所重视,其重要性和可信性不在《孟子》之下:“阳(杨)生贵己”。*《吕氏春秋集释》卷十七《不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下册第467页。“轻物重生之士”。*《韩非子集解》卷十九《显学》,第459页。“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集释》卷十三《氾论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中册第940页。将此三条文献所论与孟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批评合而观之,或可对杨朱思想做出正面的概括:贵己者,轻物重生之士也。不拔一毛,以全性保真;不利天下,不以物累形。可见,此说与先秦道家注重个体性,尊重个体生命的一贯主张完全吻合。至于孟子竟斥之为“禽兽”,则显然带有强烈的学派性。*对此,笔者在另一篇未刊稿《从“重生”到“为我”》中有详细的讨论,限于拙作之主题,此处不再做展开。因此,要了解杨朱思想的真正内涵,还应以道家文献为主。
有趣的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庄子,虽为道家人物,但亦有“辟杨墨”之议论。他希望通过“钳杨墨之口”,以阻止他们“外立其德”而导致“爚乱天下”,*《庄子集释》卷四中《胠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中册第353页。对他们“离跂自以为得”的形象颇有讥刺。*《庄子集释》卷五上《天地》,中册第453页。具体讲,即是:“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庄子集释》卷四上《骈拇》,中册第314页。显然,庄子对“杨墨”的批评,意在将其归入辩者之流。*《庄子·徐无鬼》:“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惠子)为五,果孰是耶?”亦将杨朱及其后学归入辩者之流。见《庄子集释》卷八中《徐无鬼》,下册第838页。因其所辩“无用之言”多为“旁枝之道”,而“非天下之至正”。
但是,庄子在阐释何谓“至正者”时,却与杨朱“贵己重生”之旨若合符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集释》卷四上《骈拇》,中册第317页。不难看出,若将“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所欲表达的意涵推到极致,则完全可说“一毛虽微,拔之则伤”。这就避开了“一毛之拔与不拔”同“天下之利与不利”间的种种“无用之言”。这为问题的澄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即以“不失性命之情”为宗旨,去看待“一毛”之拔与不拔。具体讲,若此“一毛”之于我身,存之则伤“性命之情”,则我必拔之而不问其于天下是否有利;若此“一毛”之于我身,存之而于“性命之情”无益亦无伤,则我宁愿不拔,也绝不做“以身殉利”、“以身殉名”、“以身殉家”、“以身殉天下”等“残生伤性”之事。*《庄子集释》卷四上《骈拇》,中册第323页。因为,一朝以天下之利易人一毛,则他日必以天下之利断人一胫。长此以往,待“他者”以天下之利索尔性命,将奈之何!
况且,“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的暴行,往往打着“爱民”以“利天下”的幌子。故而,“失性命之情”以“利天下”来“爱民”者,正是“害民之始也”。*《庄子集释》卷八中《徐无鬼》,下册第827页。其“以己养养鸟,非以鸟养养鸟”者,*《庄子集释》卷六下《至乐》,中册第621页。实乃欲爱之而实杀之。治民者以一己之私、一隅之见强施于民,往往事与愿违,甚至引发灾难。可见,一毛之拔与不拔,竟牵引出如此冗长的因果链条,难怪杨朱路遇衢涂竟“哀哭”道:“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荀子集解》卷七《王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上册第218页。
不难看出,庄子表面讥笑杨朱*此“杨朱”之所指,实为杨朱后学末流,详细论述亦见未刊稿《从“重生”到“为我”》。为善弄“无用之言”的辩者。实质上,他才是杨朱“贵己重生”思想的真正继承人。以此为基础,庄子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以身为本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中,身体并不是一团孤立存在的血肉,而是被安置于整个宇宙之大化流行的过程里。庄子断言,“通天下一气耳”,*《庄子集释》卷七下《知北游》,中册第733页。意即宇宙之大化流行的过程,乃是“一气”流行之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所拥有的身体,亦来源于这“一气”之流行。具体讲,人所得到身体的过程,不过是“杂然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集释》卷六下《至乐》,中册第615页。身体,不过是“气之聚也”,*《庄子集释》卷七下《知北游》,中册第733页。是气化流行中的暂时现象。故曰:“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庄子集释》卷六下《至乐》,中册第616页。这作为现象的身体,不过是假借气之流行而暂有生命的“尘垢”。所以“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庄子集释》卷七下《知北游》,中册第739页。于是,常识中被“我”所直接支配的身体,其实并不属于“我”。换言之,“我”对于身体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至于这“所有权”,则归于“道”,它是一切世俗权威、现象存在之前提。
若能以此为前提,则杨朱之议论将得到正面、积极的解释,其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集解》卷七《杨朱》,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0页。我身之一毫,乃得之于道。道曰与,则与。道曰不与,则不与。“利天下”之虚名,岂可与道同日而语。我所拥有之一身,乃道之体现。一身比于“天下”固然微小,若能奉之以道,“安时而处顺”,*《庄子集释》卷三上《大宗师》,上册第260页。则“天下”虽大,亦轻于吾身;若奉之不以其道,虽以“天下”之大而奉吾身,“不取也”。假使天下人皆能顺道而“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同时亦不以“利天下”为由而损他人之“一毫”,世间便不会有悖道之事。一切顺道而行,顺道而成,天下之治,可坐以待之。
总之,在以庄子(包括杨朱)为代表的道家看来,人们所以要“贵己重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生命均为“道”之直接体现。既然“道”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对于体现“道”的身体、生命就理应贵之、重之。一言以蔽之:“不拔一毛”、“不利天下”。若仅看字面,而不深入道家理论结构的内在逻辑去理解这一口号,当然会将其误作“自私自利”。而这也是杨朱不能不遭到广泛非议的原因之一。
二、“亲之枝”:儒家身体观
道家将身体置于整个宇宙之一气流行的大背景中,认为身体是气之凝形,其最终根据来源于“道”。与此不同,儒家将身体置于血亲延续的“长河”中,认为“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礼记正义》卷五十六《祭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1844页。个人身体被定义为父母生命之延续,而孝的基础正是建立在“要善待父母之遗体”的绝对命令之上。*《大戴礼记·曾子立孝》:“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乎身,敢不敬乎?”《大戴礼记解诂》卷四《曾子立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2-83页。
具体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注疏》卷一《开宗明义章》,第4页。“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礼记正义》卷五十六《祭义》,下册第1848页。其所以不敢毁伤身体发肤,要将身体“全而归之”,是因为:“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大戴礼记解诂》卷一《哀公问于孔子》,第15页。“身与亲”的关系被比拟为“枝叶与根本”。对“枝叶”的伤害会间接导致对“根本”之伤害。“根本”若被伤害,“枝叶”亦会失去存在依据,从而随之消亡。这种比喻,形象地说明儒家眼中的个人身体与道家相较,缺少绝对的独立性,而是血亲宗族“大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大身体”又是由父子、夫妻、昆弟等亲戚成员共同构成的,其曰:“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仪礼注疏》卷三十《丧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册第911页。每个身体在宗族“大身体”中所担任的职能,决定于其在宗族中的地位、角色:“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仪礼注疏》卷三十《丧服》,中册第911页。如果向古儒提问身体是什么、身体属于谁,他们会说,身体是祖先血脉的延续,是祖先已经逝去的生命在现世的呈现;它属于整个宗族,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大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道家相似,儒家亦认为“我”对于身体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不同的是,这“所有权”归于宗族、祖先。
不仅“所有权”不在“我”,就连“使用权”亦受到严格的限制。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孟子正义》卷十五《离娄章句上》,上册第524页。“守身”与“事亲”是人生两件头等大事,而且贯穿始终。所以,“我”对身体的“使用权”,以是否能够充分履行“守身”、“事亲”的义务为前提。换言之,身体只能被“我”用于“守身”、“事亲”。对此,孟子还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正义》卷十五《离娄章句上》,上册第532-533页。仁义礼智,是孟子推崇的德行。这些德行的起点,却是“事亲”、“从兄”。质言之,“尊亲”为诸德之始。孟子所言直白明了:“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正义》卷十八《万章章句上》,下册第640-641页。总之,在古儒看来,身体属于宗族。从某种角度讲,守身而尊亲、事亲,乃是身体存在的终极意义。
儒家一向主张将宗族之内的人伦秩序扩展为国家、天下的政治秩序。“尊亲”,正是这种类比推致的基础:“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礼记正义》四十四卷《大传》,中册第1367页。社稷,即国家之象征,“亲亲”、“尊祖”则是个人身体进入国家政治运作之前的一种训练。故宗族之内以身体之首足比喻父子,国家之内亦以身体之腹心与手足比喻君臣。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章句下》,下册第546页。一国之中,君为“腹心”,为首脑;臣为手足,为股肱。这种“君心—臣体”之喻,古已有之:“臣竭其股肱之力。”*《春秋左传注·僖公·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一册第328页。“君之卿佐,是谓股肱。”*《春秋左传注·昭公·九年》,四册第1311页。“右我先王,股肱周室。”*《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四年》,三册第1018页。“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正义》卷六十三《缁衣》,下册第2121-2122页。于是,国家亦被比喻为一“大身体”。君、臣、民按其所扮演的角色之不同,分别成为“国体”(国家身体)之腹心、股肱与百体。以国家为背景,儒家眼中之个人身体又属于“国体”,且前者是后者的构成部件。*这种以身体喻国体的思维模式,在法家思想中亦有充分体现:“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入,镆铘付体,不敢弗抟。”见《韩非子集解》卷二《有度》,第35页。
有趣的是,儒家亦将“国体”的架构用于反向比喻个人之身体结构。荀子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论》,下册第309页。个人的身体被分殊为“耳目口鼻形”与“心”之两层,又用“国体”所特有的“官”与“君”之层级为喻。显然,君贵官轻。君者,大体;官者,小体。一身之中,亦被分出贵贱、大小。而对身体之修治,当从贵者、大者入手。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正义》卷二十三《告子章句上》,下册第789页。并进一步解释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正义》卷二十三《告子章句上》,下册第792页。所谓身体中之“大者”,就是心。心之作用,则是思。“思则得之”,所得何物?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正义》卷二十二《告子章句上》,下册第757页。“思则得之”者,正是心中固有之仁义礼智。孟子又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正义》卷二十六《尽心章句上》,下册第906页。“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正义》卷二十七《尽心章句上》,下册第937-938页。于是,不同的个人身体又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君子、圣人之身体;一类是小人之身体。二者区别于是否能够完成一种道德之“转化”。*参见杨儒宾著《儒家身体观》,第三章《论孟子的践形观》。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第129-172页。这种“转化”表现为:圣人“能先立其大者”而“从其大体”,即充分运用心之思的官能,将根于心的仁义礼智充分调动、扩充,使这种道德之流行“施于四体”。于是便会产生“道德之光辉”睟然现于面、盎然发于背的效果。亦即所谓“生色”、“践形”。
总之,儒家的身体同时属于宗族与国家。身体之首足、心身,与宗族之父子、国家之君臣互为比拟。国家有君臣,礼乐刑政上行下效,则国治,则教化。身体之心与形,又如国家之君与臣、民,能以心驭形,以德充体,则可实现整个身体的道德之“转化”。可以说,“身—家—国—天下”是一种同质同构的共轭体系,是一个连续、互动的共同体。
三、小 结
通过前文分别对先秦儒道两家身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儒道在定位身体之根本性质的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两家都认为身体绝非孤立、静止、封闭的“原子”,而是网结、动态、开放的“过程”。每个身体都是一个“结点”,是处在联系之网中的不断生成与演化。区别仅在于两家建构理论时所参照的背景不同:道家指认的身体是一种在宇宙之气化流行中凝形、展开的活动过程;而儒家身体所界定的,则是在宗族人伦、国家政治的互动中发生作用的过程。
与道家相比,儒家的身体似乎更受限制,更为被动,更缺少一种绝对的自主性与自由。其实不然,正因为身体处于普遍的人伦联系之中,所以对身体的积极修治,反而会对宗族、国家、天下造成直接的影响。通过修治使个体生命完全展开的过程,亦即是将人文化成全面推展、扩充的过程。一个修治到至善而纯然体现道德之光辉的身体,就是圣人的身体。而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礼记正义》卷六十《中庸》,下册第2023-2024页。其“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礼记正义》卷六十一《中庸》,下册第2040页。这样一来,儒家身体观对本己身体的限制与规定,正是为其修养论提供前提。而修养的过程,则是以至善之道德本体转化心性为开端,进而通过道德化的心性来涤荡受限、被动的肉体,使之接受道德本体的支配而成为一个人文化成的行动中的展示场。唯有如此,才做到能由心性到体表,再由体表而及于他人的感化和转变。对此,孟子曰:“王者之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正义》卷二十六《尽心章句上》,下册第894-895页。其所谓“与天地同流”者,正是理想中唯有圣人才具备的“人格—身体”之共同体,而这种纯粹体现道德的主体,全然就是“道”的体现,或者说,圣人的身体简直就是“道”。
可见,儒道都承认“身体是‘道’的体现”。只不过,在道家看来,要使身体体现“道”,必须通过负的方法,去减、去损。要去除一切人为、造作,才能使禀赋于“道”之“性命之情”昭然朗现。儒家则相反,其使身体体现“道”的方法是积极的修治:不仅要返回内心去寻找超验的道德本体,更要用内心之“良知”调动身体,与之配合而不可缺少的,则是以外在的礼仪规训威仪。总之,要从内外两方面对身体实施“转化”。
[责任编辑:刘春雷]
A New Research on “Refutation of Yang Zhu and Mo Zhai” from Chuang Tzu and Mencius
SHI Chao
(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Different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has always been based on cultivation of one's body. The literature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pre-Qin period is filled with the evidence of such claim. Just for the concept of body itself, in the Taoist view which is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Tao”, therefore, they advocated to “go with the flow”, and “reconcile oneself to one's situation”; by contrast, in the Confucian view which is the display field of the enlightenment, so they advocated to “deny 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 and “take oneself to worship”.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although the tenet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s different, in two books that individually named Mencius and Chuang-Tzu——which were written at the same time——all had similar words to be preserved, and both discussed how to treat the body. Taking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w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views of body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view of body; Mencius; Chuang-Tzu; refutation of Yang Zhu and Mo Zhai
2014-09-16
石超(1985- ),男,内蒙古包头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与身体哲学。
B 222;B 223
A
1002-3194(2015)01-0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