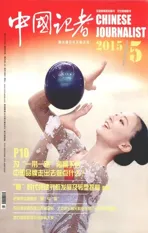热点案件报道的技巧和策略
2015-12-09□文/韩芳
□ 文/韩 芳
热点案件报道的技巧和策略
□ 文/韩 芳
随着我国司法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案件报道正日益成为媒体关注热点。媒体与司法的“亲密接触”使媒体和司法不断擦出“火花”,因而二者都在找寻独立行使并和谐相生的权利边界。本文通过对几个司法热点案件报道的分析,探讨媒体在案件报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又不僭越司法审判权力的技巧和策略。
法律边界 报道禁区 舆论监督
2014年底,轰动一时的内蒙古呼格案,借助媒体的持续关注而最终沉冤得雪,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也成为深受社会敬重的媒体人。随之而来,人们重拾了媒体在法律热点案件中匡扶正义的价值与信心。对于媒体在案件报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又不僭越司法的审判权力,一时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然而,在2014年梳理的传媒法治事件中,世界奢侈品协会诉《南方周末》和《新京报》侵害名誉权,奇虎和奇智公司诉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及上海经闻公司名誉侵权,两起媒体当被告的官司,一审均为媒体败诉。可见,一方面,如呼格案中媒体对司法的正向影响日益彰显;另一方面,媒体人也在感慨,为追求事件真相,一不小心就会越过法律边界。
司法“红线”到底在哪里?
毋庸置疑,司法和媒体的初衷都是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媒体报道时,那条不可逾越的司法红线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报道既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又不至于陷入舆论干扰司法的窠臼,甚至成为新闻侵权的当事人?该怎样报道,才能真正构建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前,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司法机关对于媒体和社会关注的案件越来越多地敞开大门,来自司法机关自身的“以公开促公平”的措施快速增加。司法舆论环境的好转,也使媒体与司法的接触从过去表层的“可不可以报道?”“能不能进入法庭?”等外在“碰撞”,走向了更深层次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解触”。
如今,有的法院不仅让记者旁听庭审;还在不妨碍审判的情况下允许记者录音、录像;有的法院还进行庭审微博直播;有的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案情……但是,由于媒体和司法各自角色定位和天然属性的迥然不同,以及社会上一些陈旧传统观念,纵观当前媒体在热点案件报道中存在的困扰,笔者认为,媒体要将司法案件报道好,做出深度与温度并存、理性与情感兼顾的好报道,首先就要更多地从法制视角入手,担当起促进司法公平、公正的社会责任;其次,记者要学会追踪法案背后的法制内涵,不光要看到司法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更要看到司法对媒体的“不限制”,用好法律不可逾越区域之外更广阔的“自由空间”。
案件审理不同阶段,报道禁区不同
媒体介入司法有其合理性,并且对司法公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也存在着深刻冲突。①按照我国的司法程序,一个案件往往经历立案、开庭审理、一审判决,有的还有上诉、二审、申诉、再审等过程。前些年,一些司法机关和法制媒体认为,案件一立案就予以报道过于轻率,当司法没有定论时,媒体最好不报道,只有结案时才可以报道,至少也要在一审判决时才能报道,否则,一旦引起舆论风潮,必会对审判产生干扰。以往,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如轰动一时的许霆案、彭宇案、药家鑫案,都曾遭遇“媒体声音大,法院声音小”的对比。有人大代表就指出,在法院没有终审之前的大肆宣扬炒作,实质是利用舆论给法院施加压力。这是一种舆论审判,是一种干扰司法的行为。
与之争论不休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体如果等司法有了结论再去报道,就丧失了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媒体虽然要尊重司法程序,但可以对报道文责自负,不该受司法程序的束缚,因此,可以自行选取案件进展阶段来报道。
近年来,来自网络的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微博、微信迅猛发展,其传播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有着层层审核制度的传统媒体,而案件当事人、代理人等相关个人都有可能在第一时间披露案件信息。不同媒介平台在时效上的竞争,舆论话语权的争夺,使传统媒体和司法机关同样需要面对。因此,在全媒体时代,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案件报道,既要发挥好舆论监督的作用,又要防止干预司法的媒体审判,探讨在什么时候可以报道,什么时候不可以报道,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现实的情况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正倒逼司法和传统媒体搁置争论、转变观念,共同面对全新的司法舆论环境。
当前,迫切要研究的是,媒体应如何把握好在案件进展的不同阶段怎么去报,报什么的问题。依照宪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在实际操作中,除特殊情况外,案件从立案到结案,对媒体报道都不再多作限制。而应把重心放在了案件不同审理阶段如何报道的研究上。对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哪些内容是可以报道的,哪些是一旦报道就触及法律红线,甚至后果不堪设想的,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探索。
实践中,媒体不触及法律红线,我们应遵循这样几点:一,在立案阶段,仅告知公众具体案由、双方诉求等内容,对于案件的审判结果不能做出定性、定罪的预告性、倾向性判断。二,在案件审理阶段,要在媒体上对涉诉双方做均等的诉求、答辩报道,不能只报道有利于一方的内容,甚至做其中一方的代言人。三,在案件宣判后,要阐述清楚判决理由,不要用情绪化的辞藻批评判决,以图干预司法的独立审判权。因为新闻事实并不等同法律认定的事实,媒体不能主观地以自己认定的事实引导舆论,进而引发公众舆论对司法的压力,那就会超越舆论监督的范畴,而跨越了舆论监督的边界。
如“秦火火”案的报道,《人民法院报》就在开庭、庭审、判决三个不同阶段,先后以开庭消息,庭审现场通讯+新闻图片,判决消息+评论等不同形式,进行了全程跟进报道。在庭审报道中,始终秉持客观理性的报道立场,庭审通讯配发的是“秦火火”鞠躬的图片②,对被告人的人格权也注重加以保护。
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不是完全不能报道
2013的“李某某强奸案”刚一案发,李及其父母的个人资料即被公开。之后,一些媒体纷纷给予报道,完全没考虑到这是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和强奸案被害人隐私的“双重不公开审理”案件。此事件因广受诟病,成为2013年十大传媒法治事例之一。
当前,随着司法机关促进司法公开的力度越来越大,司法舆论环境也越来越好,那种时不时就有司法热点案件成为全民话题,舆论“参与判决”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是人们对司法案件的关注热情依然高涨。数据显示,上海的复旦投毒案发生后,在受害人黄洋去世次日,即2013年4月17日,新浪微博的单日讨论量就超过了60万人次。而此案在公开审理和全面报道后,也一直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备受关注,甚至在二审开庭中,代理人还亮出了新的证据和辩护意见,但2014年12月8日二审宣判后,该案并没有形成舆论漩涡而顺利“靠岸”。试想,如果本案不在媒体上公开详尽报道,会给公众留下多少猜疑?或者仅仅报道一下判决结果,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应该说,此案的公开审理和媒体的全方位客观报道,携手打了个漂亮的司法公开“组合拳”。
但是,司法审判按照法律规定,有些情况是铁定不能公开审理的,例如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依法可以不公开审理。然而,一般的传播规律是,愈是司法机关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公众愈是产生强烈好奇。因此,一些依法不公开审理的热点案件,更容易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媒体又该怎么做呢?此时,如果主流媒体选择集体沉默,自然是被动而不可取的做法。事实上,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媒体并非只能选择沉默。此时,媒体既不能对新闻事件充耳不闻,又要遵守法律规定,那就只有从法律本身入手,寻找报道突破口。
首先,要分清案件中不能公开的是什么,不公开是所有内容都不能公开,还是部分内容不能公开。
一般情况下,不公开的案件一般如涉及未成年人,强奸案中受害人等不宜公开的内容,媒体在报道时,对于当事人的姓名、年龄、身份、肖像等就一定不能公开。但是,如果这些案件对于社会有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那么媒体可以通过技术处理,隐去他们的真实身份,对于案情有选择地进行报道。不公开不等于不能报道,只是不能报道法律规定禁止报道的内容,因为法律禁止报道的是当事人的身份而非案情,禁止的是详细的案情而非判决结果。在不披露法律禁止的内容的前提下,媒体可以对判决结果等法律允许的内容进行报道。
其次,对于法律虽然没有禁止,但因为一些报道会对司法机关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时,媒体应当遵守相应的职业道德。
目前,在报道司法案件时,虽然有些是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但已经是被新闻界公认的行业自律准则,专业的媒体人应该具有的法律素养要求我们,懂得在报道中以身作则地运用法治思维,向社会传播法治理念。如在报道刑事案件时,不能公开报道详细的犯罪手法;不报道淫秽、血腥、恐怖的场面;不披露刑事案件的侦破手段;尊重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人格权,对与其犯罪事实无关的内容不报道、不渲染。
对热点案件判决,应依法理性评论
关于媒体对案件报道的评论规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迅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评论一般在判决后进行;判决前发表质疑和批评限于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批评性评论应避免针对法官个人的品行学识;不在自己的媒体上发表自己涉诉的报道和评论。
2014年12月10日,复旦投毒案二审判决后,《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也指出:一方面,法院应尊重公众知情权;另一方面,公众和舆论应理解、尊重法院的独立审判空间,以有节制的报道、理性的评说,营造理性的舆论环境。③
上述观点说明,依法审判需要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最能直抒胸臆的非评论莫属。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切忌媒体做出对司法案件审判结果的未判先决,但媒体可以监督司法审判的过程,即程序的合法性以及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依法行使。
我们知道,当一个案件一审结果出来以后,如果当事人觉得判决不公可以通过司法手段提出上诉,如果对二审结果还觉得不公,可以提出申诉。司法程序不仅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也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因媒体既可以监督司法,也能成为司法案件的当事人,所以媒体自身也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和限制,故媒体在行使其监督权利时也要以遵守法律、尊重法律为前提。因此,当传媒认为法院的判决结果不公时可以展开讨论,但不能凭借其舆论监督权,做出超越法律权限的事,用舆论轰炸的方式抨击法院的判决。
所谓的“法律的归法律,舆论的归舆论”,是指法院的裁判结论不因舆论对其有不同看法而受影响,但媒体的记者、编辑们在行使舆论监督权时,依然对司法判决是“有可为”的。媒体正确的做法是,在一份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形成后,媒体可以约请学者从法理的角度对法院司法文书,包括判决书进行学理与学术评价,无论观点是肯定、否定,都是对判决文书的意见分析和理性表达,这也是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必然使命。同时,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共话语平台,理应做遵守法律的表率,对司法判决的评论应是合法、理性、平衡、善意的,决不能做诉讼一方的代言人,更不能贬损法官的人格。如此,媒体才能更好地维护司法的公信力、权威性,才能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行使媒体的监督权利。我们说,只有媒体舆论维护好法律的尊严,法律才能更好地保护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司法和媒体才能做到双赢。
(作者单位:人民法院报社案件部)
【注释】
①刘徐州:《法律传播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53页。
②《迟来的鞠躬——“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庭审直击》,《人民法院报》,2014年04月12日03版。
③人民时评:尊重“复旦投毒案”独立审判空间,《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0日 05 版。
编 辑 陈国权 2468711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