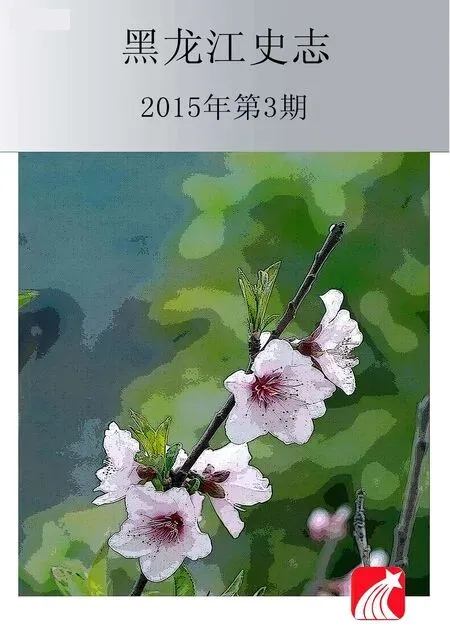民国时期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研究
2015-12-07高阳,冷静
高 阳,冷 静
(1.重庆市档案馆重庆 400015;2.重庆市南岸区文物管理所 重庆 400064)
民国时期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研究
高 阳1,冷 静2
(1.重庆市档案馆重庆 400015;2.重庆市南岸区文物管理所 重庆 400064)
民国初年,重庆已凭借其天然航道优势成为通商巨埠,与此同时,慈善事业亦蒸蒸日上,较为著名的已有慈幼堂、育婴堂、保赤所等,但这些机构普遍存在“有养而无教”的问题,后来得到了许多慈善人士的帮助。
民国;重庆市;孤儿院
一、重庆市私立孤儿院之缘起
民国初年,重庆已凭借其天然航道优势成为通商巨埠,与此同时,慈善事业亦蒸蒸日上,较为著名的已有慈幼堂、育婴堂、保赤所等,但这些机构普遍存在“有养而无教”的问题。重庆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幼年成为孤儿流亡重庆,几经奋斗成为富商,加之其早年接受基督教洗礼,后一直致力于各类慈善事业。1913年刘子如游历上海,参观了著名的龙华孤儿院,受该院立法完善、成效卓著的影响,亦决心在重庆创办一所兼备抚养和教育双重功能的孤儿院。
1914年2月8日为创办孤儿院事宜,刘子如宴请中西德育社、中西英年会、基督教美以美会、内地会、公谊会、自养美道会、重庆总商会等,席间受到众城中名人富商相助,决议成立孤儿院,并择定刘子如捐出之临江门外胜家缝纫女校为住地。初期招男女生共40名,刘子如夫人、胜家缝纫女校校长陈文贞女士认领其中25名孤儿全部生活学习费用。10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取名重庆孤儿院,杨法三于1914年出任首任院长。后因房舍不足,董事张琴舫以十年钱原价捐卖出大溪沟高家庄田业一处作为新院建筑之址,1917年落成后添办高小班,添收60名孤儿,正式循高初两级小学制授课。1929年重庆建市后更名为重庆市私立孤儿院。是为重庆市私立孤儿院之缘起。
二、重庆市私立孤儿院之管理与运作
(一)组织机构及经费来源
重庆市私立孤儿院设董事会为立法监督机关,任期3年,内设责任董事40人,名誉董事无定额,由董事会聘任社会热心人士并能资助孤儿院者充任。董事会设正主席1人、副主席2人,由董事互选充任,任期3年,得连选连任,下设总务、经济、劝募、设计、调查五组分掌各项事宜。此外,孤儿院设正院长1人、副院长2人执掌具体院务,由董事会票选董事充任,任期3年,得连选连任。正院长总揽孤儿院对内对外一切责任,下设事务、教育两委员会,受院长之监督指挥办理所掌事宜。
孤儿院在二三十年代发展繁盛时期常年在校院生有两三百人之众,加之各职员工资费用等,每月所需可谓不菲。就其经费而言,分为下列两种:“基金,由全体董事及社会热心赞助本会人士劝募之;经常费用,由董事分别担任或劝募之。其中基金即基本金,由“董事会经济组交由银行公会安放生息……无论如何,不得动用基本金”。就笔者翻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有关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办理之资料而言,笔者认为孤儿院经费之来源简单叙述约可分为:1)董事捐助。重庆市私立孤儿院乃慈善性质,按月分担经常费用,常年捐助该院者方有资格成为董事,《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组织简章》明确规定董事须“能资助本会”,以捐款、认领孤儿教养费用或捐建院内设施为主要形式。蔡佑祥先生所著《重庆名人刘子如》一书中更言及“规定凡担任董事者,每年要对孤儿院捐赠500元银元,正副院长捐赠的金额比董事还要多些。‘经费若遇不足,辄由子如捐助’”。此外,除有前文已提及的在孤儿院设立之初,陈文贞女士认领25名孤儿之教养费用外,亦有院长曾子唯6000余元捐建纪念堂,副院长李奎安2000余元捐修图书馆之例。2)社会人士捐款。董事会下所设之劝募组,专司劝募之职,包括劝募经费,催收应募捐款、研讨劝募方法及机会、表扬捐款人等。笔者统计1934年《重庆市私立孤儿院院务纪要》所载“两年来捐款人题名”,总计收到52位具名人士捐款,两位无名氏捐款,最高者“一千一百五十仙正”,最低者“三元四角五仙正”;另有仁济医院、广益小学校、宏胜盐号、盐业公会、美道会、内地会、美以美会、鉴丰盐号八家机构捐款,其中以盐业公会“捐洋五千五百元正”为最。3)基本金孳息。孤儿院创立时究竟募集多少基本金现无从考证,唯一有迹可循的是在1934年时任院长曾子唯在谈到孤儿院之未来改革计划时提及“以募足三十万元基金为度”。
(二)招生对象及旨趣
《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组织简章》第二条“本院以教养孤贫之男女儿童俾能自谋生活为宗旨”,精辟的道出孤儿院的招生对象及旨趣。
首先,“孤贫”即言明不单招收孤儿,亦招收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儿童。笔者翻查“1934年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各级男女院生人数比较表”发现,孤儿院各级学生由“孤儿、孤女、附学男生、附学女生”构成,其中“附学生”即是指该院临近不孤而贫之通宿生。以上两类入院学生须确系孤贫无依,且年龄在“6岁以上12岁以下,身体健全、资质优良而无暗疾者”,并经孤儿院院长及考试委员会考选后决定是否录取。录取入院后,教养等各项费用一概由孤儿院承担,学生于高小班肄业后可自由出院。该种生源名额每年由董事部视经济情况决定。需补充说明的是,后因孤儿院办院声望日隆,应非孤贫而愿来院学习之家庭申请,亦招收部分自费生。自费生之报名、考选与孤贫儿童相同,但须负担学食衣履四项费用,剩余部分由孤儿院供给。
其次,孤儿院之办院旨趣在于使儿童能“自谋生活”。第一,孤儿院在平日教养中即非常重视院生生存技能的训练,开设众多职业技术课程,这一点将在下文“课程建设及教学发展”中详细介绍,在此不累述。第二,孤儿院与众多企业建立了推免制度:“1916年保送男生周德入蜀新砖厂,赵金美、董维新、杨邦权、张嘉铭、陈守才、刘道炘6名入裕蜀丝厂,黄志堂、王泽云入澄川织袜厂学艺。1924年保送蒋云才、文明德入美丰银行学业”。类似记录在《重庆市私立孤儿院院务纪要》中多次提及。
(三)孤儿院课程建设及教学发展
孤儿院设立之初,即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定之高初两级小学制授课。1919年经董事会议决,邀请巴县劝学所加入董事部,至此孤儿院教育教学纳入官方监督体系。
1.学科。根据笔者所查之重庆市孤儿院1934年春季教务处制定的“重庆市私立孤儿院课程标准一览表”,孤儿院初级部开设之学科有国语(分语言、读文、作文、习字四项)、算术、常识、公民、体育、音乐、农业、工艺、手工九门课程,每周共计43个课时。高级部开设之学科有国语(分语言、读文、作文、习字四项)、算术、自然、社会、公民、卫生、英语、体育、音乐、农业、工艺、图画、珠算、手工、国技十五门课程,每周共计51课时。单就课程设置本身而言,应该说是丰富且关注院生全面发展的。
2.工业。考虑日后孤儿就业、自食其力的需求,孤儿院尤其重视相关职业学科的设置与发展,1920年经孤儿院董事会议决添设工业,先后开办了织袜科、织毯科、音乐科(即军乐科)、鞋科、印刷科等。
3.工读互助。1929年,李奎安任院长期间,与幼稚工厂订定《工读互助办法》,即孤儿院年长不易造就之才送至该厂学艺,该厂幼稚儿童不能工作者,送入本院读书。
三、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特点分析
(一)教养兼施
通过前文的论述,相信读者亦能发现孤儿院设立的目的、学科建设等均在践行教育与抚育并行的理念。笔者认为“教养兼施”的理念于刘子如创办之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如此淋漓尽致的实践绝非偶然,是与彼时的社会思潮及刘子如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从社会思潮来说,早在晚清时期,“教养兼施”的救助理念就已开始盛行。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加之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大量难民涌现,其社会救助问题随之浮现,其中难童教养尤引人关注。与此同时,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华传教,开办教堂,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等机构,收容孤贫幼儿。《资政新篇》、洋务运动、早期维新派的论述、公车上书等影响晚清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均或多或少的涉及到教养兼施的理念。内外合力之下中国传统慈善事业悄然转型,由重养轻教逐渐趋向教养兼施。1913年刘子如在佛教大师苏曼殊的带领下参观的上海龙华孤儿院即是这样一所近代意义的儿童救助机构——既是济贫抚孤的慈善机构,亦是工读兼修的学校。该院院生除完成六年制高小外,“男院设籐工、木工、竹工、鞋工四工场……,女院设立缝纫、烹饪、刺绣等业”。龙华孤儿院这种教养兼施的运作方式使刘子如大为赞赏,并触动了他渝市孤儿男女“既无所养,亦失所教,流离载道,良堪悯怜”的思绪。这次旅行返渝后,刘子如即投身孤儿院的筹办工作,并得到好友曾办理成都孤儿院的杨法三、重庆青山年会负责人毛宅三的支持。
除了这段上海龙华之缘,刘子如少时经历也不得不提。就目前留存不多的刘子如资料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刘子如幼年即成为孤儿生活困顿,辗转来渝后举目无亲,一度被临江门外嘉陵江边红庙的当家和尚所收养。这段经历无疑令刘子如领会到无养无教的痛苦和受到救助的可贵,必对其日后的慈善之路产生影响。在发表于1934年的《刘子如自述》中亦提到刘13岁时“仅带53文小钱,步行来渝。初学刻字,继营书铺,稍有积蓄,常入木牌坊伦敦会福音堂,颇受感化,尝以博爱慈善诸教义自勉”。相信读者也不难理解刘子如日后为慈善千金散尽的人生。1934年时任重庆市市长潘文华在孤儿院成立21周年纪念时为纪念刊题词“教养兼施”,这无疑是对刘子如创办孤儿院最贴切的褒扬。
(二)立法完备、管理先进
孤儿院在设立之始即受到立法规范之上海龙华孤儿院影响,颇为重视各项规章的设立,又因刘子如邀得办理成都孤儿院多年的友人杨法三加盟并出任首任院长兼董事使得孤儿院办理有经验可鉴。仅笔者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有关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的资料中找到的各项规章制度就有《重庆市孤儿院组织章程》《重庆市私立孤儿院董事会执掌规则》《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办事细则》《捐助本院者褒扬条例》《本院现行孤儿入院出院章程》《本院招收自费生办法》《重庆市私立孤儿院暂行会计规程》《重庆市私立孤儿院经济审查委员会暂行简章》《重庆市私立孤儿院院生惩奖条例》《本院稽察室办事简则》《图书馆参观简则》《本院院生一般生活纪律》等10多个,涉及院内工作各方面。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在立法方面堪称完备。此外,管理先进亦是应当一提的特点:董事会制度,如当代公司治理一般,有了相互制约、系统管理的可能性,董事会及院长政务系统之分立设置,稽查室、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存在,无不透露着现代企业治理的智慧。又如孤儿院1932年设图书馆,内藏图书除时任院长李奎安寄存部分未分类陈列外,其余图书均按照杜威“十进”分类法分类、“四角号码法”排列,这些细节均向后人表明孤儿院虽为慈善机构,但在内部管理、机构设置上科学、先进的理念。
(三)关注学生长期发展与回馈学校
前文笔者已经讨论了孤儿院在院生离院前,多有推荐入厂学艺或学业的情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孤儿院亦鼓励、支持学生的进一步深造。重庆市私立孤儿院《本院现行孤儿院入院在院出院章程》规定,“院生在本院各班毕业品学俱优经本院认为堪资深造者本院得资助其升入院外优良高级学校后每期之学食费,但如中途无故辍学仍须饬保偿还本院该项费用”。有如是政策之鼓舞,加之孤儿院亦一贯重视教学,孤儿院中有不少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如1920年“升送毕业生蒋昌裔王在明投考联合中校,秦文钦何仕仪投考川东师范,均蒙免费录取”。1924年“升送毕业生杨麟昭入求精中学,张开文入川东师范学校肄业”。1932年“升送吴富荣胡明发入川师,胡廷贵入巴中,谭正治周济富罗万贤邵本清入重中肄业”。类似学生继续深造的例子在《重庆市私立孤儿院院务纪要》中屡次出现。从孤儿院整个30余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这里还走出了红岩烈士江姐,重庆市第一任副市长余跃泽等名人。
慈善的精神予人以希望,其精髓重在传承,而最好的传承莫过于回馈。笔者认为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具有先见的:继续深造的院生,要求每周日回院一次,与在院院生分享经历与心得;已毕业的院生如经营工商业的,要求经常书信联络报告经历;“院生曾在本院高小班毕业将来就业如月薪在50元以上者本院于必要时得募收其所得捐十分之二至三年以上。院生曾由本院升送院外高级学校毕业者如愿回院扶助院务进行本院得视其在院工作之成绩与年限之递增每月酌给其相当生活费否则得于其50元以上之收入内募收其所得捐十分之三至三年以上”。
(四)重视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直至今日都是国际教育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更是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板块。而设立于上世纪初年的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再一次向后人展示其创始团体卓越的眼光,“职业教育,为现今极有研究价值之问题,故本院特加注意”笔者分三个层面进行介绍:
1.音乐科。1910年至1929年孤儿院开设之工业各科因各种原因陆续停办,仅音乐科一直持续办理。音乐科即为军乐科,为1920年8月由刘子如自美国购回多件军乐器后开办,聘日本人细田市松为军乐队长,以“院生中年龄较大而相宜学习者学习之”,是为重庆第一家军乐队。彼时的重庆作为内陆城市,保守且落后,军乐科的成立无疑是超前的,既培养了学生的音乐才华,拓宽了职业道路,军乐科院生待“娴熟后,即应社会人士或其他集团之请出为社会服务,所得酬金,除酌提奖金分给该班学生外,其余悉作补充院费”,亦给孤儿院不充裕的资金做了些许贡献。
2.职工班。该班以院生中年龄较大、资质较钝,而又无家可归的孤儿组成。在课程安排上,每天除上国语等重要课程外,主要即于职教员之指导下分理办公室图书馆以及校园事务,以能独立生活时出院。
3.一般院生之职业陶冶。其余院生在亦注重一定程度的职业陶冶,旨在“引起职业兴趣、去除贱视农工的恶俗”,初小三年级以下之院生主要是在课余施以“游戏工业之指导”,初小四年级上之院生则“令其实际参加校园之各种作业”。
在1934年时任院长曾子唯的改革设想中还提到,“扩大职工班、筹办职业中学部、筹办职业速成班、筹办专修班”等设想,可惜是否成行现有资料难以一窥究竟。
4.善用社会名人影响扩大孤儿院影响力
在孤儿院发展的三十多年中,创始人刘子如最高也是唯一一届担任职务即是在1918年时曾任副院长,其余时间均为普通董事。因刘子如希望将董事会主席、院长等重要职位用以吸引有名望有实力的人士担任,借以扩大孤儿院之社会影响力,争取更好的办学条件。于是在孤儿院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影响颇著的民国名人,如担任名誉院长的四川省省长刘湘、重庆市市长潘文华;任院长的重庆市商会副会长、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李奎安,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任董事的重庆大学的倡导发起人之一温少鹤等等。
四、孤儿院的衰落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自如亲率“重庆各界抗战后援会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支援抗战,重庆市私立孤儿院失去最大精神支柱。此后的陪都重庆频遭空袭,孤儿院多次受损,房租收入和社会捐助锐减,后校舍亦大部被征用。资金日窘、维系困难之下,1940年——1941年孤儿院校长程远、孟康先后向重庆市社会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市政府申请救助。1940年下半年,院内孤儿悉数被重庆市第九保育院接收,1941年春重庆市私立孤儿院改办小学。这座重庆市最早、规模最大的民办孤儿院就这样在战火中衰落,不可不谓可叹。聊以安慰的是,1941年,年逾古稀的刘子如返回故乡重庆綦江青山,亲自料理自己在1931年开设的青山孤儿院,千金散尽,成绩蔚然,令人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