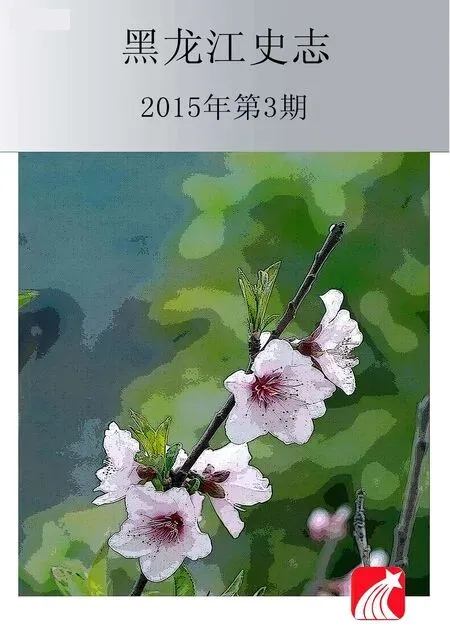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历史原因探析
2015-12-07曹祺马敏
曹祺 马敏
(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关于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原因,学术界主要形成四种观点,“扩张”说、“防御”说、“综合”说、“多因素”说。“扩张”说认为苏联出兵是一种武力侵略行为。[1]“防御”说认为苏联出兵则是一种国家自保行为。[2]“综合”说主张苏联出兵是扩张性与自保性兼而有之。[3]“多因素”说则提出抛弃“扩张-防御”的叙事框架,从各个角度分析。在抛弃“进攻-防御”话语体系后,学术界研究的视角渐次关照到“国家安全利益”、“意识形态利益”、“地缘政治利益”、“自然资源”等因素。[4][5][6][7]但是,这些观点无不是把苏联看成一个整体来考察,殊不知苏联决策层内部的分立和私心对于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苏联对美国的错误判断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也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除了主观因素外,阿富汗糟糕的局势也让苏联焦头烂额,决心出手处理。
一、苏联决策层的分立和心理
苏联决策层的私心和分立是推动苏联出兵阿富汗的重要原因。1979年,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不佳,“国家的政策由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三驾马车决定。”[8]525“三驾马车”从勃列日涅夫手里接过苏联的最高决策权。但是,他们显然并未能造福于苏联,反而把苏联拉进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之中。正如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评价的那样,“不管觉得多么奇怪,三人联合执政确实比勃列日涅夫一人执政时的情况糟糕。自信的领导人通常善于作出让步和妥协,可这三个人,每个人都极力表现自己的毫不动摇性、坚定性。他们使国家陷入了同外部世界的激烈对抗之中。”[9]640三人联合执政的最大弊病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机制来运作由勃列日涅夫短暂下放的最高权力。“三驾马车”的权力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互不干涉,“每个人都掌管着自己的领地”,三人表面上的“协调一致基于相互之间的保证:你不干涉我的事情,我也不干涉你的事情。苏联最高机构的决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12]275各部门各自为战,甚至有时还暗暗较劲,致使信息流通不畅,进而导致决策层判断失误。1979年12月,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手写的绝密报告。报告认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兼总理“阿明很有可能为确保个人的权利而投靠西方”、“他背着我们与美国代办进行接触。”[12]252-253基于这一情报,苏联高层认定“为了掩饰自己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阿明发表了急进的革命言论,与此同时,他的代理人却同华盛顿的代表进行秘密接触。”[2]681但是时任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参赞的萨夫龙丘克公使却说:“当时,我与阿明、阿姆斯特茨以及美国驻喀布尔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经常见面。”[12]250可见,阿明与美国的接触是在苏联监控之下的,并非秘密进行。关于阿明亲美还是亲苏的问题将在下文得到更为详细的论证。外交部与克格勃之间缺乏基本的信息交流,致使苏联决策层对阿富汗的局势判断失误。“三驾马车”互不干涉的工作模式使得苏联的每一次决策都因缺乏全面和准确的信息而面临着极高的风险。
“三驾马车”决策模式的另一个弊病在于缺乏对个人私心的压制和监督。这就让个人的私心在自觉不自觉中左右着苏联最高层的决策过程。这里以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为例,观察私心如何影响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的决策过程。不少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积极地主张出兵阿富汗。其实,在乌斯季诺夫积极主战的背后无不掺杂着个人的私心。格·阿·阿尔巴托夫敏锐地指出,“特别是在当上国防部长以后,他仿佛企图证明,文职部长甚至可以比职业军人为军事部门获得更多的东西。”[10]280军事行动必将有助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为军事生产部门争取更多的预算,从而证明自己卓越的才干和价值,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在那个时候,乌斯季诺夫肯定想不到苏联会被困在阿富汗整整十年。在他的预想中,出兵阿富汗是一场耗时短、规模小、取胜易的军事行动。多勃雷宁回忆说,“乌斯季诺夫满有把握地认为,整个军事行动可以相当迅速地完成。”[11]501格里涅夫斯基也谈到,“据乌斯季诺夫的亲信讲,乌斯季诺夫确信,只要苏军一出现在阿富汗,那么叛乱者要么立刻缴械投降,要么就会望风而逃。”[12]245乌斯季诺夫希冀利用阿富汗的军事胜利来提高自己以及国防部的地位与威望。他的信誓旦旦无疑坚定了决策层出兵阿富汗的决心。总的说来,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权力运行制度,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在决策时往往带有或多或少的私心成分,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私心和“各自为战”影响了苏联最高决策层的判断能力与决策的正确性。
二、苏联对美国的错误判断
莫斯科对华盛顿的错误判断也是导致苏联出兵阿富汗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种错误判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苏联错误判断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程度。人民民主党掌权后不久,阿富汗境内便频频出现反政府运动与武装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向反政府人员提供有限的间接援助,这一行动使莫斯科大为不安。“苏联特工机关警告说,中央情报局挖空心思搞这些活动是有图谋的,他们想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监视苏联航天火箭试验的基地,这个基地原来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国人不得不将它紧急撤出伊朗。”[12]195随后,勃列日涅夫在《真理报》上进一步明确,“不断发生的武装干涉,外部反动势力的阴谋串通,给阿富汗造成丧失独立和变为我国南部边境的帝国主义军事据点的现实威胁。”[2]682显然,高度紧张的莫斯科听风就是雨,完全认定华盛顿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阿富汗,并且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那么,华盛顿是否有此设想呢?“美国中央情报局还的确讨论过这些想法。”但是,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坦言这些想法是“思维僵化,脱离实际的官僚习气。”[12]195也就是说,美国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些设想。由此可知,华盛顿对喀布尔的实际影响力并不大,还远没有达到莫斯科所担心那种的程度。其实,阿明政府与美国的关系也可以佐证美国并不能操纵阿富汗。在决定出兵阿富汗时,苏联决策层一致认为阿明具有强烈的离苏亲美的倾向。克格勃甚至怀疑阿明“在美国读书时曾经被中央情报局雇佣。”[10]278在莫斯科看来,阿明掌控下的喀布尔显然已是华盛顿的囊中之物。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苏联驻阿富汗公使萨夫龙丘克所言,“我并没有感觉到阿富汗和美国的关系有什么改善。”美国驻阿富汗的代办阿姆斯特茨也说到,“事实上,阿明在其执政期间从未与美国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从最初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到后来任总理,直至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阿明很少为赢得美国的信任和获得其援助而花费心思。”[12]250可见,神经衰弱的苏联主观认定美国对于阿富汗的控制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错误地判断了局势。
另一方面,苏联错误判断了美国对于苏联出兵阿富汗最有可能的反应。1979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与卡特在维也纳签署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期间,卡特曾说:“在世界的这些地区中,有些地区涉及我们的切身利益,苏联应该承认这些利益。其中的一个地区是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地区。……伊朗和阿富汗存在不少问题,但美国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我们希望苏联也能像我们这样做。”针对卡特的这番表态,苏联决策层有两种俨然不同的理解,产生了分歧。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认为“卡特在维也纳建议我们在西南亚划分势力范围,这和当年在雅尔塔划分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别无二致。伊朗和阿富汗归入苏联的‘切身利益’,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则划到了美国的‘切身利益’中。”他们误以为这是卡特总统在向苏联透露美国的底线,即美国不会为阿富汗而破坏苏美关系。这无疑极大地减轻了苏联做出出兵阿富汗决策的压力。但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不这么看,他认为“卡特所指的不是划分势力范围。他只是建议双方要在阿富汗和伊朗保持克制,并使波斯湾地区依然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内。”[12]214-215那么,卡特总统这番话真的意味着划分势力范围吗?吉米·卡特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一九七九年五月起,我们就一直密切注视着苏联在阿富汗增加驻军的情况,并对苏联人显然意欲干涉这个小小邻国的政治事务提出警告。”[13]550-551很明显,葛罗米柯抓住了卡特的真实意图,可惜,他很少会在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莫斯科自以为摸准了华盛顿的底线,因而肆无忌惮地将军队开进阿富汗,自信华盛顿会像对待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一般宁静。正如当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所言,“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采取行动时认为这一行动不会触及美国的利益,而且不会威胁我们所知的美国在波斯湾的根本利益。”[11]511不过令莫斯科诧异的是,华盛顿这次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强烈。
三、阿富汗的局势
阿富汗客观形势的发展是促使苏联出兵的直接因素。1978年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主席塔拉基发动政变上台,杀死统治者穆罕默德·达乌德,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史称“四月革命”。在塔拉基统治后期,阿富汗已经面临了尖锐的国内矛盾。人民民主党内部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派”与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争斗不断,清洗运动不时发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人民派”大获全胜,成功地驱逐了“旗帜派”。然而,内斗并没有随着“旗帜派”的失败而告终,“人民派”内部又出现塔拉基和阿明的争权。1979年9月16日,塔拉基被迫宣布辞去党和政府的职务,阿明接替为党的总书记。阿明上台后,阿富汗的形势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陡转直下。阿富汗80%的领土被反政府武装控制,政府军只能占据着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主要的交通运输网和公路干线也在反政府力量手里。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莫斯科决定出兵阿富汗,稳定阿富汗局势。同时,苏联还不得不考虑到意识形态的问题。“苏联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共有5000万左右,其中3500万人生活在中亚地区。”[14]苏联担心伊斯兰原教主义势力夺取阿富汗,危及苏联中亚地区。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谈到,“意识形态的原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即维护这个亲苏政权的目的旨在对付我们穆斯林人口居住的边境地区附近的伊斯兰原教主义不断上升的挑战。”[11]505时为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的弗·亚·克留奇科夫也说到,“伊斯兰因素令人担忧,莫斯科担心伊斯兰原教主义在阿富汗占优势以后,会很快扩展到苏联的中亚地区。”[15]181伊斯兰原教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坚定了莫斯科出兵的决心。
1979年12月25日,第108摩托化步兵师独立侦察营进入阿富汗,同时,第103空降师的运输机也降落在喀布尔机场。随后的两天内,苏联军队大规模开进阿富汗。在27日,代号为“霹雳”的克格勃特种部队击毙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兼总理阿明。当晚,喀布尔电台广播阿明死亡以及卡尔迈勒被任命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消息。应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华盛顿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态度。1980年1月4日,卡特宣布对苏联采取广泛而有效的惩罚措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体育等方面。1月5日至7日,美国在联合国的特别紧急会议上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卡特总统在1月23日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要极其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立场:任何外部势力想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切身利益的侵犯,对这种侵犯,将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的手段予以击退”。[13]565这就是著名的卡特主义。
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仅使苏联深陷近十年的战争泥潭,国内经济背上沉重负担,而且在国际上丧失了“特权地位”,将美苏关系由十年缓和时期带入“新冷战”阶段。
[1]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M].韩正文、沈芜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M].王振西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4]刘金质.冷战史(中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5]郭春生.苏联出兵阿富汗:原因和后果[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1(1).
[6]于卫青.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原因及决策因素探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7]李琼.从犹豫到出兵:1978-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决策探析[J].历史教学,2011(16).
[8][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M].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9][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M].李惠生、赵志鹏、钟忠、王宪举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0][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11][俄]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M].肖敏、王为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2][俄]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苏联外交秘闻[M].李京洲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13][美]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M].卢君甫、周慧、徐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14]谭荣邦.苏联侵略阿富汗新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4).
[15][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M].何希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