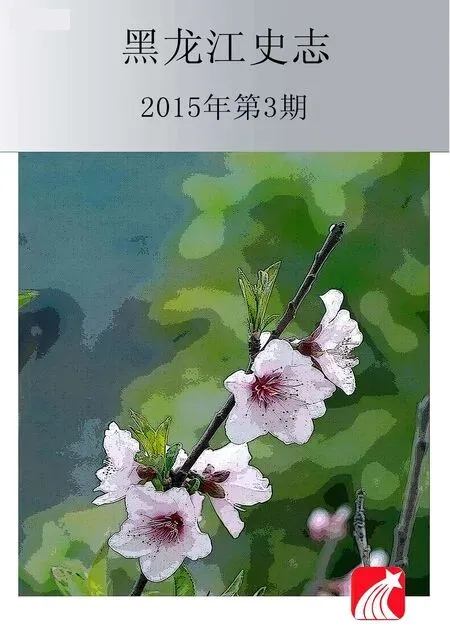两面镜子里的肖像——伏尔泰与卢梭自然观的比较
2015-12-07蒋文杰
蒋文杰
(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康德在1784年写的《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他号召人类摆脱外在的权威,用理智把自己从幼稚中解救出来。在18世纪整个启蒙运动中,“自然”常常与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关键词“理性”一起,受到赞美。按照古典传统,自然界只有服从于理性时才美;按照浪漫主义观点,自然界唤起激动情感和富于诗意反应才美。正是这两种对比性的观点构成了整个18世纪激荡思潮中“哲学家们”的两种自然观。
亨利·古耶《卢梭与伏尔泰》序言中指出,启蒙运动的精髓不在于“同一”,而在于各种差异思想在相互批判中形成“统一”的运动。““承认思想差异”与“提倡批判精神”是欧洲社会经启蒙运动涤荡,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在启蒙运动高涨的法兰西,伏尔泰和卢梭是两位极具代表性的“哲学家”。歌德曾说过,伏尔泰标志旧世界的结束,卢梭代表新世界的诞生。短短一句话,表明了伏尔泰与卢梭之间关系的要害:他们同为新旧世界之交的历史巨人,启蒙运动的主将,然而两人着眼点不同,加之他们各自的个性、共同的朋友圈子、生活际遇等因素的作用,使两个人成为这两种自然观的代表性人物。布林顿也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写出,18世纪是西方近代世界形成时期。基于18世纪这两种自然观,布林顿把伏尔泰划分为启蒙运动的第一生代,卢梭列为另一生代。
一
在18世纪的法国,占主流地位的思维方式是用数学和力学的观点观察一切的机械论思维方式。相信理性能够带来社会发展与进步也成了那个时期启蒙思想的主流。以伏尔泰为首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以理性精神对抗神权迷信,批判现存国家与社会中一切腐朽没落的方面,动摇着法国封建专制的根基,宣扬着理性会带来社会的自由与进步的理念,使理性自然法成为启蒙运动中的一个主流思潮。
如今,在伏尔泰丰厚的著作中,被阅读和引用最多的应该属《查第格》、《天真汉》、《老实人》这些散文体的故事书。严格意义上讲,伏尔泰算不上自成一体的哲学家,没有固定的理论,他的思想是一些他经常论及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比较松散的“思想”中,把握来自两个主要的影响:一是笛卡尔、牛顿的数学理性;一是洛克的人学和经验学说。崇尚理性,崇尚科学,是伏尔泰用以批判宗教神权最有力的武器。伏尔泰始终都在运用理性同封建专制、神学、迷信进行着战斗。他认为,上帝的存在只能靠惟一的理性来证明,人的理性是神所赐予的,且神给了每一个精神健全人理性自然法的观念。在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伏尔泰对宗教神权的批判,无疑是最彻底、最不留情面的,他甚至说出了“天主教和加尔文教都是用粪土和腐朽血浆捏成的”这样过激的话。但与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不同,伏尔泰对宗教的批判,并没有导致无神论,他继续着对理性的探索与追求。
作为牛顿和洛克所开创的哲学的拥护者与积极传播者,伏尔泰继承了西欧尤其是英国哲学所宣扬的理性自然法观念。即人的行动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历史是人的本质作用的结果。有特定目标的自然或理性意图贯彻于历史的进程之中。伏尔泰接受了牛顿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背后有一个至上的存在,存在着一种超人的意志,它是人类智慧的来源,他是世界的“设计师”,并赐给人类的永恒理性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支配性力量。伏尔泰的上帝等同于牛顿的上帝,是一种宇宙和谐的表现,它关注于理智,而不是人的情感。他的上帝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大理性。自然界在宇宙之中,宇宙又在笛卡尔、牛顿等人物理数学规律的理性之中。
“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完美智力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转换造成的。”3把上帝与科学分开,从一种更为客观的科学方法上讲是一大进步。伏尔泰利用牛顿式的科学理性把自然宗教与历史宗教区分开。伏尔泰认为自然宗教是一种善,基督宗教作为历史宗教的一种,严重践踏了人类自然宗教信仰,基督教与自然宗教格格不入。在其著作《五十人的说教》、悲剧《默罕默德》中,从内心厌恶一个与暴力、贪婪、肮脏联在一起的上帝。然伏尔泰并没有对基督教的批判走向无神论,他相信至高、至善的上帝。他相信的是拿着理性火炬的上帝。
伏尔泰崇尚理性,人的本性是理性,做人,就是施展理性。但他的伟大之处又在于,伏尔泰看到了理性的有限性,面对大千世界,人的理性显得有点苍白。在《哲学通信》一书中写道“冷酷的决策者、能说会道的教育家、博学的理论家,你要寻找自己意识的界限吗,它就在你眼前”。古耶指出,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是出于对基督神权深刻批判之后,对人类理性认识有限性的无奈。
二
与伏尔泰信仰的上帝不同,卢梭的上帝则来自与人类内心的呼唤。造成这种同时代“哲学家”们信仰极具差异的原因正是18世纪两种自然观。卢梭把启蒙运动带向了一个非常不同与伏尔泰所追求的发展方向,也正由于此造成了伏尔泰与卢梭颇具说道色彩的恩怨。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十年,卢梭去世——他没有想到,伏尔泰更没有想到,他的骨灰会移葬先贤祠,“我们的道德、风俗、法律、感情和习惯有了有益健康的改进,应该归功与卢梭”这么高的评价。卢梭成为了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标杆,成为了18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中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物。
在启蒙运动摧古拉朽的年代,此两种观念,或两种态度,曾通力合作过,使旧制度的威信殆失已尽。布林顿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中指出,“浪漫主义运动全貌大体已具见于卢梭”4卢梭认为,自然不惟生来即道德的,亦且生来及合理,人的心与其智同等重要。“浪漫主义毋宁乃对于理性主义的一种叛离的运动,此叛离乃子代对亲代的叛离。”此叛离运动最富代表的是卢梭在1750年获奖论文中回答了“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道德进化”问题。卢梭的回答是否定的。“人性本是善良的,是社会制度使人变恶”。在卢梭看来,这个使人能够超越自然,倾听上帝的“情感”,就是善良的本性。这是卢梭由理性向情感的升华。正是这种不同与伏尔泰,对人类善良本性的信念和期望,使卢梭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人。
卢梭“私自”打开了“另一世界”的门,叛离了启蒙运动的“通过理性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信念”。《论科学与艺术》从社会现状出发,揭露科学与艺术泯没了人类纯洁、善良的本性;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没有升华人类的道德情操。人类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沦为科学与艺术的奴隶。“只要权力是一回事,而知识与智慧又是一回事;学者们便很少会想到什么伟大的事物。君主们则更少会做什么美好的事情来,并且人民也会继续卑微的、腐化的与不幸的生活下去”[7]“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8]卢梭认为,人类接受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和智慧箴言,却失去了对行为善恶的辨别能力,破坏了人的天然的淳朴本性。而且知识的扩展加大了人与人的才智差别,更造成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卢梭看到了科学发展与社会风尚、个人德行之间的不统一,特别是他所指出的科学认知的进步与社会正义之间的悖论,无疑具有睿智卓识。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之重要价值,首先在于他以其远见卓识,开启了研究科学与道德、理性与价值关系的先河。
之后,卢梭又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于基础》中,进一步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自然状态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历史的人的,私有制的产生如何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卢梭发现社会关系的适当基础在于美德之中,在任何情况下,人生来就在美德状态中,而社会使人堕落。人类行动背后的驱动力量就是激情,而理性只能够指导和约束但不能排斥他们。嫉妒、幸福、藐视、恐怖、悲哀等这些激情构成了人类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心”要素。
卢梭认识到科学所代表的理性虽然揭示了自然规律,促进了技术进步,但却只关心以合适的手段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无关人生的意义。在他看来,在价值观念方面,科学理性是无道德是非的、中立的,而科学如果独立于社会生活,缺失了价值的维度或方向,那就隐藏着危险。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不但是自己全部学说的出发点,而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在休谟那里发展为清晰的怀疑主义,休谟对“事实”和“价值”进行了区分,认为在伦理领域,科学方法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从而使启蒙运动中乐观的理性主义陷入了困境。卢梭的思考对康德亦有启示,康德哲学提出的“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区别,亦即科学认识的对象领域与道德思考的对象领域的不同。
卢梭对科学与艺术的批判不是一场对理性的抨击。正是通过理性,卢梭希望揭示人类本性的东西。在启蒙运动的年代,人们的思想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也使人类的激情被释放出来了。卢梭的学说其实是以情感的理性对科学的理性的一种批判。抨击与认可,卢梭已经把启蒙运动引上了另一个方向。卢梭的“批判理性”的精神对人类发展进步产生了居功至伟的贡献,堪称“精神世界的牛顿”。
三
卢梭也许不是第一个赞美激情的人,但确实是最富典型的思想家。卢梭的这些言论不是那些启蒙“哲学家们”想要听到的言论,他们承认社会可能产生贪婪、肮脏等坏的东西,然更相信理性的社会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进步而不是堕落。卢梭换个角度看科学与艺术,发现自己的观念有多可笑,无疑是给“哲学家们”的一记棒喝。
卢梭进入“另一世界”的言论是对启蒙哲学家们圈子的叛离,是对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以来思想领域的一种革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与围攻是无疑的。伏尔泰对此表示了深深的厌恶,他在1755年8月30日致卢梭的信中讥讽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牲畜。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望用四只脚走路了。”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视为“一部非常蹩脚的小说”;且认为最早的人们更有可能是粗野的而不是善良的。正是这种对人性本质认识的不同造成了卢梭由崇拜伏尔泰到与其恩怨丛生,甚至卢梭在1760年给凡尔纳的信中写到“您跟我说起伏尔泰,为什么让这个小丑的名字来玷污您的信呢?这个卑鄙的小人断送了我的祖国,我对他除了鄙视,只有恨,他的天才是对他的侮辱”[10];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也强烈地要求卢梭改变其言论。然卢梭的言论也受到了一些“有理性”思想家的承认。休谟就把禁欲、克己、苦修视为无人性的行为;霍尔巴赫认为禁止人们的激情就是禁止他们成为人。
正是伏尔泰和卢梭代表的这两种进步自然观,构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的核心“智”与“心”,成为西方近代世界形成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仍部分以伏尔泰“科学理性”和卢梭的“伦理理性”为生。
注释:
[1]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转自于《中国思想论谈》,2007年11月.
[2][法]亨利·古耶《卢梭与伏尔泰》,(裴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2版,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