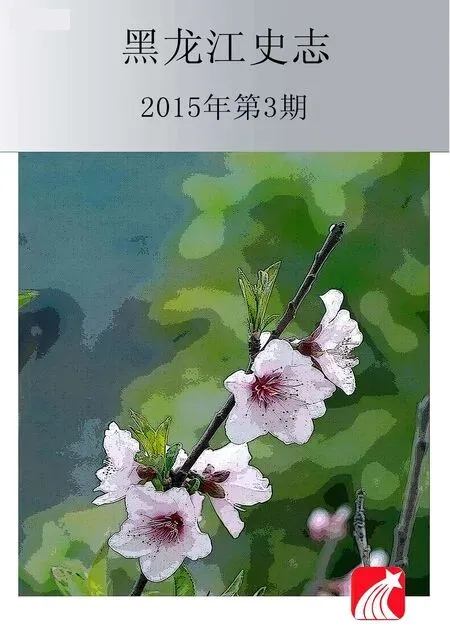抗战前上海的纸张供给论略
2015-12-07曾宪足
曾宪足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纸张为现代世界文明国家的必需品。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对于纸张的消费和需求更是十分旺盛。大量书刊的印刷和出版,频繁的贸易往来和货物购销,构成了抗战前上海纸张消费的主体。然而,上海本地所产机制纸却远不敷所需,必须经常依赖外界各种纸张源源不断地输入。那么,当时上海需求的纸张究竟来源于何处呢?
一
当时我国需用之洋纸,种类虽较繁多,然重要者不过有光纸、新闻纸及印刷纸三类。“有光纸为我国独用之教科书用纸,新闻纸除用于报纸之外,亦供印刷包装之用。印刷纸即俗所谓洋纸,供帐簿册籍票据等用”[1]。抗战前的上海,不仅是我国新式文化的中心,而且工商各业素称发达,内外贸易十分频繁,对于纸张的需求自然也异常显著。据统计,1913年全国纸张进口占该年度进口总值的比重为1.3%,而上海纸张进口占该年度进口总值的比重则为1.5%。到1936年,上海纸张进口占该年度进口总值的比重更是比同期全国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达到5.4%。[2]输入上海的纸张,主要来源于国外和国内两大渠道。就国外而言,以挪威、瑞典、芬兰、英国、日本、美国等国为主。由于国外进口的洋纸以上海为最大消费市场,因此全国洋纸进口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上海洋纸输入的状况。一战前后,我国洋纸的供给和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战以前,瑞典、英国输入于我国之洋纸最多,欧战起后,欧洲来货尽绝,日、美两国乘机而起”[3]。如1920年我国进口之纸与硬版纸,共计关平银13102116两。其中,自日本进口之数最多,计关平银3802987两。美国次之,瑞典、挪威、英国又次之。[4]另据王云五的观察,“近数年来,洋纸进口之额,有加无已。民国十五年,达二千八百万两,而以上海为最大消费市场。进口纸类,日货为多,英、美、瑞典次之。”[5]直到1927—1929年间,各国输入中国之洋纸额,仍以日本为最多,平均每年占37%。其余各国,英国占13%,德国约占10%,美国约占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典、挪威为世界著名产纸国,但输入中国者,反在德、美之下”。[6]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绝大部分时期,日本一直是我国洋纸进口的重要来源国,并长期位居各国洋纸对华输入额的首位。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经济濒临绝交,日本在华贸易地位亦为美国所取代。“而日本洋纸暗中活动,倾销如故。此虽日商手段之恶劣,实亦我国纸业衰落有以致之”。[7]但不管怎样,日本洋纸对华输入额毕竟有所减少。如广州市即因“自对日经济绝交后,日纸来途顿绝”,而陷入困境。幸亏欧洲洋纸在对日风潮发生不久后多已到达,方得以解困。[8]这说明事变发生后,欧洲洋纸取代了日本洋纸在广州的销路。到1932年,日本对华之纸张输入额较上年减少11425266两,计减退67.96%,尚不及1931年输入额的三分之一。[9]但此后数年,日纸进口额又复增加。据制纸联合会调查统计,1935年上半年日纸向我国中部及其它各处输入额,较1934年同期增加15430070磅。“然比较九·一八事变及日货排斥以前,依然低落”。不过,随着1935年下半年中日关系的变化,输入额顿呈激增状态,创“九·一八”以来最高纪录。[10]
二
至于国内方面,各地对上海的纸张供给约可分为两端:一是上海及国内其它城市所产的机制纸,二是由我国东南各省输入的手工纸。光绪十七年(1891年),李鸿章等始创伦章造纸厂于杨树浦,遂启我国新式制纸工业之端绪。厥后七年,中西人士又合资创设华章造纸厂于浦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龙章造纸厂又开业于龙华。此后十年间,这三厂“虽以营业失败,迭更组织,变易厂名,而绝无继起之新厂”。但到1919年后,在纸板业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江浙两省制纸工业争相崛起,上海竟成造纸厂亦于此时设立。后因日制连史、毛边输入甚巨,1925年乃有江南制纸公司之成立,以期抵制日货。1927年民生造纸厂继起,采用机器仿造国纸,目的亦大致为此。[11]江浙之外,其它通都大邑也相继仿设。据唐凌阁的调查,“全国机器纸厂,资本在四十万元以上者,计有十一厂。分布上海、汉口、济南、武昌、苏州、杭州、嘉兴、香港、吉林、江西、永修等处。”其中,上海各厂如龙章等,所产以连史纸、毛边纸居多,主供包裹书写之用。[12]其余各地机制纸厂,所产纸类亦多有输入上海的。到1936年,全国共有造纸厂36家,而上海一地就有11家,占全国厂数的28.2%;产纸量2.7万吨,占全国产量的27.65%。[13]虽然国产机制纸品质难敌洋纸,售价亦复高昂,但因社会各界对于国货运动的提倡,故其在上海纸市颇有可观的需求。尤其是机制连史纸、毛边纸虽于教科用书上略嫌粗糙,但在其它领域却是甚受欢迎。
三
手工纸为我国历来袭用之旧纸,虽呈日趋衰落之势,然亦不可忽视。“我国手工造纸,以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四省最为发达,湖南、广东、安徽三省次之。”至其种类,可分五种:竹纸类、皮纸类、稿纸类、反故纸类及其它。[14]在国内外机制纸的冲击下,本国手工纸被迫退出传统的销场,日益集中在上等纸和下等纸的产销上。前者以适于中国书画用之宣纸等为代表,后者则以用途广泛之黄烧纸、表芯纸、草纸等居多。据1936年调查报告,宣纸“总产量每年约四、五千件,运往上海者约三、四千件,苏州、浙江七、八百件,汉口四、五百件,南京二、三百件”。福建毛边纸在上海也有销售。据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的物价统计图,1923—1932年上海福建毛边纸之趸售市价总体呈上涨趋势[16],于此可窥知上海毛边纸需求之一斑。草纸则因成本极低、原料易得,加之用途又十分广泛,故受洋纸之冲击较小,而在上海纸市尚有其销路。据褚玉如的调查,上海在江苏宜兴设有草纸行,常派员赴乡收购。如无人来乡采办,则由农民自己运出。细货常销往上海、杭州等处,粗货则运至上海、苏州等地。至于土纸中之表芯纸、黄烧纸、纸箔等迷信用纸,实为一般宗教信徒之必需品,上海市民亦复如是。如在抗战前,浙江所产之迷信纸多赖京沪及华北一带为主要销场,即为一证。可见,虽然在机制纸的竞争下传统手工纸的销场日益缩减,但仍在某些特殊领域有着一定需求。
结语
抗战前的上海不仅是我国新式文化的中心,而且工商各业素称发达,内外贸易十分频繁。大量书刊的印刷和出版,频繁的贸易往来和货物购销,构成了当时上海纸张消费的主体。供应上海的纸张,既有来源于欧美和日本的洋纸,又有来自上海本地和国内其它城市所产的机制纸以及本国出品的部分手工纸,但以前者为大宗。在国外洋纸和国产机制纸的双重竞争下,土纸在上海的传统销场日益缩减,最终只得集中在上等纸和下等纸的产销上。
[1]中国之造纸业[J].中外经济周刊,1924(61):5.
[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195.
[3]我国输入洋纸及洋纸工业[J].中外经济周刊,1923(5):4.
[4]费炳章.各国在我国之纸业观[J].钱业月报,1922,2(11):15-16.
[5]王云五,蔡元培主编.中国经济地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92.
[6]陈晓岚.中国造纸工业之发展问题[J].东方杂志,1934,31(7):119-120.
[7]经济研究室.最近我国造纸工业与洋纸进口状况[J].中行月刊,1934,8(5):6.
[8]洋纸来途日盛[J].农声月刊,1932(153):51-52.
[9]日纸输入锐减[J].检验月刊,1933(3):15.
[10]去岁日纸输华锐增[J].国货月刊,1936,3(1):16,21.
[11]上海之纸业(一)[J].社会月刊,1930,2(10):56.
[12]唐凌阁.中国机器纸业调查[J].科学,1926,11(3):288-289.
[13]上海市造纸公司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造纸志[G].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11.
[14]魏天骥.江西手工制纸之现况及其改进[J].经济旬刊,1937,8(7):2.
[15]魏兆淇.宣纸制造工业之调查[J],工业中心,1936,5(10):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