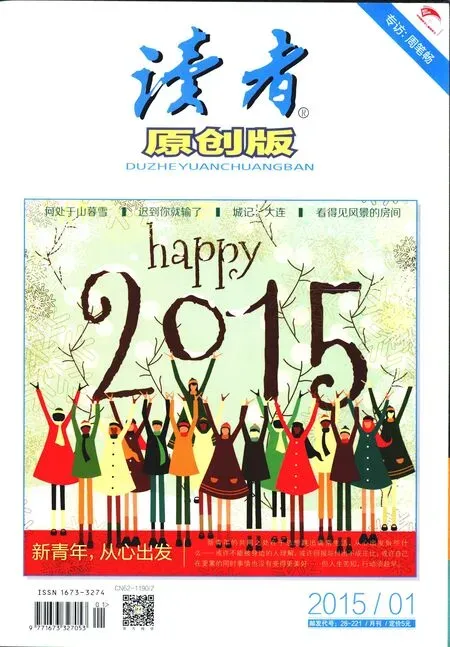我就是这样的“女汉子”
2015-11-29文_马曳
文_马 曳
我就是这样的“女汉子”
文_马 曳

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在沃尔玛买了一辆自行车,大约是便宜货的缘故,没骑两天链条就掉下来了。我去找楼下宿舍几个认识的美国男生帮忙,开门的是身高近两米的红发兄,他仔细听了我的情况,表示爱莫能助。然后,他去问了他的两个室友,大家都认为装链条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不过作为朋友,红发兄表示愿意帮我把自行车扛到约800米外的一家自行车行去。我婉言谢绝了红发兄的好意—那家自行车行的自行车至少卖1000美元,而我这辆车才50多美元,去那里修自行车的钱,够我去沃尔玛买一辆新车了。
但50多美元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何况还没有听说过有谁因为自行车链条掉了就把它遗弃的。于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我回想着当年高中校外修自行车的老大爷是怎么装链条的,就自己捣鼓起来。还别说,我折腾了半个小时,把链条给装上了!成功的那一刻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我成功地给自己省了至少50美元,悲的是我连自行车链条都能自己装上了,那还要男朋友干吗呢?
那时候还没有“女汉子”这种说法,我也还流于苏青式的顾影自怜:“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当时没有料到,日后我在美国自己装过宜家的大型家具,冬天在波士顿齐膝深的雪里推过车,还曾经开着卡车搬过好几次家。其中有一次,正逢我爸妈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爸得以坐着我开的卡车招摇过市。后来我妈偷偷告诉我,我爸为这件事耿耿于怀了很久,觉得美国生活太艰苦,以至于他从小惯大的女儿“居然要自己开卡车”。
坦白地说,我小时候挺希望找个能够在“武力值”上超过我一大截的男朋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向往的伴侣是那种比我高出一头,对我充满保护欲,令我肩不必扛、手不必提的男性。我以为,除了少数例外,这类伴侣往往也会有意识地希望自己的女友或太太遵守传统社会中女性柔弱顾家的角色设定,而这类角色,我觉得我演不来。
如果女人有能力,无论在经济、体力还是社交方面都不依靠男人生活,她会在婚前有更多的底气和筹码像男人那样问:结婚到底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何种改善?我有没有爱这个人到要和他共度一生?如果婚姻生活不能如她所愿,她也有能力离开那个人,把生活翻篇,重新来过。
现在对我有吸引力的伴侣模式是郭靖和黄蓉那样的:两人一起走江湖,各有各的本事。这也许是因为我嫁给Dududu后内心起了变化,也许是我按图索骥才找到了Dududu,年代久远,已不可考。
如果坐下来细细画张图,就会发现我和Dududu的确给我们的生活贡献了不同的本领。比如,我特别怕蛇,不管是在野外遇到蛇还是在路上碰见有蛇的海报,都会捂着眼睛,由Dududu做导盲犬带我离开;他怕蜘蛛、马蜂和其他一切奇怪的虫子,我们去乡下度假碰到虫子的时候总要我挡在前面;还有,Dududu完全不认路,而我恰好方向感极强,所以我经常会接他的电话来帮助“迷途的羔羊”。
有时候是我们的互补性发挥了作用,有时候又是相似性发挥了作用。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都在professional service(专业服务领域)工作,也因此以己度人,对对方时间的不可控性有更高的容忍度。我记得我们还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有一年恰逢情人节,两人都很忙,于是一通电话之后,约好晚上7点在两个办公室之间的茶餐厅碰面。那里既不需要排队,也无情人节套餐霸王条款,我俩每人一份鸭腿泡饭吃完,各自回办公室上班。因为都需要加班,这顿情人节晚餐还获得了公款报销,性价比颇高。
黄舒骏从前给张国荣写过一首歌,后来成为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那里面说:“你负责美丽妖艳,我负责努力赚钱,如果想倒过来演,我当然也不会反对。”
我猜,如果我问Dududu同样的问题,他也会说:“我愿意。”
这就是我想要的爱情。
图/是是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