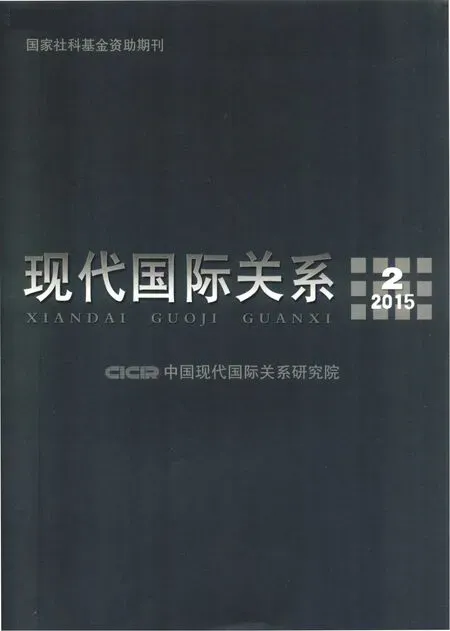2014年国际乱象评析:太阳底下原无那么多新鲜事
2015-11-2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达 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2014年的国际形势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是“纷繁杂乱”,很多没有想到的事情又“回来”了。一是近十几年显得“过时”的地缘政治竞争又回来了。美欧俄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对抗为冷战后所仅见;总说“坏也坏不到哪儿去”的中美关系,在上半年一度出现滑向“新冷战”的迹象。二是近3年似乎被削弱了的国际恐怖主义又回来了。“伊斯兰国”攻城略地,斩首人质,迫使美国组织空袭。三是近五六年来总是跟“衰落”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经济又回来了,其全年走势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此外,“埃博拉”疫情、油价“跳水”、“弗格森骚乱”,“占中”事件、苏格兰独立公投、东南亚重大空难……这一切确实给人空前混乱之感。
在这乱象之下需要思考的是,十年或二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望,2014年真的发生过什么让人记忆深刻的事吗?现在回头看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能称得上世界政治结构性变化的事件或许只有两件。一是“9·11事件”。恐怖组织对超级大国发动攻击,凸显了世界政治中权力分散的现实。世界政治中的权力正在从大国向中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人扩散。就国土安全而论,恐怖组织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绝大多数民族国家。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持续崛起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态势凸显了世界政治中权力转移的现实。世界权力重心正在持续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向中印等新兴国家转移。
从世界政治权力的转移与分散这两个结构性大趋势来看,2014年应该没有出现任何有结构意义的新变化。
在权力转移方面,有三个领域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是一个“并不新鲜的结构性变化”,这就是中美之间权力的持续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两国关系的紧张。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了美国。在中美权力逐渐接近的进程中,2014年划下了一个重要标记。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竞争面继续上升,2014年上半年两国之间围绕东海、南海、网络等问题,出现了紧张态势。不过,中美实力的接近及由此产生的紧张虽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结构意义,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新鲜,至少在过去五年当中一直如此。
第二个是一个“并不确定的结构性变化”。这就是美国经济的快速扩张。美国经济数字2014年表现靓丽,二季度增长4.2%,三季度增长5%,失业率降到5.6%,美联储也退出了第三轮量宽。与此形成对照,欧洲、日本经济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在中高速增长,其他国家则哀鸿一片。目前趋势持续下去可能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中国经济规模将继续接近美国,但追赶速度放慢;二是全球经济分化,中美经济规模与其他大国差距拉大。但是,经济形势总是有起有落,2014年这些变化能持续多久,现在尚难判断。这一领域的变化是否具有真正的结构意义尚不确定。
三是一个“佯装为结构性变化的新闻事件”。美欧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博弈在2014年博取了最多的新闻关注。但是就世界政治的结构意义而言,这一事件既不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不会根本改变大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国,但是其经济规模与欧、美、中差距颇大,从其人口与经济结构看,未来前景也并不乐观。同时,美欧、中俄确实因为乌克兰危机分别走得更近了。但是美欧本就是盟友,中俄本就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乌克兰危机只是使其分别走得更近。另一方面,美俄、欧俄仍互有需要,中美还在搞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也不会结盟。因此,乌克兰危机对这两组战略关系仅有程度的影响,而无性质的改变。
在权力分散方面,2014年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伊斯兰国”异军突起;二是非洲“埃博拉”病毒肆虐,并一度在美欧引起恐慌。这两个动向分别再次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当今国际安全中扮演的角色。不过,十多年前世界就面临着“基地”组织和“非典”疫情威胁。“伊斯兰国”与“埃博拉”疫情同样是“并不新鲜的结构性变化”。
太阳之下并没有那么多新鲜事。2014年的新闻事件也许不少,但并未出现2001和2008年那样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以上这些事件并未改变世界权力重心东移这一趋势;至于是否改变了东移的速度、“东升西降”是否在走向“中美二元结构”尚需观察;另一方面,这些事件并未改变世界权力分散的趋势。美国经济形势好转,但是其能够影响、控制的范围如果不是进一步缩小了的话,至少是并未扩大。美国无法靠空袭消灭“伊斯兰国”,也无法让伊朗、朝鲜弃核,更不能让俄罗斯“吐”出克里米亚。
至于2014年的其他事件,基本上只具有新闻价值,对世界政治的意义有限。东南亚空难基本上是偶然事件;美国“弗格森骚乱”、中国香港“占中”、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虽然反映了三国(地)内部存在的问题,但并不影响三国(地)总体政治稳定,也不大可能在2015年继续引起大规模连锁反应。油价下跌短期影响巨大。但是市场需求迟早还会上升,欧佩克国家对油价下跌也有一个可承受的底线。油价“跳水”这件2014年的大事,在2015年未必会成为更大的问题。
最后,世界秩序是否正在“从无序走向有序”呢?冷战结束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讨论秩序问题时,常使用“大调整”、“过渡期”等说法。关于格局有单极、一超多强、多极等多种观点,关于时代有“后冷战时代”、“后9·11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等不同提法。但是如果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一个秩序还没调整出来、一个时代还没过渡完毕,我们可能就需要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本身有什么问题?例如,在讨论世界秩序时,我们是否陷入了国家中心、大国中心、西方中心的思维定式?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后,国际秩序似乎就意味着世界秩序。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到雅尔塔体系,欧美强国之间形成的秩序逐渐统摄全球。但是如果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民族国家间形成的国际秩序就等于世界秩序,也许只是17~20世纪这300余年的“特殊情况”。欧美国家的秩序就等于世界秩序,也许更只是19~20世纪殖民时代与冷战时代的“特殊产物”。这正是基辛格2014年的新书《世界秩序》讨论的问题之一。今天,欧美国家已不能垄断世界权力,甚至民族国家也不再能垄断世界权力,世界是否一定要有一种可以命名的、具有几何美感的“秩序”?亦即是说,探讨、追寻21世纪世界秩序,其本身是否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由于世界权力的分散化,也许“乱”才是世界政治的“新常态”。无论如何,中国是一个新兴经济体,更是一个有着自己悠久独特文明的非西方国家。我们看世界,理应有我们自己的视角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