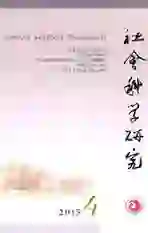钟嵘“寓言写物”的诗学意义
2015-11-27郭锋
郭锋
〔摘要〕 “寓言写物”是钟嵘给赋比兴的“赋”新增的一个特点。其中“寓言”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化用过来的;“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也在诗赋递变、赋体演化中由简单的“敷陈”变成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当这种方法再次回到诗歌创作以后,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缘情绮靡的特征,对寓言写物进行了新的整合,尝试着用间接抒情的方式来抒写读者心中的意,并突出其以形写神、文词典雅的特性。寓言写物是钟嵘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为唐宋诗学的发展导夫先路。
〔关键词〕 钟嵘; 《诗品》; 寓言写物; 唐宋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4-0201-05
钟嵘把五言诗歌三义兴赋比的赋阐释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学术界对此并不认可,陈衍说钟嵘“既以赋为直书其事,又以寓言属之,殊为非是”。〔1〕今人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没有注意到“寓言写物”背后深厚的诗学背景,仅仅从字面上阐释其含义,如曹旭“寓言,即‘寄言;寄托之言。”〔2〕张伯伟“其实,这里的‘寓言并非指有寓托的语言,而是说寓托或凭借于语言,亦即‘叙写之意。《诗品序》又云:‘今所寓言,不录存者。与此处‘寓言写物之‘寓言的含义是一致的。”〔3〕这些结论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解决钟嵘诗论的实质问题。笔者考察了赋比兴的发展历程,发现历代经学家把赋阐释为“直陈其事”,强调其“直陈”的特性;而诗学家则有意淡化其“直陈”的特性,强调“敷陈”的一面。其实,“敷陈”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但在五言诗歌创作中,间接抒情逐渐成为主流,于是钟嵘通过对兴赋比内涵的改造,转移或新增了一些特点,使其适合五言诗歌抒情写意的需要。“寓言写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引入诗学理论的。本文从寓言、写物的渊源流变切入,通过对钟嵘在寓言、写物之间取去心态的分析,揭示钟嵘诗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对唐宋诗学产生的实际影响。
一、寓言
寓言不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而是从早期辞赋的创作方法演化过来的。《荀子·赋篇》是现存最早的赋作之一。它的创作方法主要是隐语。朱光潜说隐语是“用捉迷藏的游戏态度,把一件事物先隐藏起,只露出一些线索来,让人可以猜中所隐藏的是什么”。 〔4〕《荀子》的“礼知云蚕针”五赋以及先王依荀子谜底制作的新谜,都具有现代谜语基本特征。谜语由谜面和谜底组成。谜底是谜语的核心部分,而谜面则从不同方面揭示谜底的各项特征,通过描述暗示等手段,引导读者逐步接近作者内心的意旨。宋玉《风》《钓》二赋也是早期的赋篇。它们采用了寄言的手法。寄言通过言在此而义在彼的方法展现作者内心的情愫。这种情愫包括字面意义和寄托意义,只有寄托意义才是作者着重要抒发的情感。《风赋》的字面意义是“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的对比,寄托意义则是讽谏楚王要关注民瘼。《钓赋》的字面意义是钓“三赤之鱼”和“钓天下”的对比,寄托意义则是钓天下开创太平基业。宋玉二赋的“寄言”,即曹旭所谓的“寄托之言”。
隐语和寄言都有“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特点。〔5〕相比而言,寄言的意义比较明显。因为从字面意义到寄托意义之间有一个必然的过渡。这就是对事物形状的描述。寄言是在形似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提升作者内心的情感。隐语则比较隐晦一些。作者有意设计迷局,扰乱读者的思路;读者处身谜局之中,也很难一下猜中作者的谜底。正因为猜谜不易,史书才对那些才思敏捷、善解廋语(隐语)的人物,不吝笔墨而大书特书。再从它们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来看,隐语对五言诗歌描写影响较大。五言诗歌从多个方面描摹事物形状,逐步揭示事物的基本特征,就是从隐语逐步揭示迷局演化过来的。寄言对五言诗歌的抒情方式影响较大,五言诗歌咏物抒怀多是通过寄托意义来实现的。寄托把触景所生之情,升华成诗人想要抒发之情。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从鲜花芳草到君子贤臣,从男女之情到君臣之义,从登高望远到家国之思,已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寄托情感的固定模式。
钟嵘之所以用“寓言”来概括隐语与寄言,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借别人之口说出作者想要说的话。相对而言,《庄子》寓言比二者特征更为明显。《庄子》寓言的特征就是“藉外论之”,典型的事例是:“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6〕按理说父亲是最熟悉自己儿子的,但父亲却不能给儿子做媒,因为父亲赞美儿子的话别人不信。可同样的话,如果从第三者口中说出,别人就会信服得多。庄子还分析了人在接受新观点时的一个特殊心态,“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7〕人在接受一个新观点时都是有选择的,总是先接受那些与自己相同的观点,排斥不同的观点。这种心态根深柢固,作家在创作时要学会适应对方的接受习惯。把自己要说的与对方可能会接受的观点比较一下,对那些别人不易接受的观点,适当改变一下表达方式。如果能把这些观点从对方口中说出来,效果无疑会更好一些。五言诗歌的创作实践也表明,直抒胸臆远不如从对方口里说出来效果好;写在纸面上的文字,远不如读者自己感悟到的真切!
仅就钟嵘所论赋的两个特点而言,直书其事属于直接抒情的范畴,而寓言写物则属于间接抒情的范畴。间接抒情虽不如直接抒情那样直截了当,却能超越时间地点、环境场景、情境氛围,抒发出含蓄隽永、意味无穷的情感来。五言诗歌《陌上桑》在塑造秦罗敷形象时就运用了间接抒情的方法,先从正面交代了“秦氏好女”的基本情况,接着运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渲染罗敷倾国倾城的美貌及惑阳城迷下蔡的独特魅力,使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会被她的美丽所征服。尽管作者对秦罗敷外貌的描摹极其详尽,但罗敷到底长什么样还是没说出来,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欣赏品味,创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罗敷来,作者成功地把自己所要塑造的形象通过读者阅读展现出来。王粲《七哀诗》之一的“西京乱无象”通过一个妇人把年幼孩子抛弃在草丛间的典型事例,使读者真切感受到汉末“白骨蔽原野”的凄惨景象,把思念明君贤主拯救苍生之情,也通过读者的阅读展现出来。
我国古代诗歌重抒情而轻叙事,一般不以塑造人物、叙述事件为能事,但在五言诗歌初起阶段,诗歌的形象性和叙述的完整性仍是衡量诗歌艺术的标准之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清新质朴、气骨刚健的建安诗歌,都具有鲜明的形象性或相对完整的故事性,而塑造形象、叙述故事又离不开间接抒情。五言诗歌间接抒情成分比先秦有明显的增加,被钟嵘称为“五言之警策、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的五言名篇,以及乐府名篇《战城南》、《十五从军征》、《东门行》、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等,都是通过叙述故事、描写景物、刻画人物形象抒发情感的,彰显了五言诗歌间接抒情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写物
“写物”是赋与生俱有的特性,但这一特性也在诗赋递变以及赋体演变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先由《诗经》中简洁明了的“敷陈”变成汉赋中铺张扬厉、庞杂繁复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再从“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回到五言诗中传神写意的“直书其事、寓言写物”。了解“体物写志”,对于认识五言诗歌的“写物”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二者繁简有别,但都体现了文人士大夫创作特有的才学化的风格。只是由于过分地强调才学,以致汉赋在体物和写志之间出现了诸多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汉赋有其特定的作者(待诏金马门的文人和朝廷的士大夫)、读者(帝王)和创作环境(西汉国力强盛的武、宣时期),这与作于昏君乱世的荀子屈宋辞赋明显不同。这些因素决定了它只能朝着歌功颂德、娱乐帝王的方向发展。汉赋一方面竭力褒扬皇权,赞美太平盛世的繁华景象,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溢美之辞与诗骚以来形成的讽谏精神相背离,于是汉代赋家往往在结尾部分画蛇添足点缀一段讽谏的内容。扬雄就是这类赋家的代表者。当创作上的激情与思想上的矛盾无法调和时,他只能选择“辍而不为”。班固则从扬雄的困惑中走了出来。同样是尊奉《诗经》的传统,但他把源自“十五国风”的美刺转为“雅颂”的褒美。在《两都赋序》中,他说西汉文人士大夫的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8〕班固第一次把汉赋(大汉之文章)抬到了上古三代文学的高度,应该说这个评价是空前的。自此以后,汉人的文学观念为之一变,歌功颂德就成了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与西汉赋家随心所欲、凭空虚构的溢美之辞不同,班固强调真实性和规范性。两汉大赋都是运用才学的,但运用才学的心态不同。西汉赋家随心所欲放荡而不羁,东汉赋家则循规蹈矩讲求出处。事实上,循规蹈矩比放荡不羁更需才学,也更显功力。
第二,汉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擅长书写宏大壮美的事物,但在把握这些事物时,采用了面面俱到、并列枚举的叙述方法。枚乘《七发》由音乐、美味、车马、宴游、校猎、观涛和辩论等七件事情组成,展现汉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字里行间充溢着汉人特有的博大心胸和豪迈情怀。七件事基本上是并列的。汉赋往往采用了《七发》式的齐头并进的结构模式,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把所叙述的对象分成若干类,逐类进行描述。如此以来,赋体结构一下子扩张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在驾驭语言上,汉赋也很有特色。大量运用排比句式,着力建构一种恢弘博大气势。司马相如《子虚赋》描写云梦景象,连用了十一重排比:“其山则……,其土則……,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其高燥则……,其埤湿则……,其西则有……,其中则有……,其北则有……,其上则有……”,置身其中,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上林赋》写天子上林苑的珍奇异兽、崇山峻岭、离宫别馆、奇花异草,连用了九个“于是乎……”,把相同或相近的事物分门别类汇为一编。汉赋的叙述方式多是粗线条的枚举,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主次分明、详略有序式的描写叙述。汉赋在创作上还呈现出某些程式化的趋向,从选题到构思,从分类到枚举,从叙述到抒情,都缺乏事物自身的特色,因而它的可读性并不强。经过西汉百余年的涵养,赋从不歌而诵、琅琅上口的美文变成了佶屈聱牙、难以卒读的晦涩之文。
第三,汉初辞赋并不以文采见长,直到汉武帝时才刻意追求文辞的华美。司马相如所说的赋家之迹,就是对文辞方面的要求。扬雄也说赋是“雾縠之组丽”,并称其为“女工之蠹”。 〔9〕左思称其为“美丽之文”。为了达到“文必极美”、“辞必尽丽”的目的〔10〕,汉代赋家自觉追求语言的典雅,其标志就是言必有据。不仅所写的事件完全是真实的,就连语言也是有根据的。语言有根据是指赋中的文字皆有出处,是前人典籍用过的词汇。自扬雄《蜀都赋》以后,描摹京都大邑之赋蔚然兴起。这些都邑大赋如同方志史册,广泛搜集与该地相关的掌故文献,细大不捐,竭泽而渔。或者出自前人的语典,或者化用前人的事典。汉人在赋的构思上着力不多,但在文献的收集上很见功力。赋因而成了典故的汇编,具有类书的某些功能。汉代赋家有意识地把各类典故组织在一起,通过故实的沿袭和改变来体现所描绘事物的基本特征。为了展现腹中才学,汉代赋家往往偏嗜一些冷僻典故和怪异文字。如果不借助笺注,简直无法阅读。汉赋是士大夫文学,一开始就摒弃俚语俗语、日常用语,改用骈散夹杂、骈俪对偶的书面语。或把同类的事物聚集在一起,上下两句表述同一个意义;或把不同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分别叙述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通过强调对比、重复夸张,指事绘形,穷尽写物之状。与才学结缘以后,汉赋表现力成倍的增长。
汉代的主要文学形式是诗赋。文人大赋和民间的五言诗歌,分别流行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据了美刺的两端,其间的共同性并不多。两汉以后,随着大赋的式微和五言诗歌的崛起,二者之间出现了一些必然的联系。从东汉中叶起,许多诗人也擅长作赋。五言诗歌在雅化过程中,汲取了汉赋的一些特点,五言诗歌的“写物”就是从汉赋“体物写志”演化过来的。它继承了汉赋“体物写志”的才学化特点,又克服了因才学化而形成的曲高和寡、流传不广的缺憾,成为一种能够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正统文体。五言诗歌的这种发展趋向,与钟嵘诗学理论的倡导有密切的关系。
三、寓言写物
赋是一种通用于各种文体的创作方法,当它再次回到诗歌以后,那些来自汉大赋的特点已不适用五言诗歌的实际。钟嵘根据五言诗歌的实际需要,对寓言、写物做了一番加工改造。
在经学家看来,赋是直接抒情的。但在五言诗歌的创作实际中,直接抒情的情形并不多见,绝大多数还是间接抒情的。钟嵘在赋直接抒情之外,新增了一种间接抒情的方式。这就是“寓言”。钟嵘的“寓言”出自《庄子》,但与《庄子》有所不同。《庄子》寓言是通过讲故事来阐释事理的,给自然界的动植物赋予人的情感色彩。五言诗歌也常常涉及动植物题材,但都不是用来阐释哲理的,而是抒发情感的。五言诗歌在抒情方式上与《庄子》寓言确有相近之处,这就是把自己要说的话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把诗人内心情感通过读者的阅读展现出来。诗歌抒发的不再是诗人的情感,而是读者阅读作品时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文学作品中所谓的“意”。“意”来自《孟子》。孟子最初谈“以意逆志”时〔11〕,“意”与“志”就分属读者和作者两个群体。“志”是作者内心的情感,而“意”是读者阅读作品时的感受。五言诗歌的“寓言写物”就是通过叙事状物,唤醒读者内心蕴藉已久的情感;或者通过对某个片段、某个场景的描写,触发读者丰富的联想。曹植《七步诗》巧妙设计了一个“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场景,把同室操戈、手足相残的残酷事实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2〕成为读者发自内心的呼喊!
钟嵘还根据五言诗歌篇幅短小、重抒情而轻叙事的特征,矫正了汉赋在体物写志上的一些偏差,把求大求全,并不精细的罗列枚举,变成简明扼要、生动传神的描写。五言诗歌写物以形尚巧似和语言典雅为特征。文贵形似是南朝文学发展的趋势之一,五言诗歌的发展适逢其时,也濡染上了这种风气。钟嵘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形似常常与神似相连。当时还没有“神似”这个词汇,于是钟嵘创造了一个新词“巧似”,称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诗歌“尚巧似”。笔者以谢灵运《登池上楼》为例,分析五言诗歌尚巧似的特征。这首诗歌描写了春天景象,开篇直接点题写登楼之所见:“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从大的方面写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景象。和煦的阳光祛除了冬日的阴霾,明媚的春日代替了阴冷的冬季。接下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13〕,从细小之处印证上句所写的景象。这两句被称为神助之笔〔14〕,其过人之处在于它前后两句过渡自然,把难以言喻的春日景象,通过一大一小、一远一近、一虚一实两幅画面刻画得清晰可感。与谢灵运山水诗特有的繁琐堆砌不同,这首诗思路清晰简洁明了,仿佛受禅宗影响的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一般。可见“尚巧似”,不仅工于写貌,还工于传神。
五言诗从“流调”上升为“正体”,经历了一个从大俗到大雅的转变过程。按照矫枉过正的规则,它比一般文体更讲究语言的典雅。钟嵘也不否认诗歌语言的典雅,但他不主张通过骈俪来达到典雅。这在当时是很特殊的。因为六朝是一个骈体文的时代,除修史、政论、墓志以外,其他文体都采用了骈体的形式,甚至连刘勰《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深的文学理论著作,也是用骈体文写成的。诗歌本来就是韵文,句式整齐,很适合用骈俪对仗的形式。谢灵运是当时的骈体文大家,王叔岷说他“才高词盛,骈俪之极,时流于繁芜”。 〔15〕如此以来,钟嵘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承认谢灵运诗歌的艺术成就,等于说自己的理论有缺憾;不承认谢灵运诗歌的艺术成就,则无法体现五言诗歌发展的实际状况。笔者发现钟嵘崇尚自然,但对谢灵运的评价也很高。不仅将谢灵运诗歌列入上品,还称其为“元嘉之雄”、“五言之冠冕,文辞之命世”,这又当如何解释?其实,钟嵘看待谢灵运的角度与我们不同。他忽略了谢灵运诗歌苦思运意、骈俪对偶、运用故实、人工音韵等不自然的因素。因为这些在当时很普遍,几乎每个诗人都是这么做的。他突出了谢灵运与当时盛行的玄言诗所不同的一个特点——天才自然。谢灵运处于玄言诗上升时期,也谈玄理,但与他人空谈玄理不同,他用自然来证实玄理。谢灵运笔下的玄理不再是一种空泛的说教,而是真山真水真性情。钟嵘把谢灵运诗歌的成就归之于博学多才天性聪明,他说:“若人学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16〕中唐诗论家皎然是谢灵运的十世孙,更是把谢灵运当做诗学典范。他评论谢灵运诗歌也是从天才着眼的,说:“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17〕皎然把谢灵运的成就归之为天性聪颖,受禅宗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悟性极高。钟嵘反对当时“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创作倾向,他从自然的角度,回避了谢灵运诗歌中不自然的因素。一般说来直寻直致、寓目辄书的诗歌,因措意不深而缺乏文采。钟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诗歌创作中引入楚辞一系,用来弥补因“直书其事”而造成的诗歌语言直白粗浅和立意不深。楚辞散句单行、不事对偶,同样也以文采著称。出自楚辞一系的诗人,都有文辞华美的特点。谢灵运即属于《楚辞》一系的诗人。《诗品》列入上品的诗人都很注重文采,而那些不事文采的诗人基本上处于中下品,如班固的“质木无文”,曹操的“古直”、陶潜的“质直”等。钟嵘论诗确实有“重华靡而轻质直”的倾向,其赋“也是很讲文采的,这就是气骨与丹采的统一”。 〔18〕钟嵘把典雅与自然联接起来,他的“自然英旨”中包含了许多文采的因素。尤其是把诗人后天学到的知识、技巧,也看成天性的一部分。这样,诗歌创作就少了许多人力工夫,而多了一些自然的成分。而这一点对唐宋诗学影响深远,成为宋诗理论创新的一个主要特征。
钟嵘继承了汉代经学的传统,用赋比兴来概括五言诗歌的创作方法。这种用旧瓶装新酒的表述方式,与日新月异、纷繁复杂的诗歌创作相比明显落伍了。于是钟嵘尝试着给它增添了一些新的内涵,使这些形成于四言诗的诗学概念,也能适应五言诗歌的创作实际,“寓言写物”就是这样被引入《诗品》序言的。钟嵘修订了五言诗歌在抒情方式,以及叙述状物方面文采不足的缺陷,用不自然的手段实现了自然的目的。而这一点对唐宋诗学影响深远,从钟嵘《诗品》的“自然英旨”,到中唐皎然《诗式》的“自然神诣”、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自然含蓄”、南宋姜夔《白石诗说》的“自然高妙”、宋元之际张炎《词源》的“自然而然”等,整个一部唐宋诗(词)学史都是沿着“自然”的轨迹向前发展的,而且方法思路与钟嵘如出一辙!在自然的名义下,包容了许多不自然的因素。相比之下,钟嵘毕竟处于诗歌雅化的初期阶段,他所主张的人力功夫还是很有限的,而他所反对人力工夫诸因素,如音韵对偶、苦思运意和化用典故等,先后被引入诗歌创作,成为唐宋诗学中一个个新的亮点。钟嵘把诗人后天学到的知识和通过训练掌握的技能也看作诗人天性的一部分,一举解决了困扰唐宋诗学几百年的一个难题——天性和才学的界定问题。唐宋诗学沿着才学化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直至形成所谓的正派体系。钟嵘的诗学理论在唐宋诗学体系构建中起着特殊的作用,而这一点还没有引起诗学界的重视。因此,研究钟嵘的“寓言写物”,对于深化中国古代诗学体系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陈衍.钟嵘诗品评议〔M〕//曹旭.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3.
〔2〕〔14〕〔16〕曹旭.诗品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6,171,91.
〔3〕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3.
〔4〕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2011:39.
〔5〕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539.
〔6〕〔7〕〔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948,948.
〔8〕〔汉〕班固.两都赋序〔M〕//〔梁〕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
〔9〕汪荣宝.法言义疏: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7:45.
〔10〕〔晋〕左思.三都赋序〔M〕.〔梁〕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039.
〔11〕〔清〕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7:638.
〔1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79.
〔13〕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64.
〔15〕〔18〕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669,28.
〔17〕李壮鹰.诗式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18.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