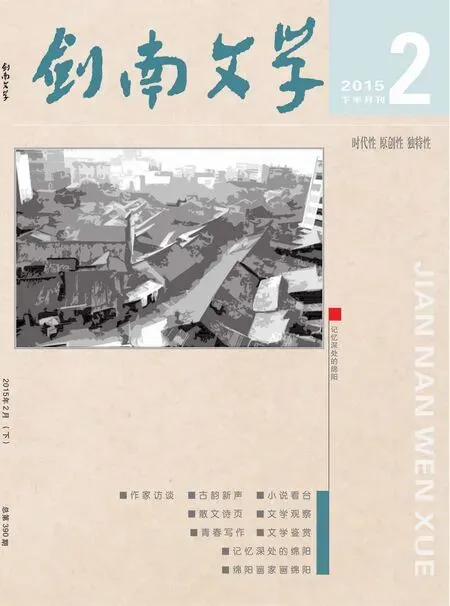恍若隔世(二章)
2015-11-22王德宝
■王德宝
衰老的锄头
父亲年轻的时候,那把锄头每天都和父亲在一起,敲烂板结的土块,或者挖出一些蚯蚓。锄头态度强硬,每天都要父亲低头和石头说话,和禾苗交流。多年下来,父亲对耕种和收获的理解,和锄头一样深刻而又坚决。
等我放学回家,天已向晚。父亲一边弹着身上的尘土,一边将锄头倚立在墙壁。那个时候,我看到锄头的面额晶亮,似乎想告诉我,这一天他和父亲一起去过哪里,做了些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锄头和父亲是什么关系。出门进门,我都看到父亲把锄头扛在肩上,样子非常亲密。
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满头大汗,腰酸背痛,都是锄头弄出来的;不知道父亲对锄头的热爱里,还掺杂着些许怨气。
农忙的时候,我也学着像父亲一样亲近锄头。
我把他扛在肩上,来到地里。
我挥动锄头。锄头始终扭扭捏捏地,不听我指挥。
我听到了土地嘲笑的声音。
锄头别扭,我也感到别扭。
远离锄头,这是父亲当时对我的用心。没想到锄头的想法也和父亲这么一致。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重重地放下锄头,才发现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已经长满了力不从心。
那把锄头也在墙角喘着粗气。曾经棱角分明的铁片,已经暗淡,秃钝。
父亲不去地里的时候,我经常看到那把锄头和犁铧们一起,在嘀咕着自己今后的日子。
父亲后来的日子和他的躯干一样,变得越来越萎缩,越来越弯曲。
偶尔回到乡下,和他谈起土地,发现他的话题里早就没有了锄头,没有了用锄头挖开的那些日子。话题里都是我不想听到的房子、车子和票子。
站在荆棘丛生的土地旁,我偶尔也会琢磨,那把锄头,后来会被我父亲送给谁……
酒里的父亲
酒是父亲的初恋情人。一接近父亲,父亲就忍不住张开大嘴,频频亲吻。
酒是父亲的化妆师。酒一出手,父亲苍白的脸上,就能腾起朵朵红云。
小时候,酒是经常闯入我们家的魔鬼。酒一进家门,父亲很快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和母亲吵闹,就是把我们叫过去,劈头盖脑地教训一顿。
时间一长,酒就成了母亲的眼中钉。父亲不在的时候,酒就会被母亲藏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角落,等父亲极尽温柔的言语,再次打动母亲那并不坚定的决心。
被我们反对的次数多了,父亲就改变了喝酒的方式。
再喝的时候,他总要约上一两个人。他们也是刚刚收拾完田地里的事情,挽起的裤脚刚刚放下来,他们也想给不甘寂寞的自己找点儿事情。
几颗花生米,一碟老咸菜,就蹲在缺了一条腿的桌面上,等他们用筷子或者指头来消灭。
酒这时就成了父亲的武器。父亲一举起酒碗,以前一直蜷伏在心里的自卑和惭愧就灰飞烟灭。
喝了再说。父亲双眼放光地看着其他几个人。其他几个人不敢去接父亲突然硬起来的眼神,在田间地头的那些嘲笑和蔑视马上离开桌边,从我们的门口溜了出去。
田边地角的那点儿事情哪用得着放进心里?更多的酒站在父亲的身体里,父亲觉得自己力大无比,说出的话也豪气干云。
其他的喝酒人听不下去了,陆续从父亲滔滔不绝的演讲里撤退。
父亲坐在已经空无一物的碗碟边,继续挥发着源源不断涌上来的怨气和豪气。
母亲这时就倚在门框上,等着被酒吹爆的父亲像气球一样瘪下来,然后扶他上床去休息。
父亲不喝酒的时候,总是在田地里,或者集市上。
这个时候,我总能看到密集的汗水,在他身上左冲右突,寻找逃跑的路径。
父亲在忙着打理一家人的生计。他知道我们的成长和生活,离不开他流出的汗水。
我站在旁边,总能隐隐地闻到,父亲奔流不竭的汗水里,有着酒一样的芬芳气息。
站得久了,我也会心动,也会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