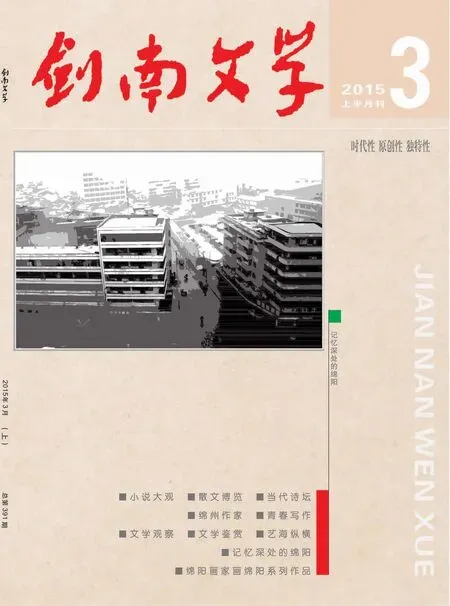《疾病解说者》中《森太太》的主题意义
2015-11-22■温琪
■温 琪
《森太太》一文选自裘帕拉希莉的小说集《疾病解说者》。“森太太”的人物形象是基于拉希莉母亲的形象而产生的,故事以一个美国孩子的视角呈现了美国印度裔族群在异质文化中的心路历程。本文则是着眼于从跨文化、文化疏离、全球化和婚姻家庭问题等方面探析《疾病解说者》中《森太太》一文的主题意义。
《疾病解说者》 是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第一部小说集,自问世以来,几乎囊括了美国所有的小说奖,其中便包括美国最著名的文学奖项之一——普利策小说奖,使其成为普利策小说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拉希莉自己就是一位处在祖先古老传统和美国新奇世界的传译者,《疾病解说者》便聚焦于再现游离于两种文化边缘的流散族群在异质文化中所体验的孤独、困惑、迷惘和失落。其中《森太太》一文中“森太太”的人物形象便是基于拉希莉母亲的形象而产生的,只不过,拉希莉是从一个美国孩子的视角来观察“森太太”的所作所为。
森太太是一个跟随丈夫移民美国的印度裔妇女,通过张贴求职广告得到了一份临时照看孩子的工作。被照顾的孩子叫做艾略特,只有一个无暇照顾他且生活糜烂的单亲妈妈。身处异国、无亲无故的森太太每天都穿着美丽的纱丽,尽可能得维护和保留着自己的文化,而来自家乡加尔各答的航空邮件和在海边市场买来的新鲜的鱼则成为她在异国他乡的精神寄托。森先生是一位大学数学老师,他与森太太的夫妻关系很微妙,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冲突最后的发生是在森太太学车的问题上,由于森先生没有时间,森太太只能自己开车去鱼市,却在路上发生了事故,这也最终使森太太适应美国生活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使夫妻的关系更加僵化。而艾略特则成为在两种文化冲击的大海上沉浮不定的森太太独自忍受漠视、被孤立、无助、绝望的见证者。本文则是着眼于从跨文化、文化疏离、全球化和婚姻家庭问题等方面探析 《疾病解说者》中《森太太》一文的主题意义。
一、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差异
森太太跟随丈夫移民美国,虽与故土和亲友分离,但文化的烙印却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身上,其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无不体现着印度古老又神秘的特有文化,而这种文化与美国充斥着新奇、繁华的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碰撞着。
小说的一开始便是对森太太和艾略特的母亲外貌衣着的描述。一位身披一件微微闪烁的、饰有橘黄色佩兹利旋花图案的白色纱丽,一位身着米黄色翻边短裤,脚蹬帆布鞋,暴露出剃净汗毛的膝盖和大腿,留着引人注意的又直又薄的短发。两者的家也有很大的差别,森太太家里的一切摆设尽可能地保留着印度的家的模样,十分温暖,艾略特的家却冷冷清清,只有一个便携式加热器。在艾略特的见证下,文化的差异还在继续:森太太和森先生进门前会脱鞋;森太太额头上的朱砂痣;森太太用刀片准备食材,喜欢买一整条鱼来做料理……
“文化就像一座冰山”,如冰山般露在水面的部分是能被看见的,如语言、服饰、烹饪等,而隐藏在水边下的则是文化的大部分,是很难被发现和理解的,它们便是文化的背景包括历史、信仰、价值观等。故事文本展示给我们的便是能被看到的部分,而其想表达的则是隐藏在水底的不同。印度和美国的文化源于不同的文化的模式。根据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的五个价值取向理论,在时间取向中,印度文化属于过去取向,这种取向的文化高度重视传统和历史,强调密切的家庭关系。美国文化属于未来取向,这种取向的文化注重变化,认为变化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而过去则是过时的,应当被抛弃。两种文化时间取向的不同解释了森太太和艾略特的妈妈上述行为的不同,也解释了在快节奏的美国生活中汽车文化的流行。根据吉尔特霍夫斯塔德的文化维度分析,印度文化注重集体主义,美国文化更注重个人主义。“如果我现在拼命叫喊,会有人来吗?”森太太曾这样问艾略特。在森太太看来社区和邻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印度,只要有人家办喜事,邻里所有的女人就会围成一圈说说笑笑地连夜切菜,谁家有什么喜事或是悲事,只要扯着嗓子一喊,所有的人都会来分享消息,安排帮忙。“他们没准会给你打电话,不过怕是来抱怨的,说你太吵了。”艾略特根据自己的经历这样回答。印度人将对集体利益的关心置于个人之上,对集体信任、忠诚、有归属感。“他们不寻求隐私,不试图隐藏情感,喜怒哀乐总是无所顾忌地表露出来。”美国人则相反,他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包括“自主动机、自主抉择、自力更生、尊重他人、个性自由、尊重隐私等层面。”这种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家庭关系,在印度,人们总是会“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即使是对待临时照看的孩子,森太太也会付出无微不至的关怀。然而在美国,单亲家庭不足为奇,人们会把老人送到疗养院,注重培养孩子独立,如在故事的最后,艾略特的妈妈没有再请保姆,而是给了他一把钥匙,告诉他“你现在是大孩子了”。
文化鸿沟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冲撞着每个人原有的文化体系,森太太、艾略特还有艾略特的妈妈都以自己的态度和方式理解着、尝试着、适应着。
二、文化疏离
文化疏离主要是针对移居者而言,指个体或群体对与自己熟悉的文化或生存地文化在 “感情和理性两方面都发生难以亲近的感觉”。作为流散族裔,森太太所遭受的是文化疏离是双重的:跟随丈夫移居美国,远离故土,对于自身文化,虽保留坚持,但在异质文化中却与自身文化若即若离、难以亲近;对于美国文化,则感到难以认同、难以融入,曾经的些许尝试也最终幻化为泡影。面对文化的差异和冲击,森太太饱尝疏离的孤寂迷茫、接触的安慰欣喜和丧失的绝望无助。
身处异国,森太太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每天只是守着自己心里那个印度的家,做着打扫、准备食材、做饭的家务事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与漂泊。对于外面世界的陌生和害怕使森太太很少没出家门,与这个社会隔离,她想念家乡的邻里乡亲、期待家人的来信、想尽一切办法买整条鱼、听家乡的拉伽音乐和录有家人声音的带子…… “比你的贝多芬还要悲伤,你说是不是?”“我能一路开到加尔各答吗?那该多久啊,艾略特……”她总是这样三句话离不开家乡,归属感的缺失流露出孤独和对家乡的思念。然而这种归属感的缺失不只体现在森太太身上,艾略特的妈妈是生活在自己国度的流浪者,她拥有着美国式的孤独和冷漠。美国社会热闹繁荣,但却不能抚慰心灵,面对生活的压力,她对一切心存戒备,把自己幽闭在自己的世界,喝酒、带男人回家,她用自己的方式细数着自己的孤独。而艾略特对自己妈妈的了解似乎还没有对森太太的了解深。从故事的描述中,森太太仿佛是带有阴影的暖色调,而艾略特的妈妈则是真正的冷色调,她将孤独隐藏得很深,直到自己也遗忘、麻木。“疏离感”中有一种具体表现叫做“社会孤独感”,森太太是流散者的缩影,艾略特的妈妈则是现代人的缩影。
在异乡漂泊的冷漠生活中,陌生人些许流露出的热情便让森太太感动不已。“那个人真不错,是不是,艾略特?他说是从电话号码本上查到我的名字的……你知道在加尔各答有多少姓森的人家吗?”鱼肆老板打来的一通电话,便让她有些得意,而每次买鱼时,她都会跟伙计有说有笑的,而照顾艾略特的这份工作则成为她与外界接触中最大的安慰,她对他倾吐着所有的感受。森太太仿佛就像一株含羞草,只要轻轻碰触,便会敞开心扉,可见她的孤独。
“艾略特,他们以为我过着女王般的日子……他们以为我按按按钮,家里就干净了。他们以为我住在皇宫里呢!”家乡的家人让森太太寄照片回去来展示一下新生活,他们以为森太太是幸运的,祝福仿佛变成了讽刺,如一把把的尖刀直直地戳向森太太的心,内心的酸楚只有她自己明白,到底是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为了森先生,她放弃了熟悉的一切,在情绪崩溃后,她将所有的纱丽翻了个遍扔在床上,“我是什么时候穿过这一件?还有这件?还有这件?”与社会的脱离,让再华丽的纱丽都没有用武之处。最后的车祸也最终导致她丧失了与艾略特的两人团体,也让她彻底丧失了作为养育者的身份,最后的心里慰藉也就此烟消云散。
三、身处全球化压力下的女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跨国移民的现象也日益普遍,身处全球化压力下的女人,一方面面临的是文化和身份的认同,一方面又面临着经济和地位的独立。
跟随丈夫移居美国的森太太首先面临的便是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全球化与跨国移民的双重背景下,要求她要具备 “双重忠诚”,于是她在保留“印度人”身份的同时努力适应“美国人”的身份,希望成为“世界公民”。纱丽、朱砂痣、身上散发出来的樟脑和孜然的特殊气味,她用着一切像他人诉说着 “印度人”的身份,她讲印度的风俗给艾略特听,用印度的特色小吃招待艾略特的妈妈……她也尽一切努力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在除了只有她和森先生的所有场合都说英语,尝试克服心理障碍学习开车,听贝多芬的音乐甚至在每天艾略特的母亲来之前销毁切过菜的所有蛛丝马迹,她假装成那个与她不符的身份,努力成为“美国人”。
由传统社会的妇女走向美国移民社会的妇女,对于森太太意味着从附属地位走向独立自主。移居异国,森太太处处都依赖着森先生,而张贴求职广告,从而得到临时照顾艾略特的工作,便是她走向独立的第一步。艾略特的妈妈曾一度在意森太太不会开车,因为会开车在美国是必备的技能。“森先生说有朝一日我拿到驾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觉得会吗,艾略特?会好些吗?”“你可以去好多地方,哪儿都能去呢。”这是森太太和艾略特之间的一段对话,只要森太太学会了开车,就不用再依赖森先生开车去买鱼,而且还可以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其生活范围也会变大,而这也将会成为森太太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标志。
但转变的道路总是充满艰辛,森太太一度迷失在“我是谁”的问题上,两次打击之后的变化也如出一辙:森太太不再做印度料理,而是给艾略特准备饼干抹花生酱——典型的美国晚餐。在学车的问题上,森太太虽然尝试但内心的抵触始终无法让她集中精神,最终在去买鱼的路上出了事故,也因此丢失了照顾艾略特的工作。在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的双重背景下,森太太不论是在文化和身份的认同还是在经济和地位的独立方面都以失败告终。
四、婚姻问题与生活在此情况下的家庭
森太太和森先生的婚姻和家庭是破裂的,故事虽没有明确提出,但从森太太对森先生如同陌生人的介绍“森先生在大学教数学”、俩人从未有过亲密举动即使是照相也会离得很远、从未有过过多的交谈即使是在森太太出了事故之后森先生也没有任何安慰中,我们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在印度的家长制社会模式下,妇女的地位很低,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这种情况虽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有所改善,但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在家长制的影响下,“男主外,女主内”是普遍的家庭观念,女性在婚姻中在经济等各方面都依赖于男性,由此导致女性的不独立、没有话语权。而森太太和森先生的婚姻和家庭状况更为特殊,不但深受家长制的影响,还承受着跨国移民的压力。在跨国移民中,森太太的移民是附属的,是跟随丈夫为了家庭的团聚而移民的。在此双重的影响下,森先生和森太太的关系仿佛更加尴尬:在美国男女平等的社会,要求女性独立自主,面对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森太太无法适应,其从事的是低层次的私人领域的工作——抚养小孩,对学车充满抵触;而森先生从事的是大学教授的工作,为了家庭,努力发展事业、融入主流社会,无暇顾及夫妻感情。夫妻间文化水平和意识形态的差距不断拉大,造成两人无话可说,仿佛是同居一室的房客。森太太在经济等各方面过度依赖丈夫,买鱼和来信等小事都要丈夫帮忙,使其在婚姻中处于劣势,然而森太太是十分渴望得到丈夫的关心,会因为一点点的关心而心满意足、高兴得不知所以:“森先生随便说什么,她都笑”。婚姻地位的不平等、相互的不理解和不沟通是最终造成森先生和森太太婚姻和家庭不幸福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由艾略特妈妈为代表的美国式婚姻和家庭似乎也充满着不幸,文中对艾略特父亲的描述只有一句 “他住在2000英里远的地方”。艾略特的妈妈虽有自己的工作、汽车和房子,经济等各方面都十分独立,但过分的独立使其不从属于家庭和丈夫,为了工作和人际关系缺少对孩子的关爱。
五、结语
作者裘帕拉希莉祖籍是印度加尔各答,也是《疾病解说者》中众多主人公的家乡或故事发生所在地。拉希莉自幼便随父母移居美国,从家庭中承袭了印度古老传统的同时又深受西方社会的影响,在故事中,拉希莉便成为了这些穿梭在两种文化、两种世界的精神孤儿的代言人,《森太太》的创作更是基于其母亲的形象:本为印度人,却用异国语言在异质文化中将 “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差异”、“文化疏离”、“身处全球化压力下的女人”和“婚姻问题与生活在此情况下的家庭”这四大主题书写得淋漓尽致。
本小说集名叫《疾病解说者》,其反映的每一个主题都被作者比喻成一种“疾病”,而《森太太》一文中的“疾病”并不是美国印裔人民独有的,也不是流散族群的专属,而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其反思的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探讨的是人类心灵的共性问题。然而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并不存在可以“药到病除”的良方,也许唯有“宽容和理解”才能抚慰人类满是疮痍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