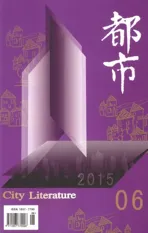在平凡的世界上寻找自己
2015-11-22杨遥
杨遥
在平凡的世界上寻找自己
杨遥
2015年春节,我特别想找一个人聊聊,她就是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人们都说世界已经成了平的,地球成了一个村落,但是我没有办法联系到她,而且想即使找到她,能说些什么呢?她说的英语,或者伊博语,我听不懂。我说的中文,她也一定听不懂。一种巨大的无力的感觉攫取了我。我只好再次读她的小说集《绕颈之物》。
这次春节回乡下,尽管老家屋子里有我以前留下的十几袋子书,但还是带了两本。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一本是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绕颈之物》。这两本书2014年都已读过,因为喜欢还是再次带上了它们。遗憾的是没有读《地下室手记》,《绕颈之物》却每天一篇读了下去。读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国王,幸福地每天听着山鲁佐德讲故事。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小说我都喜欢,几乎都能找到生活中相似的情节,或自己有过表达这种主题的冲动。《上个星期一》里面,刚从尼日利亚到美国的卡玛拉,在白人家做保姆。女主人崔西称赞她牙齿美丽、身体好,问她愿不愿意为她脱下衣服当模特?卡玛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战栗和兴奋中下定决心为崔西当模特时,孩子的法语教师来了,女主人赞美她眼睛漂亮,问同样的话,“你给艺术家做过模特儿吗?”“你应该考虑一下。”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杨遥,我喜欢你。他的语气和眼神是那么真诚,让我很感动。因为在我眼里,他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我喜欢他的小说。后来,看到他对许多人都这样说,我喜欢你。在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小说读到与我的朋友相似的人物,我觉得世界真是一个村子了。尽管她出生在尼日利亚,后在美国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在她的《猴跳山》中,那些在非洲作家写作营中的年轻作家和我们日常参加文学活动时多么相似,讨好权威或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编辑、评论家,践踏自己的伙伴,想突出表现又装出清高的样子。《一号牢房》《个人感受》《赝品》《幽灵》等篇章中,人物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恐怖的袭击下,或者在美国别墅中,领取退休金的大学校园里,他们都追求人的尊严,坚守纯真的理想,让人在绝望之中无处不看到光。这个1977年出生的黑人女子,让我刮目相看。对于那些长久沉睡的大师们,我永远心存敬意,但我更愿意和我年龄相近,比我厉害的人物相交,我等待相逢的一天。
这些年读了一些书,真正让我觉得好的,是那些能穿透时空,折射不同时代的作品。记得读卡夫卡的《城堡》时,我在一个小城市借调,每天埋在没有尽头的材料里,平均一个星期有一天通宵加班。三年时间,单位每年都要进人,进来的人可以啥都不干,就因为他们都有好亲戚。我却调不进去。感觉自己就是土地测量员K,用尽一生在等待。
读到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时,世界仿佛在我眼前重新打开一扇窗口,一下发现风景原来可以如此眺望。善与恶、灵魂与肉体、寻常与怪异等之间关系和我以往认识的截然不同,但觉得都准确。现代世界,人真的是分裂的。
2014年读完《金瓶梅》,猛地感觉到中国语言多么鲜活而富有活力。潘金莲、应伯爵等人说的话简直就是艺术品,而且完全生活化,没有半点书卷气。里面许多的方言俚语我们那儿的人现在还说,而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却看不到了。于是,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这些话一一摘录出来。读《金瓶梅》让我认识到我们的科技发展了,GDP提升了,但国人的习性似乎一直没有变。潘金莲作为西门庆的六老婆,为了笼络一个仆人,自己又没有钱,只好答应给他做一双鞋。至于其他达官贵人相交,莫不以“礼”先行。
再说伟大的托尔斯泰。读《战争与和平》,开头几章就让我从皮埃尔、安德烈、陶洛霍夫、尼古拉等人身上看到熟悉人的气息和举动神态,这可是十九世纪初的事情,托尔斯泰是怎样做到的呢?在这部伟大的作品里,他几乎写到了人类能表现出的所有的感情,又到那么细腻、准确,他像创造人类的上帝。托尔斯泰对战争的态度,让我想起世界上许多优秀的战争题材小说,如《裸者与死者》《亡军的将领》《活下去,并要记住》等,他们无一例外地反对战争,向往和平。尤其是读到库图佐夫带领俄军步步撤退,甚至放弃莫斯科的时候,我荒谬地觉得托尔斯泰比国内任何一位作家写抗日题材都写得好,尽管中国抗日战争比《战争与和平》出版晚近百年。这也再次印证了好的文学作品是超越时代的,而不是仅仅反映当时的时代。
而读《地下室手记》,让我想起自己和身边的一些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坦诚和深刻,让人震惊。小说中的“我”说自己是一个病人,与周围格格不入。他把自己比作苍蝇、鼻涕、臭虫,他用最低的姿态往上看,看到了真实、残酷。真的力量让人震颤!
读这些作品,觉得时空和地域仿佛不存在,无论怎样孤单、寂寞、落魄、卑微,总有那么几束光在温暖自己,在告诉自己要坚持。
阅读的同时,这几年也去了一些地方。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古镇、古城。记得不知道在哪个景点,第一次看到陶笛、烟斗、打火机、手工织的披肩等工艺品时爱不释手,一家挨一家看、摸、玩,但当把这些景点都转了之后,发现乌鲁木齐和鼓浪屿卖的东西大同小异,全国的每一个古镇几乎都是陶笛、烟斗、打火机等玩意儿。再也没有了新鲜感。于是想起2011年在鲁院读高研班时,有评论家说当代小说严重同质化。当时自己坚决不同意,认为评论家没有认真读当代作品。就在当时的鲁15班,我看到的同学们的作品也不一样,何来同质化?但是游过这些景点后,觉得确实是同质化,只不过甲作家是生产烟斗,乙作家生产打火机,丙作家制造披肩。放在一个地方很有特点,放大到全国,非常一样。于是我想,怎么能写出些别样的东西,像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品,穿透时光和空间,不管后来有多少模仿者,它们还是独一无二、熠熠生辉。
2015年清明节,我回老家上坟。坐在绿皮火车上,周围大都是农民或农妇。他们扯开嗓门说话。他说:“我儿子在老家开着个饭店,想增补点收入。”他说:“今天人真多,抡抢舞剑的到处都是人。”一个女人说自己的孩子,“她脾气可倔了,一说话就是‘就不’。”……“增补”、“抡抢舞剑”、“就不”听到这些熟悉的词语,我仿佛已经回到了家乡,呆在一群乡亲们之间。好像看到了《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应伯爵。这么多年,我在寻找的过程中,遗失了多少东西。
如何在平的世界上寻找自己?向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学习,从我熟悉的地方和人群中寻找。
责任编辑 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