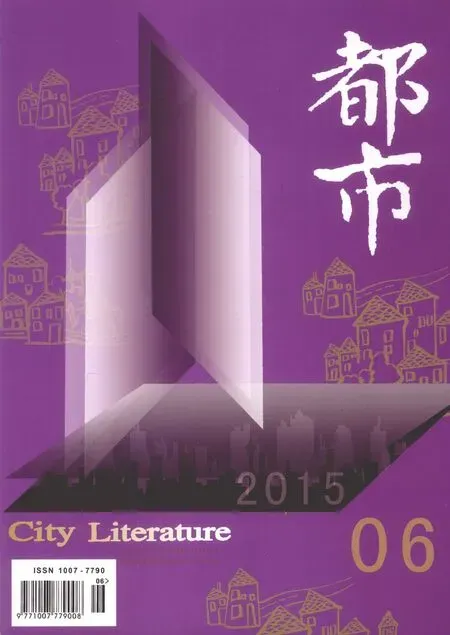散文二题
2015-11-22李元红
李元红
散文二题
李元红
历史的慷慨——从白堤、苏堤到韩江韩山
历史对名人好像总是十分慷慨的。譬如杭州的“白堤”和“苏堤”。因为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做过官,历史就慷慨的把冠名权给了他们。倘若是无名之辈,可能就无缘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了。
“白堤”并非“白公堤”,它原名“白沙堤”,为了贮蓄湖水灌溉农田而兴建,早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就已经以风光旖旎而著称。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在旧日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修筑了一条堤,称为“白公堤”,可惜的是,这个真正的“白堤”如今已经无迹可寻。
但这没有关系,一千年来,人们依然乐意亲切地把“白沙堤”称作“白堤”,把这个荣耀的光环无怨无悔地、发自内心地戴在白居易的头顶。以讹传讹也好,将错就错也罢,或者有意为之更好。总之,一个普通的“白沙堤”与白居易联系在一起,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美好的想象,更富诗情画意。名胜更需名人捧,“白堤”瞬时变得天下闻名。当然客观地说,白居易不仅是名闻天下的大诗人,还是一个做实事的好官。他在杭州做刺史时,修堤筑坝,防旱救灾,灌溉农田,赢得了百姓的爱戴。“白堤”,不仅是名人效应,我觉得,其实,是百姓对他的一个褒奖,一个长久的念想。至于这是不是真正的原址,又有何妨!
当然,白居易与“白沙堤”也并非毫无关系。当年,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流连于西湖美景,漫步白沙堤上,曾写下了“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的美丽诗句。有诗为证,“白堤”就更加顺理成章、有据可依了。“白沙堤”之为“白堤”,一字之少,却增添了无穷的妙味。
“苏堤”,则是名符其实的“苏公堤”。距白居易任杭州刺史的265年后,苏东坡来杭州任知州,他以白居易自居,为民,务实。积极疏浚西湖,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堤坝。这就是那个名扬天下的“苏堤”。
苏东坡曾两次在杭州任职。1071年,36岁的苏东坡上书神宗,议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奉命通判杭州,他在这个相当于副市长的职位上干了三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就写于这个时期。16年后,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在京师的苏东坡官场依然不顺,遭新旧两党攻击,54岁的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杭州任知州(公元1089—1091年),做了一把手。当时西湖的情况十分糟糕,湖面因杂草淤塞而大面积缩小,面临湮废的边缘。苏东坡作出了全面整治西湖和兴修杭州水系的计划,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的疏浚。苏东坡发动杭州军民以工代赈、疏浚西湖、沿湖筑堤。苏东坡不辞辛苦,几乎天天到工地察看。由于上下齐心,仅用半年时间就完工了。共挖淤泥925万立方米,花了20多万工。“苏堤”由此诞生。
如今,苏公堤上,游人如织。新柳如烟,春风和煦,百鸟和鸣,意境动人。然而,人们在享受这美景之时,一定会更多地想起苏东坡,想起这位可爱高贵的大文豪,想起他扑下身来为民办事的高大形象。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曾写道:“我简直不由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火命的苏东坡,也正是人们所敬重的苏东坡。“苏堤”之所以千年传颂,包含着百姓太多的情愫与眷恋,它是由心而发、自然形成的一种亲切的称谓。这与当下许多地方拼命争抢名人故里、名人墓地,甚至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所谓名人,进行人为地炒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韩愈。他比白居易大4岁,算得上是同龄人。而比后来的苏东坡,两人则相差269年。
唐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奉迎佛骨于长安,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昌黎上书《论佛骨表》,极言其弊,触犯龙颜,被贬偏僻遥远的蛮荒之地潮州任刺史。韩愈起八代之衰,蔚然文宗,而仕途坎坷,前后三贬,尤以这次天命之年贬黜岭南为甚。51岁的韩愈,在仕途上遭此重创,心力交瘁,悲苦绝望。而且路途遥远,辛苦异常。他自京师至潮州贬所,颠沛百余日。当他来到陕西蓝田县蓝田关时,漫天大雪,山路难行。韩愈对前来相伴的侄孙韩湘留下了遗书般的诗句(《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谁知宦海沉浮,世事难料,韩愈在潮州任职仅八个月,于第二年正月,调任袁州刺史。很快,九个月后,于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奉诏调回京师,先后就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朝廷要职。这是后话。
韩愈潮州任职仅八个月,却留下一段江山为之易姓的千古佳话。
韩愈以戴罪之身,在潮八个月,并没有消极颓废、“痛哭罔暇”。而是恪尽职守,不辞辛劳,一心一意为民办事。
韩愈做的头一件事是驱鳄鱼。他到潮州上任后,即询吏民疾苦。当他了解到恶溪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时,立即采取措施。他命属下将一头猪、一只羊投入江中。亲自写了篇《祭鳄鱼文》临江致祭。历数鳄鱼不安溪潭、与民为害的罪状,责令鳄鱼限期离开,否则尽杀乃止。此文既义正词严,又诙谐有趣。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归容,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据新、旧《唐书》记载,韩愈祭鳄当晚,暴风起于溪中,翌日江水尽涸,鳄鱼南徙六十里入海。这个记载虽有传奇色彩,但由此可以看出,韩愈的祭鳄、驱鳄行动,却是深得民心的。
韩愈到潮州的第二件事是兴学育才。他经过调研发现“此州学废日久”,感到痛心,于是他捐已俸百千(相当于他在潮州任职的全部俸禄)作为办学资金,又大胆提拔乡贤赵德为县尉,主持州学。其功德正如一副古联所称赞:“若无韩夫子,人心尚草菜”。
韩愈做的第三件事是劝农、释奴。韩愈治潮,十分关心农桑。他在潮州写的五篇祭文,多是为民祈雨,祈晴的内容。天旱少雨,他写《祭大湖神文》《祭城隍文》,为百姓祈雨。阴雨连绵,他写《又祭止雨文》。显示了他关心农桑、为民解困的至诚至爱。潮州当时有逼良为奴的陋习,这是唐代法律所禁止的。韩愈为掠卖的奴隶赎身,又颁布赦令,使他们成为自由人。劝农释奴是韩愈受到潮州人交口称赞的一个善政。
韩愈在潮仅八个月,却政绩突出,深得民心。正如韩祠中的一副对联所写:
“天意启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
潮州人民感念韩愈。他们慷慨地送给韩愈三件礼物:
——城北的笔架山改名为韩山;
——山下的鳄溪改名为韩江;
——为韩愈修建了韩文公祠。
可见,历史的慷慨,不是惟名是图,而是看你是否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事。历史不会谄媚,不会无缘无故地去讨好什么名人。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在潮州韩文公祠,赵朴初先生的诗句赫然入目: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圣教序》的诞生
早就想以“《圣教序》的诞生”为题写篇文章,但一直找不到下笔之处。
思来想去,还是先捋捋脉络,对《圣教序》的诞生过程有一个粗线条的把握: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西域取经,历时十七年,取回657部真经——唐太宗李世民命玄奘在长安弘福寺译经——三年后经玄奘再三请求,太宗为所译经文亲撰《三藏圣教序》,并命太子李治撰写《述圣记》——弘福寺怀仁和尚用25年时间,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将《圣教序》《述圣记》及玄奘所译《心经》三部分内容,一千九百多个字,集字而成,并刻制碑文。咸亨3年(公元672年),完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圣教》书法,为百代楷模”(明王世祯)。《圣教序》,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崇高地位,虽为集字,却被公认为是书圣王羲之书法之集大成者,开集字之先河,是书家必临之经典。用“诞生”一词,自是出于对这部书法经典的仰视。不用此词,不足以表达我的敬重之情。今天,我们坐在书房,品茗论道,可以悠闲地领略这部经典书法的无限妙趣,应该抱有深深感激之情。1300多年前,如果没有玄奘西域取经,没有皇家对佛家的重视,没有李世民极度地喜爱王羲之,没有怀仁和尚25年执着地努力,没有刻成碑文,等等,等等,没有这些机缘巧合,就不会有《圣教序》的出现,后人也绝无机会欣赏到这件艺术极品了。
我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古人会把许多重要的文字刻在碑石之上。千百年来,火烧水淹,无数纸质的东西丢失、毁灭,它们在历史的风霜面前,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随着这些纸质文本的佚失,上面承载的各种信息也随之烟消云散,让史学家们、书画家们常为之叹息。而只有石碑,在历史的强力冲刷下,显得是那么坚固和顽强。《圣教序》的得以留存至今,就是最好的例证。据说,王羲之的墨迹,到了明清之际几乎一无所存。而《圣教序》碑石尚在,善本犹存,成为保留王字最多的碑文,也成为研究王字最重要的资料。
应该说,《圣教序》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传奇。是关于坚韧、信仰和传承的一个传奇。
我最想说的是怀仁。一介僧者,念经事佛之外,用了25年的时间默默地做了一件事:集字圣教。据说他是一位擅长王羲之书法的名僧,还有人说他是王羲之的后裔。虽然关于怀仁和尚,史书记载寥寥,但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他名垂史册。有人把他和玄奘、书法家怀素、东渡日本的鉴真并列为唐代四大名僧,我觉得应是名符实归。这是一项异常艰难浩繁的工程。怀仁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收集王羲之书法真迹。大约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唐朝内府所藏,二是从散落于民间寻找。据说仅收集王书真迹的工作,就用了18年。民间传说此碑又叫“千金碑”,因为怀仁到民间购求王羲之真迹花钱太多,大约花了千多金,故有此称呼。收集真迹自然是要尽量的多,甚至要尽可能的全。这是决定集字成败的基础。之后,还要对所有收集回来的作品进行整理和甄别,去伪存真,归档分类。虽然没有资料证明怀仁收集真迹的具体数字,我想数量一定是相当庞大的,因而怀仁付出辛苦也可想而知。有人说,怀仁是王羲之的后世子孙,是大书法家。我想,怀仁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大收藏家,大鉴赏家。他对王羲之的书法一定是吃得极深极透。相对于收集真迹来说,集字工作可能需要更大的技术含量和艺术感觉。《圣教序》一千九百多个字,要从成千上万的真迹中,遴选中最贴切的字,做到自然流畅,气息贯通,富有变化,韵味高雅,真正体现王羲之书法的风貌,使之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实非易事。事实上,怀仁确实做到了。《圣教序》被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集字碑刻,也是水平最高的集字作品。其集字的工程量之巨,难度之大,历时之久,均达“之最”程度,堪称我国书法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最为宏大和伟大的文化工程。号称天下第一书法工程。
当然,从书家专业的眼光看,《圣教序》并不是完美无缺。因为整幅作品不是作者本人一次性书写而成,而是从已有的真迹中选择较恰当的字集字,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贯气的瑕疵,个别字偏大,有跳出来的感觉。有的字多次重复使用,会有雷同之感。还有极个别字因为找不到原字,可能会有两字拼接成一个字的现象,甚至还会有怀仁自己按照王书风格写成的。据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考证,《圣教序》的字可分为三类。一是鉴真(证实确实是摹自真迹);二是存摹(属于怀仁加入了自己意思);三是存疑(在钩摹或刻石的时候已经走了样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照相机,没有电脑和软件,没有任何科技手段,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完成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圣教序》开创了书法集字的先河,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历来为史界和书界所公认。不完美也是美,是历史留下的遗憾的美。人们不会苛责怀仁。有的,只是深深地敬意。
我想,怀仁和尚既是一个虔诚的佛家弟子,更是文化传承的苦行僧。或许,也只要他这样的一种身份,才有可能完成这件浩繁而持久的工程。官员、文人或者他人,都不具备条件。没有家庭的拖累,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官场的浮沉,没有名利的羁绊。而该有的,比如信仰的执着和虔诚,对书法的敬畏,对名利的淡泊,他都有了。于是。这个历史重任,自然地落在他的身上。而他,也不负使命,终成正果。《圣教序》的诞生,怀仁居功厥伟。
我第二个想要说的,是玄奘。他十七年含辛茹苦,西城取经。回国后,全力主持译经,翻译了许多重要佛教经典。他是中国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对弘扬佛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我要说的,是他在促成《圣教序》这件事上的巨大贡献。为了取得皇帝的重视,他先后两次上表,请求太宗赐序。贞观二十年,玄奘将《大菩萨藏经》二十卷、《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及翻译完成的《诸经论》呈给太宗皇帝,并请皇帝为《诸经论》钦赐序文,未允。玄奘并不气馁,又一次上表:“陛下英才盖世,玄奘冒犯,恳请赐序”。三年后,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太宗终于答应作序。并于当年御制序文撰写完毕,还敕命皇太子李治写了一篇《述三藏圣记》。一年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因病驾崩。如果再迟缓一年,这事可能就黄了。李世民皇帝和皇太子作序和记,这是天下第一大广告。它对于弘扬佛法自是非同小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玄奘确实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人物,极具政治眼光和远大谋略。这还不算,如何让《圣教序》昭示天下、传之后世。玄奘一定是进行了深思熟虑和精心谋划。他知道,唐太宗对王羲之极度喜爱和推崇,为了进一步博得皇帝的垂爱和支持,玄奘进而做出一个重要的决策,这就是从王羲之的真迹中集字刻碑。这个决策当然主要是从投皇帝所好、弘扬佛法的角度考虑。但也从客观上对书法的弘扬做了好事。为了确保这个决策的完成,需要选择一个得力的实施者。而弘福寺怀仁和尚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坚毅的品格以及极深的书法造诣。这样,从决策到实施,形成了一个可靠的保证。从玄奘当时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被李世民称之为“法门领袖”,他一定是这件事的决策者和推动者。于是,就有了怀仁二十五年的艰苦卓绝的集字工程。自然,皇帝和皇太子作序和记,刻字立碑,可能会有皇帝的敕命和朝廷的重视,但我相信,王字《圣教序》的诞生,玄奘这个始作俑者,一定是最积极、最坚定的推动者和实施者。
《圣教序》的诞生,当然绕不开李世民、李治父子这个大的背景。无论微观的还是宏观的。《三藏圣教序》这篇序文,据说是李世民亲撰。七百八十余字,骈俪对仗,文采飞扬。他在文中推崇佛教为“大教”,对玄奘取经的艰难和功绩,不惜笔墨,大加褒扬。最后,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希望圣教佛经流传广布,与日月同辉。福祉布撒人间,与天地共存。幸运的是,经过玄奘和怀仁诸人的努力,《圣教序》书法经典亦横空出世,光耀千秋。这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莫大的幸事。从大的背景来看,贞观盛世、大唐气象,营造了大气、包容、繁盛的浓厚氛围。在这样的文化沃土上,文艺繁荣,群星闪烁。《圣教序》的诞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文化的盛事,后人的神祉。
贞观22年(公元648年),唐太宗李世民亲撰《圣教序》。25年后,咸亨3年(公元672年),李世民死后24年,玄奘逝世后8年,《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完成,刻石立于弘福寺。现于西安碑林。
遗憾的是,李世民、玄奘均无缘看到此碑。
责任编辑 梁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