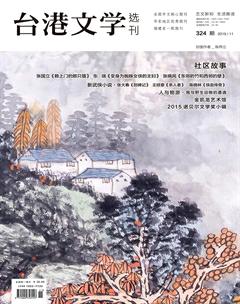白喉与哈士奇
2015-11-20黄信恩

黄信恩,1982年生,毕业于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系,现为住院医师。著有散文集《游牧医师》、《体肤小事》,短篇小说集《高架桥》等。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等。
学生时代,我上过一堂小儿感染学的课,关于白喉、百日咳与破伤风。由于轮到我做记录,那天起了大早,赶在课堂开始前,坐定了好位置。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突然被书上一段白喉兴亡史吸引,着迷它大起大落的身世。
这是一种由白喉杆菌传染的疾病,好犯小孩。因为在病患口腔、咽、扁桃腺等处常见白膜形成,1826年法国医师Pierre Bretonneauru首先将其命名为“白喉”。
历史中的白喉,总以叛乱性的气势出现。爆发,流窜,割据。早在十八世纪中叶,白喉就曾掠袭北美,造成孩童死亡;十九世纪更在英国皇室流行,不少成员因此丧命;直到1890年代,德国医生贝林培养出抗毒素,用以中和白喉杆菌释放之毒素,人类对抗白喉才有了突破,贝林也因此获得第一届诺贝尔医学奖。不过,白喉疫苗要到1923年才被成功研发。此后,白喉身世衰微,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奋力搏击,在俄罗斯境内大规模流行。疫情控制后,白喉节节败退。
对于处在疫苗普及、公共卫生进步年代的我而言,要在临床上遇见白喉个案并不容易。那天上完课,我到图书馆找资料,其中有篇文章竟引了一段白喉的轶事,谐趣地说:“对抗白喉,先要有哈士奇犬,再来才是抗毒素。”
这并非一篇学术性文章,有点像简易版的卫生教材,作者是位英国医生,名叫布鲁斯。他真顽皮,且应该具有撰写新闻标题的潜质,成功地吸引我的目光,将它复印了下来。原来,1925年,阿拉斯加一个叫侬(Nome)的地方,爆发白喉感染。这饥寒的边陲,并无白喉抗毒素血清可供使用。于是人们想出用雪橇运送的方式,从数百英里远的地方,接力传递血清,而扮演运输功臣的正是哈士奇犬,据说共花了五天半完成运送。
我想象在历史镜头里,那片热烈欢呼的雪原,从不知道“哈士奇”这三个字,包藏救难与怜悯。对我来说,这有些震撼,因为我家正养着一只混血哈士奇、客居三只纯种哈士奇。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这栋大厦流行养狗。这个年代比陈小春《男人与公狗》走红的年代来得晚些。我常在电梯里遇见年轻女子,搂一只玛尔济斯于胸前,哈气私语,举动间有种恋人的情感流转着;有时也见一家四口,孩子牵着黄金猎犬,又抚又揉,电梯里他们的对话与关注,全环绕着这条狗,展开一种以“狗”为核心的“核心”家庭;不然就是一只吉娃娃,穿着费工的缝织品,搭配讲究名牌的主人;还有不多言的阴郁男孩,牵一只德国洛威拿警犬,在中庭抽起红宝马,带点稚气地耍帅。
有一阵子,电梯里外国人进出频繁。他们固定每周五晚上到其中一人家里举办派对,于是那晚,大楼中庭就会流动一股酩酊与喧噪。这群外国人与住户互动不多,语言和生活背景或许都是因素之一。我常在电梯里,听见住户和他们交谈,对话不外乎是叫什么名?从哪来?来台湾干嘛?要住多久?喜欢台湾吗?偶尔碰撞到一个熟悉的国籍,便聊起相关的旅游见闻。只是对话很快就静止了,没有任何延续的迹象。
或许是话题贫瘠,主导这群外国人一片空疏的人际网络。几个月后,我发现他们养起狗来,而且不只一只,通常三到五只不等。中型犬居多。最受瞩目的,就是和电影《冰狗任务》一模一样的三只哈士奇。
这三只狗洋味浊重,除了听英语指令、吃欧美饲料,有些身体特征也和美籍主人丹普西一样,譬如多毛、淡色眼珠;而女主人叫洁西卡,来自南美,轮廓分明,性喜对比色调、夸大耳环,生活满是热舞与调酒。
几个月前,丹普西夫妇俩搬来台湾,打算开设风味餐厅。或许是没有小孩的缘故,他们把心力全投注在三只哈士奇身上。每天晚上,丹普西牵着它们散步,像辐射出磁力线,总吸引不少遛狗民众趋前,探问身世底细。不久,公园里出现一种不成文的聚会约定:每到晚间九点,一群狗就在广场前互舔互嗅,吐露燥热的舌头;狗主人则交头接耳,分享狗毛剪法、狗衣制作、狗脾气等。
就在那阵子,我突然感到某个对话出口封塞了。每当行经公园,总有种被拒于外的感觉,仿佛不曾进入公园,不懂通关密语。于是我开始养起狗来。
这是一只棕红色的杂种幼犬,身上混些灰黑色的毛,有二分之一哈士奇血统,是某日逛跳蚤市场,从流浪狗关怀协会的摊位认养来的。义工们昵称它为小花,但我不容许这种老外所谓“average Joe or Jane”的狗名。小白、小黑、小黄、来福、小胖……通通不可以,于是我叫它Coconut,没有理由,纯粹喜欢这单词带来的发音喜感。
我开始牵着Coconut到公园,故意凑近三只哈士奇,以招来注意。但Coconut过于平凡,总被丹普西夫妇忽略。某天,我在Coconut颈上围了三角巾,亮黄色的,缀满铃铛。那种搭配,在它毛茸茸的颈上,像是违建,显得闷热而多举。隔天,洁西卡按我家门铃,表明想改造Coconut。对于她的前来,我愣了一下,表面故作犹豫,内心其实荣幸,不久,便将Coconut全然开放给她未知的技法。于是狗毛一圈挨一圈,有层次地剪落,乍看之下,狗身竟有了分节、褶皱的错觉。她说,这是台北101造型。
此后,洁西卡似乎对Coconut特别关心,常约它去宠物餐厅。Coconut因为食量大,每餐动辄花费五六百元。几次下来,我发现Coconut嗜肉,迷恋鸡爪与羊小排。不久,洁西卡开始教我如何帮狗狗挤肛门,听说肛门的腺体,必须按时挤压,狗狗才会健康,我觉得很恶心。而我也开始加入了以三只哈士奇为核心的狗聚,卷入一个由狗所维系的网络。这种关系不深不痛,却让我感到自在,可以在一个合理、无须顾及冒昧的状态下,和一些从未说过话的住户,有了交谈。
但不久,洁西卡因为有急事,要回阿根廷老家一阵子。由于没有人督促我养狗的进度,Coconut自此从天堂坠入地狱。我用粗糙的方式对待它,不仅吝于出资购买希尔思饲料,洁西卡交代每月上一次宠物美容院:烫理狗毛、修剪指甲、SPA薰衣草按摩浴、健身房……我通通搁着,疏于处理。
不过是只庸俗、从流浪命途挽回的狗,我总如此认为,不甘沦为狗奴。
几周下来,我观察到:自洁西卡走后,Coconut的骄纵与任性,一一露馅。它开始绝食,嗅一嗅我喂它的饭菜,连舔舌的动作也吝于做出,就转身缩回窝里,毫无兴致地,像在赌气。由于Coconut有哈士奇厚毛的遗传,每次洗澡后,吹风机总要开个两小时才会全干,于是重回美容院,店员说它不安分,吵闹咬人,要再酌收一百元。有时,Coconut数天未洗澡,被我强制关在笼里,它会用鼻子顶开门,狡猾逃脱,跳上沙发睡觉,掉一些泄了密的毛。然后隔天清早返回笼里,一脸什么事都没发生。
当我责备Coconut,它总装出无辜的表情,用眼神撒娇;接着以猪鬃般的背部,摩擦我的小腿。然后,我心软了,摸摸它的头,于是它躺下,软趴趴地,不雅地摊开四肢,曝露私处,充满猥亵、引诱的意味。
此外,Coconut还有不少挑逗的举动,譬如它常趁我熟睡时,跳上床来舔我,一种无目的的舔舐。因此,我不能尽情裸睡,得穿条四角裤。有时它看我毫无反应,索性坐在床上看着我,伸出前肢拨弄我的手,要我抚摸它,像任性的情人。
Coconut似乎会察言观色,揣测我的想法。虽然它总是摇尾、嗑药似地迎接我回家,但当我哪天心情低落、与人有冲突,它能嗅出不愉快的情绪,突然停止吠叫,坐下盯着我。
有天,我在Starbucks翻到一本外文杂志,里头大幅报导洛杉矶几间五星级宠物旅馆。从暖色系lobby、纹样毛毯、桧木阶梯、蜡烛水晶灯、花瓣浴池到古埃及壁画,极尽奢华。这似乎暗示一个国家,当金钱裕余到某个程度,人们转而把生活搬进宠物世界里,替它们办保险、针灸治疗、找玩具、心理医生、殡仪馆等。不少以狗为叙述角度的影片蓬勃上映,譬如《101忠狗》的大麦町、《再见吧!可鲁》的拉不拉多、《猫狗大战》的米格鲁等。
那阵子,我在CNN看见一则报导,关于“高龄宠物照护”。故事发生在日本,一只十七岁的拉布拉多犬,老态龙钟,上车或翻滚均需他人扶助。主人说这条狗就像他的孩子,于是每周安排它水疗、漂浮、按摩,甚至为此搬家至水疗馆附近,以方便治疗。一个月下来,花费超过五百美元。记者用“dote on”(溺爱)描述日本人对待宠物的态度,并加以“mundane”(庸俗的)这个词,说明在日本,替爱犬订制服饰的行为,已过于普遍而落伍了。
这几年,日本的宠物养老行业勃发。报导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日本开始盛行宠物饲养。如今,这一批宠物都老了,有点像战后婴儿潮,于是人们开始替爱犬寻找照护规划。
阅读这民族对狗的呵护,我突然感到愧对洁西卡。有天,丹普西来我家,说要赶去阿根廷,由于找不到体贴的宠物旅馆,想托我照顾。他频向我解释,哈士奇生性温驯、好照顾。看着他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神,我答应了,却感到心虚。他送我一箱洋酒,就在隔日清晨出境了。
傍晚回家后,我拿出录音笔,重复听着课程录音。但没多久就累了,突然想到“对抗白喉,先要有哈士奇”这段话,索性拿出这篇文章,无意间,我发现布鲁斯以“husky voice”描述白喉患者的发声症状。我不禁微笑,这似乎是个双关,“husky”一方面指粗哑的嗓音,一方面指哈士奇犬;这也似乎是有意的安排,因为医学原文书都惯以“hoarseness”描述沙哑,显然他认为白喉的沙哑有不同的腔法,或特殊的故事底蕴。
我继续赶制记录,偶尔停笔,看看家中做客的哈士奇,它们没睡,有些不安,似乎感应到主人在阿根廷发生了什么,激发某些救难本能。我突然想起电影《极地长征》里,八只在南极洲等候主人的哈上奇;而Coconut也醒着,在房里亢奋地兜圈子,或许已感知我要熬夜,决定陪我。
夜里,我听见窗外零星的狗吠声,在这寂寞大厦里显得清脆,那似乎是一种友善的语言,向人们指示交谊的连结入口。以往被设定来执行防卫任务的狗,如今反而用来消弭防卫——人与人之间的。仿佛这个年代,狗吠已消失象征的警戒意味,人们以养狗诠释生活圈的孤独。
或许就像白喉,失去历史中的骁勇意涵,在这个三合一、四合一、五合一,甚至六合一的疫苗年代。
(选自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游牧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