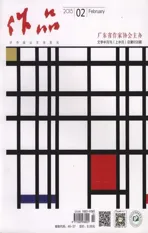父亲的河流
2015-11-17文/马亿
文/马 亿
父亲的河流
文/马 亿
马 亿 湖北浠水人,生于1992年,大四学生。第十五届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2013年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优秀奖,小说发表于《新作家》、《四川文学》、《短篇小说》等杂志。
如果说每个少年的成长都有一个特殊的节点,那么我的这个节点显然是在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新麦收割之后,空气中飘散着满满的麦浆甜味,闻起来就令人食欲大开。大田里的野草也被牛吃得只剩下茬子了,田地里一下子显得十分安静,仿佛酝酿着什么大事。那几天,村子里四处都响动着磨刀的声音,家家户户都把闲置了大半年的犁铧拆卸下来,由当家的蹲在大门口的阶沿上使劲地磨着,小孩子则负责给磨石浇水,整个村子呈现出一幅欢快的景象。
但是父亲没有那样做。
我和弟弟很着急,隔壁几家的犁铧陆陆续续都磨完了,父亲仍然没有动手的意思,他依然是日日吃完早饭后坐在打谷场的石碾子上抽旱烟,不时地把烟管往身下敲一敲。下午则是去后山竹林里坐着,直到黄昏,残阳越过远处的第四个山拗口,父亲才会起身回家。
我和弟弟都很怕父亲,也不敢催他,于是跑去问母亲。母亲说他可能是太累了,要休息几天,还叫我们最好别烦他,当心皮痒。父亲本来就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突然变得更加沉默了,连母亲跟他说话都不理了,端起饭碗就发呆。晚上他倒是说话,但不是跟我们说,而是对着天空说,还指手画脚手臂大开大合,像是做广播体操。
那年的犁铧终究是没磨成。
一天早上,父亲早早起床提着斧子就走了,跟谁也没打招呼。父亲走到村头时,正好碰到起来解大手的王三叔,他对王三叔点了个头,由于王三叔走得急,没顾得上回个答应,但是之后据王三叔回忆,那天早上父亲的脸色发青,显得心事重重。他当时还纳闷,大清早提着斧子这是去干啥。
谁都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
那一天,父亲很晚才回来,似乎是很劳累,连扛着斧子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柄桦皮的斧子被父亲拖在地上。母亲连忙揭开用碗盖好的晚饭,父亲却懒懒地说一句,明早再吃吧,随即直接走进卧室倒在床上了。母亲打发我和弟弟进去看看,才眨眼的工夫,父亲已经响起了震耳的鼾声。我和弟弟望着床上的父亲,都感觉很陌生,最近一年,父亲已经很少跟我们讲话了,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是一副淡漠的表情,似乎是耳背。跟母亲也是这样,有时候母亲叫他好几遍,他也只是回过头对母亲笑笑,不答应,为这,我和弟弟多次看到母亲偷偷抹眼泪。
第二天,父亲很早就起床用开水泡了昨晚留给他的晚饭,依然是提着斧子走出了家门。我和弟弟听到母亲在说什么话,但父亲全都没有回答。不一会儿,母亲就来到我和弟弟的床前,她叫我们跟着父亲去看看,看他究竟在干什么。
弟弟很兴奋,一骨碌就跳了起来,趴在地上系起了鞋带,还不停地催促我快点快点。要是当时我也像弟弟一样,跳起来就穿鞋跑出去,可能我们就能追上父亲。但是起床之后必须上厕所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所以从床上下来我直接冲向了门前的厕所。不知怎么搞的,那天早上我蹲在厕所里,精神完全不能集中,就像在上一节数学课。弟弟在厕所外面不耐烦地大喊大叫,更加让我急躁,当时我有一种冲出去把弟弟提进来扔进粪坑的冲动。那是我上过的最煎熬的一次厕所。
等到我和弟弟赶到村口时,父亲早就没了踪迹。我们在村口问了几个排队上厕所的老头儿,他们全都没看到父亲,父亲究竟去哪儿了。
我和弟弟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弟弟一边走一边埋怨我,说我上厕所怎么这么慢。我都快烦死了,完全搞不懂今天早上是怎么了。听到弟弟的埋怨,火气更大,把弟弟逮过来使劲地踢了两脚。弟弟被打翻在地上,抱着被踢痛了的脚哭了起来,我也懒得理他,一回家就钻进了被子。母亲焦急地问这问那,我一个字也不想说,最后她嘤嘤地哭了起来。
真是令人讨厌的一个早上。
母亲照例留了晚饭在饭桌上,我和弟弟也陪着母亲坐在堂屋里,盼望着疲惫的父亲拖着斧子再次踏进家门。夜越来越深了,母亲也越来越焦急,坐都坐不住了,必须隔几分钟就要站起来在堂屋里转一圈,我和弟弟张着嘴打着大大的哈欠,似乎是在坚持着什么约定,都没有提出先去睡觉,但眼皮越来越重了。
第二天我从床上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照在卧室里亮堂堂的,弟弟砸吧嘴睡得很香。我下床去母亲的卧室看了看,床上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的,我凑过去闻了一下,还有新鲜的阳光味儿。看来母亲昨晚是没有睡觉,也说明父亲昨晚没有回来。母亲应该是找父亲去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弥漫在我心里,像滴入玻璃杯里的一滴红墨水,慢慢地浸润,渗透,变形,最终呈现出一张毫无表情的中年男人灰色的脸。那张脸给人一种父亲的感觉,却不是父亲。那是谁呢?
我神情怔怔地走了出去,站在门前的打谷场上,刺眼的白光从竹林间射进我的瞳孔,每一根都深深地扎了进去。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但我想去找母亲,如果有可能,把父亲也找回来。
就在我不知所措地立在门前的时候,大婆婆从下湾走上来了,她端着一个捆着粗铁丝的木盆子轻轻巧巧地登了上来,木盆里几件素色的衣服像扭好的大麻花一样安安静静地躺着,看来她是刚从大塘冲里洗完衣服回来的。
大婆婆走到了我身边,慢慢吞吞地说:“快去河滩看看你妈吧,人都哭摊了,也不听劝,几个人抬也抬不走。你爸也是的,搞个么事名堂……”我没听完大婆婆的话,抬脚就冲了出去,几粒小石子硌在我的脚底板上,我也顾不得疼痛,冲过了竹林,冲过了小山岗,沿着田畈里细小的田埂一路冲到了平坦坦的河田边,河滩就在堤坝的那边。
我下到河滩时,并未看到想象中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景象,她坐在一块栓牛的花岗岩上,直呆呆地看着向东流去的河水,表情出奇地严肃,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母亲。我感到了一丝害怕,脑袋里想象着父亲可能遭遇的情况。我想到了去年夏天淹死在鱼池子里那个叫小安的男孩,他是在捞鱼草的时候遭遇了意外,潜水衣被什么东西划破了,他就像一条裂了船底的小舟,慢慢地沉没了,皮衣里灌进来的水就像一块千金巨石一样压在他的身体上,他没能解开皮衣的暗扣。被三文叔从水里抱出来的一刹那,小安的脸色很干净,很白,手臂完全扭转了过去,软若无骨。
我一屁股坐到地下,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或者去问问她父亲怎么了,我甚至连走路都忘记了。白惨惨的太阳毫无遮拦地撒在河面上,粼粼波光一闪一闪地晃动着,河岸边抽着白穗的芭茅芯子在微风的拂动下左右招摇,似乎在召唤着什么。
万里无云。
母亲后来回想起父亲出走的那个早晨,她完全不记得我的存在,她说,那天早晨的河水气味真好闻。
父亲成了一个生意人,真是让人没想到。
那天早上就是父亲生意的开始,这当然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在这之前的那两天,父亲在一公里之外的梅梓山砍了数十棵合抱的大丛树,然后一个人把树拖到河边用麻绳捆好,扎成一个小筏子的样子。那天早上母亲找到河滩的时候,正好赶上父亲启程,他划着一只竹篙子,不顾母亲撕心裂肺的呼唤,朝刚刚露出头的朝阳驶去,顺着奔腾的陈庙河划进浠河,融入巴河,汇进浩瀚的长江,把母亲和家乡留在了身后,他成了一个生意人。
母亲回家之后栓上大门,坐在床沿上三天没踏出房门,连觉也没睡。我和弟弟拿着小板凳坐在母亲面前,面面相觑。母亲的眼神涣散,好像我和弟弟根本就不存在,她的眼神飞向了虚无的远方,远方就是父亲要去的地方。
三天后,母亲打开大门,把堂屋里堆积的鸡屎清扫出去,然后抹桌子扫地煮粥,替我和弟弟整理好书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饭桌上,母亲说,以后就当你爸死了。弟弟诧异地看着我,我端着饭碗,心想,既然母亲说的是“当”父亲死了,那说明父亲肯定没有死。在上学的路上,我把我的推理结果告诉了弟弟,弟弟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问,那爸爸去哪儿了。我说,去了他一直想着的那个地方。我觉得父亲的出走和他之前在打谷场上坐着抽旱烟有关,但是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
一个月之后,去女儿家看外孙女的王三叔急匆匆地跑到我家门前的打谷场,告诉正在扫打谷场的母亲,父亲回来了,正在梅梓山上砍丛树呢。母亲连忙牵上我和弟弟,往梅梓山赶。
我们娘仨登上半山腰时,父亲正坐在已经放倒的树身子上用家里的那柄斧子砍着树的旁枝,空气中飘满了丛树汁液的独特芳香。父亲的脸变黑了,也变红了。父亲看到了我们仨,只是有那么一瞬间,斧子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埋头干他的活去了。弟弟看到了父亲,表现得很激动,想挣开母亲的手。母亲把弟弟的小手握得更紧了。
“吴德贵,你今天给我说清楚,我哪里把你伺候得不好。”母亲的语气很柔和,跟说出的话有点不相配,但是她喊了父亲的大名,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之前,母亲一直喊父亲“六点”,父亲是在六点钟出生的,全湾人都是这么喊的。
父亲停下了斧子,从树身子上抬起脚,站起来在上衣的内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扎紧了的红色方便袋,走过来塞在了弟弟没被母亲牵住的那只手里。然后回转身接着砍那棵树的旁枝。我和母亲呆呆地看着父亲的一举一动,他就像一位哑剧演员,在我们身边表演着谁都看不懂的后现代戏剧。
回家的路上,母亲仿佛松了一口气,她把红色方便袋里的一叠“大团结”数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永远也数不清。你爸是在做生意,母亲说。
从此以后,我们每个月都能在梅梓山上见到父亲一次,当然,他都是在砍树,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钱也依旧是一叠“大团结”。关于父亲的一些细节,也由在巴河里铲黄沙的三旺父子给补充完整了,他们说父亲顺水穿过巴河之后,在入江口卖掉丛树,然后坐小舢板登上江心小岛上的那座寺庙,呆半个月再坐挖沙船回来。他还替我们算了一下时间账,父亲的划子从陈庙河过巴河入长江只需要个把星期,但父亲每次一个月才返回,这就充分说明父亲在那座寺庙里是住了半个多月。我们都将信将疑,父亲去寺庙干嘛,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有了父亲每月拿回来的那叠“大团结”,我们家似乎比以前过得更好了。母亲每个月都会炖一次猪脚黄豆汤给我和弟弟喝,猪脚黄豆汤让我和弟弟明显比同龄人高出一截,只是父亲仍旧没和我们说话,我们也很少提起他,仿佛他是我们家的一个禁忌。我和弟弟渐渐长大,见父亲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每见一次,父亲好像都比上一次更老了,但是他的目光好像越来越柔和了,看什么都饱含着深情。
在我高考那一年的夏天,整个村子都笼罩着一团喜庆,我考上了远在首都的重点大学,是县里的理科状元。看着家里亲朋好友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因为父亲已经好几个月没出现了,母亲自然也高兴不起来。办考学酒那天,三旺送来一封红包,说是父亲特地跑到巴河交给他的,让他带给母亲。母亲捏着红包,问,他还说什么没。三旺抓着脑袋,过了好半天才摇摇头,好像就说了这。母亲的眼泪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大三那年,我带着母亲和弟弟坐着挖黄沙的船顺河而下,走上了父亲已经走了千百遍的河流。我们要把父亲带回来,弟弟说。船一出浠河,水面顿时变得宽敞,两岸的芭茅草也不见了踪影,全部换成了身子妖媚的垂杨柳。我们找到三旺的儿子二黑,问了父亲以前常去的那个小岛的方位,二黑说他好几年没去那边了,那里采砂船不准进去,他也说不准父亲在不在那里。我们赶到入江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奄奄一息,变成了一个温吞吞的鸡蛋黄,举目四望,哪里看得到什么江心小岛。下岸一打听,才知道三年前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把这段江给封了,顺便把偷采黄砂的工人歇息的江洲小岛也给挖了,那座小寺庙自然也不存在了。再问原先住在寺庙里的人呢,谁都不知道,“谁会注意那几个野和尚呢”,他们说。
又过了十几年,我和弟弟在人海中沉浮,终于混出了点儿样子,我当上了一家科技公司的副总,弟弟是一家日用品公司的经理。而母亲在老家孤独地去世了,她说她离不开家乡的那条河。我和弟弟赶回家奔丧,在母亲那架从外婆家带过来的老梳妆台上发现了母亲留下的一张字纸,她说死后火化,把骨灰撒入陈庙河,她要顺着河水去寻父亲。她说那是父亲的河流。
我和弟弟两个大男人看着母亲的字纸泪流满面,那一刻,这些年出门在外的艰辛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们仿佛读懂了父亲。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