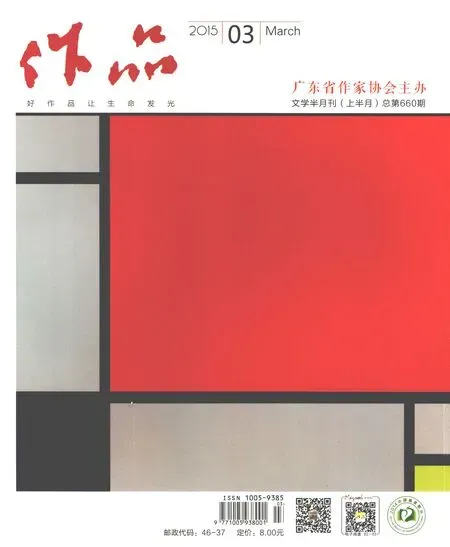姊 姊
2015-11-17台湾朱国珍
文/(台湾)朱国珍
姊 姊
文/(台湾)朱国珍
朱国珍
台湾清华大学毕业,东华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艺术硕士。长篇小说《中央社区》获亚洲周刊2013全球十大华文小说。曾获《拍台北》电影剧本奖首奖、台北文学奖。曾任中华电视公司新闻部记者、主播、节目主持人。现为广播节目主持人。作品有散文《离奇料理》、长篇小说《中央社区》、《三天》、短篇小说集《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猫语录》。
我这一生,只见过我姊姊三次面,可是我为她流的眼泪,比我亲妹妹还多。
打从我懂事开始,爸爸就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姊姊,当年在大陆逃难的时候,来不及带她出来,他离开家的时候,姊姊只有七岁。爸爸说,等到反攻大陆的那一天,他会带我回老家去,就算姊姊与我是同父异母所生,见着她的时候,也得亲口喊她一声“姊姊”。
姊姊!姊姊!这个名字在我的心里,已经呐喊了一千遍。即使她是另一个妈妈生的又如何?我的亲生妈妈,在我们十几岁时绝然改嫁,曾经脐带相连如今见面都要预约时间的亲生母亲,与只有一半血缘却终日想象依望的姊姊,亲情的距离,也不会更遥远。姊姊!姊姊!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姊姊能照顾我,跟我说话,带着我长大;我可以卸下长女的包袱,不必凡事在妹妹面前做榜样,因为我有个姊姊,她更懂事,更孝顺,更听爸爸的话。我一直幻想那一天,当我见到我的姊姊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她说,好多好多,只有姊妹才会掏心掏肺的话。
只是,当我真正亲眼见到姊姊的时候,她已经五十九岁了。
在那之前,是通信。一开始,所有写到大陆的信件,都要透过美国的朋友帮我们转寄,一来一往,通常要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常常看到爸爸收到信时,脸上透露着期待与哀伤的表情。爸爸看完信之后,会叫我再看一遍,我接过那张薄薄的信纸,一字一句用深蓝色粗黑签字笔写着简体字的端正字迹,却都是由姐夫写的,信中不外乎陈述家乡岁收,天气概况,家人健康,与问候我们平安,学业进步,孝顺父母,努力读书之类的。我问爸爸,姊姊为什么不写信?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可能不会写。”
那时候,爸爸还能亲手提笔回信给姊姊、姐夫,但总还是要我另外再自己署名写一封,表示诚意。十几岁的我心浮气躁,经常随便写一封日记体般的文字应付,心里嘀咕着,这种事都不会要求妹妹做,都是我,这个台湾的“姊姊”必须概括承受。几年之后,爸爸老了,老得没力气写信,开始由我代笔,那时,两岸也开始直接通邮,对岸的地址是“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告城村西南街”。
一个没有门牌号码的地方,与我们保持着固定联络,每一次的信件内容都差不多,孩子们长大了,收成好了,天气变了,家人都平安,希望你们能保重身体,期待团圆的那一天。
团圆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却是爸爸挺着六十九岁的身躯,独自去大陆探亲。回来之后,也带来了姊姊的近照,将近五十岁的姊姊,和爸爸真像个复制品,只是性别与头发的长度不同;同样是厚实圆满的身躯,方正的脸庞,姊姊留着齐平耳下的直发,微笑着,头发银白,脸庞历尽沧桑。
我的姊姊……
即使后来电话可以接通了,她也是不太说话。爸爸说,因为她害羞。姊姊不擅长说话,却是务农高手,姐夫在中学作教员,家事全靠姊姊操劳,举凡下田、煮饭、挑井水、运煤炭、照顾孩子,全靠姊姊一个人撑着。
“她手脚勤快,做事俐落,是个好孩子。只可惜,她四岁时死了亲娘,七岁没了父亲,十岁的时候,照顾她的奶奶也走了,后来投靠四叔家,寄人篱下,十七岁嫁给姐夫,一辈子都在辛苦。”爸爸每次说到这儿,总是噙着泪接上一句:“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你姊姊。”
姊姊生了四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儿子,两岁时连续发了五天高烧,捡回一条命后,成了癫痫症患者,姊姊不离不弃,亲手抚养他成年,这孩子就这么整天跟着她,有时遇到街坊邻居欺负姊姊,身材高大的他往旁边一站,怒目以视,似乎帮她讨回了一点正义。这儿子长得好看,却也薄命,三十几岁就过世,不到一年,姊姊积劳成疾,中风之后,从此行动不便,更失去了说话能力。
之后,父亲动了一场大手术,心里明白,日子可能不多了,唯一的遗憾,是不能落叶归根,也无法再见着那亏欠了一辈子的亲生女儿。于是,我们克服万难办了探亲签证,让姊姊与姐夫从大陆来到台湾,与爸爸做最后一次团圆。
我终于在香港机场,第一次亲眼见到姊姊。那年她五十九岁,被姐夫用轮椅推出来,重新染黑的头发让她看起来精神奕奕,身上穿着爸爸上次去大陆时送给她的花棉袄。见到我的时候她笑着,眼角却流下了眼泪;我那时自以为能成熟从容地应付这种陌生的场面,没想到,两行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脸庞滑过。我把他们从香港接到了台湾,距离前两次返乡探亲到现在,经过十年,我的父亲,与他的女儿,我的姊姊,终于再度重逢,然而我们心里都有数,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那次团圆之后,过了三年,八十三岁的父亲,在睡眠中辞世。也不过一个星期前,我惯常在休假时回家陪伴他,那次他特别叮咛我:“孩子,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要记得,把我的一颗牙齿带回老家去,跟爷爷奶奶埋在一起。”我瞪着他,心想,又来了,怎么最近每次见面,都要提后事?他交代完之后,沉默了几分钟,也许有半个小时,也许只是因为电视节目的广告太长,让我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他悠悠说出口:“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姊姊,恐怕是没办法弥补了,如果有下辈子,我最希望的就是尽到一个作父亲的责任,好好照顾她。我这么说,希望你不要介意,你们都是我的女儿,但是你比你姊姊幸福,你有爸爸,她什么都没有,这是我最亏欠她的地方。”
父亲过世之后,我依照他的遗愿,带着那颗恒齿,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过去我一直以为时间很多,总有一天会有空陪爸爸返乡探亲,而任意蹉跎机会,直到无法挽回;这一次,没有任何借口,我终于回到了让我父亲一生萦绕心头的家乡,那儿是祖籍朱沟村,那儿是夏日遮荫的大槐树,那儿是产量丰盛的大枣树,还有在山洞里挖凿的窑,冬暖夏凉。我父亲编织的家乡之梦,丰饶富庶,我在梦中,仿佛也见过不下百次,直到,我亲眼目睹了那用黄土与砖块建造的瓦屋,那用煤炭生火煮饭的灶,那一桶桶用人力走上十分钟所挑回的井水,那为了省电费而永远不插插头的冰箱。我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说我很幸福,因为我的姊姊,这一辈子,都在这样的环境里,无父无母,艰辛地活着。
姊姊特别穿上我在台北买给她的桃红色菱格纹针织棉衣,等着我们到来。这次相聚,是在父亲刚过世三个多月后,我握着她长满粗茧的手,坐在她身旁,问一声姊姊好吗?她的宿疾让她无法言语,只能看着我笑,我再问她:“姐夫待你好吗?”她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这么多年来,姊姊行动不便,全靠姐夫照顾,为她更衣、煮饭,还要把屎把尿。曾经这些照顾家计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做,如今,她却是动也不能动了。我看着姐夫干瘦的身影,与简陋的墙壁,房子里就是两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个电视机,还有一张破烂的沙发椅;两个灯泡,是室内唯一的照明,仿佛要等到天亮,才会有光。
姐夫问:“妹妹,爸爸走了,你们的日子怎么过?需不需要钱?我现在退休了,每个月有月俸,给你姊姊买药还有剩,如果缺钱,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这时候才想起,二十多年来,我们通信的内容虽然都是家常小事,可姊姊与姐夫,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穷困,而开口跟我们要过钱,甚至到这个地步,他们还担心我这失怙的妹妹,需不需要帮助。
我的姊姊……
我从小就梦想拥有的姊姊,第二次见到她时已经六十二岁,白发苍苍,不能言语,我跟她说话,她专心听着,偶而用笑容回应我,大多数时间是点头或摇头,但我知道她一直在看我,她在看我跟爸爸长得像不像吗?她也跟我一样,曾经幻想着有个可以说心事、互相陪伴的姊妹吗?我跟她只有一半的血缘,可是因为爸爸,我们的生命始终连结在一起。爸爸第一次返乡探亲,姊姊托他带回一对玉镯子送给我做礼物;姊姊与姐夫亲自来台北那一趟,也特别准备了一个纯金戒指送给我。而我,除了在路边摊敷衍地买了十几条围巾当作礼物之外,还嫌玉镯子跟金戒指老土。
姊姊不能说话,但她会笑会流眼泪,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多年来,都由姐夫代笔写信给我们,姐夫能解读她的心事吗?每次的信件,重复着鼓励我要好好活下去,努力上进,做个成功的人,为他们尽到孝顺父亲母亲的责任,这也是姊姊的心意吗?父亲过世之后,姐夫的信件里,改为希望我们能继续孝敬母亲,照顾母亲。对于一个这辈子只见过一次面的后娘,姊姊的宽容,更显得我是个任性的妹妹。我那不能言语的姊姊,即使病了,还是坚强的活着,她是为着什么?是为了一份牵挂?还是那个情份?有生之年,如果她还能站起来,还能病愈,她愿不愿意跟我说出真心话?愿意告诉我,她沉默了这么多年,是为着什么而坚强的活下去?
返乡之后,我答应他们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要回来,却又食言了。过了两年,等到两岸都直航了,还是没办法回去,以前是没空,后来是没钱,这样的理由也不敢明讲,心里想着,总之等存够了钱,总有一天会再回去看姊姊。但是那个总有一天,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到来。起先是七十岁的姐夫病倒了,他因为脑溢血住进医院,救回来之后留在院里复健,两个月之后才回到家,那时,姊姊的眼神开始变得落魄,没有语言的脸庞更形黯淡,仿佛支持着她的那股能量渐渐消失了。时序进入冬季之后,姐夫又住进了一次医院,这次,姊姊也倒下了。
电话里,他们只是说姊姊不太吃东西,越来越消瘦,其他就是老样子,不要太担心。我想,姊姊生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过去因为太胖而不方便活动,现在体重减轻,应该是好转的迹象吧!直到除夕早晨,姐夫按照惯例,打电话来拜年,语焉不详的转述,说姊姊不行了。我刚开始听不太清楚,浓重的乡音让我们的对话经常变得像猜谜,失去耐性时更容易简化所有的问题,抗拒电话那一头隐约传来的焦虑。挂了电话之后,我沉静思索刚才姊夫在电话里到底想说的重点是什么?越想越觉得不妥,转身立刻又打了电话去大陆详细询问,姐夫依旧安慰我说是老样子,只是姊姊瘦得很厉害,完全不吃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挂上电话后,我到了爸爸的灵骨塔前祭祖,香炉火旺,余烟缭绕,我一个人在父亲的遗照面前,面对着供桌上的水饺、烧鸡和卤蛋,心里头禁不住一阵酸楚,今晚又是独处的除夕夜,自父亲过世后即不断重复的孤寂。思量半晌,决定回去大陆探望姊姊,我天真的以为,姊姊就算是病重,也会像从前父亲在八十岁高龄时,进行心脏手术、下肢动脉硬化手术一样,只要有我们陪伴,都能勇敢地挺过去,坚强地活下来。
订了三月八号出发的机票,却在启程前两天,接到家乡来的电话,说姊姊走了,跟父亲一样,在睡梦中去世。没想到要返乡看姊姊最后一眼,演变成回去送她最后一程。我本来以为可以在她的病榻前,再一次握着她的手,仔细地看她,究竟我们俩是谁像父亲多一点?我也决定要诚实的告诉她,自从爸爸死了以后,这些年来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可是我也挺过来了,虽然人们都说时间最无情,可时间却也是最能治愈忧伤的良药,我用了八年的光阴,走出生命的谷底,这是我从来不敢写在信上的秘密。
楚辞里面有句话说:“悲莫悲兮生别离。”过去我总以为,“生别离”就像是送行的人与远行的人,在车站里挥手道再见,两个人虽然各自有旅程终点,但总是会有再相见的一天。现在我才明白,生别离中远行的人,其实是去到了我的肉身所不能去的地方,留下送行者,在人世间独自啃噬被抛弃的悲哀,活着的心灵,终日反复思索着逝去的亲情,为什么,我这一生想要做的事总是来不及?
姊姊火化入土之后的当晚,我梦见她。起先是我那件雪白的羽绒大衣,覆盖在她的水晶压克力棺木上。我始终没有见到姊姊最后一面,他们说,姊姊最后瘦成皮包骨,完全变了样,还是不要看,看了难过。我听从长辈的指示,却执着于肉身的样貌,我的姊姊,那个圆圆胖胖的姊姊,怎么可能改变?因此,在梦里,我怀着惶恐与敬畏的心理,掀开雪白羽绒衣,却依然是那座完整的压克力水晶棺,姊姊躺在里面,从头到脚被绿色绣花被单覆盖着,我依然没见着她的容貌。我说:“姊姊,我来了,却来不及见你最后一面……”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姊姊的声音,轻轻地用浓重的乡音说着:“别看吧!看了莫啥意思。”我继续说:“我好想跟你说话,我们姊妹俩,这辈子,都没时间好好聊过天,说些心里话……”姊姊的声音,平静地传递着:“现在,我们也可以好好聊聊……”隔着透明的棺木,与看不见的身躯,我和姊姊,在梦中,终于认真地聊上了一回。她的形体,她的声音,她的样貌,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只有一种安详的感觉。她的心里有我,才会回来看我,就像她从前活着的时候一样,静静地聆听我说话,这一次,她也许已经超越肢体的障碍,可以自在地回应我,告诉我这些年来,她是如何坚强的活下去,是凭着什么样的意志力,在劳苦的人世间,默默的存在。
天亮了,姊姊真的离开了。我从梦中清醒,一切都这么真实,却再也摸不着,见不到。我望着窗外,几株冬日里的白杨树,孤悍地挺立在寒风中,华北平原的冷空气,一波接着一波拂向窗台,阳光从晨雾中穿透,融进我的血液,是我一生中遥远的姊姊,最近的距离。
(责编: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