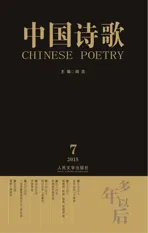诗学观点
2015-11-17李羚瑞
□李羚瑞/辑
诗学观点
□李羚瑞/辑
●蒋维扬认为诗歌是一门学问。诗歌有它的规律,有它的标准,有它的操行,亵渎不得,轻慢不得,儿戏不得。真正写诗的人得爱诗,敬重诗,从骨子里爱,首先自己不做“玩”诗之类的事情。当诗歌编辑也是这样,一夫当关,不让伪诗出笼,不授人以柄。那些奚落诗、鄙薄诗、埋汰诗的人,对诗的修养其实多很肤浅——或者说,他嘲笑的本不是诗。一般说来,诗歌是青年人的事业,一代诗人隐去了,又一代诗人成长起来了,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青年诗人要沉心下气,把诗作为一门学问来做,古今中外广泛涉猎,汲取营养,同时博大些、深刻些,心忧天下,关注时代,关注人生。
(《一封由“大展”引出的信》,《诗歌月刊》,2015年1-2月合刊)
●王昉认为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中带有彝族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文化观,区别于西方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诗歌的精神内质,它上升到了信仰伦理的层面,在浪漫主义的颠覆与破坏和现代主义的颓废之外,传递出信仰的救赎力量。当西方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面对现代性的威凛,徒然悲愤伤感以致迷失的时候,吉狄马加用其在故乡之中传承的信仰与信念为无奈的现代文明的溃败指出了“通往天堂的路口”。在充斥着西方玄思,弥散着虚无与悲观情愫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的余绪中,吉狄马加矗立起了东方传统文化与信仰的尊严,在打破惯性的历史文化经验之后,他的诗获取了不同于以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相对独立的具有浓重东方色彩的文化价值意义。
(《在经验与超验之间传递信仰——论吉狄马加长诗〈我,雪豹……〉》,《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刘波认为新世纪以来,但凡提到余怒的,大都觉得此人写诗很古怪。他写的诗大都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所作的变形,变形为一种你意想不到的生动。他几乎不按既定逻辑出牌。在一个先锋诗人看来,创新是写作首要的行动,从语言到语感,从结构到诗意,他总是要带给我们某种出其不意。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变动的,所以追求变化就成了他的法则;而相应地,在他笔下,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恒常的,他需要打破的就是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超稳定结构。这样的思维方式对接了词语,就是想象在推动每一个意象前行,而我们在读到下一句之前,根本想不到诗人会出什么招数,这是疑惑,也是诗意本身。
(《当代汉语诗歌的神秘魔方——余怒诗歌论》,《红岩》,2015年第1期)
●白杰认为由反抗外部世界走向拷问自我灵魂,再至怀疑主义、虚无意识的疯长,朵渔的精神困境在“中年写作”中具有普遍性。这一现象如置放在哲学层面的话,我们可从阿尔都塞的言说中获得启示。他指出,人们自认为可凭借自己的主体意识去清除意识形态遮蔽而自由独立地把握现实,但事实上,主体意识本身就生成于意识形态构架中,并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主体,必定成熟且强大,但从这一刻起,他的主体意识也将面临消弭的危险。朵渔印证了阿尔都塞的说法,在中年,在生命经验如此丰厚,以鼓足勇气去直面体内的黑暗扩散时,他的精神震荡发生了。某种意义上,这种震荡,是一个诗人走向伟大的必由之路。
(《朵渔:在灵魂震荡中重建写作的支点》,《扬子江》,2015年第1期)
●于坚认为汉语本身就是存在性而非工具性的语言,汉语决定着汉文明的亮度,诗是文明的最高水平,也是精神世界的领袖。诗有宗教责任。将语言工具化乃是现代汉语的一个趋势,聪明诗人受到西方诗歌影响,长于辞令,巧言令色,是当代诗的一个趋势。其危险是,汉语诗本来更倾向于天然的宗教色彩,长于辞令使这一功能弱化,读者也会丧失对诗的古老信任。西方诗歌长于修辞的精致被注意到并影响了一些诗人,但思这个特点并未引起注意。就现代诗来说,思非常重要。汉语诗在思上面比较贫乏。语言之思非常重要。而在西方,指向存在之思、富于宗教感的诗也是最高的。
(《说道法自然、日常神性与汉语诗性》,《钟山》,2015年第1期)
●于贵锋认为泉子有思辨甚至雄辩的一面。这里面有激情,也有将问题搞清楚的执着。他得让自己知道,他说出的是他内心确实存在的,而不依靠别人的阐释或误读。因此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将思辨直接入诗,直至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二是思辨与感性融合;三是写纯然之境,不落言筌。如果说第一种情况还存在机巧的话,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客观的抒写中以意蕴的柔软来对应思辨的岩石,而第三种情况,往往看起来稚拙实际上是臻于化境。可以说沉思、思辨、冥思,这种内视的方式让泉子的诗歌不仅在大的方面,体现出诗与思结合的特点,更是由此获得了思想上和诗歌上的新的向度。
(《静止的风暴眼:泉子诗歌札记》,《作家》,2015年第2期)
●王珂认为诗形建设是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韵律不严格甚至完全没有表面的韵律结构所造成的诗的音乐性的减少,必然导致它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承载功能的减弱,诗的分行排列及对诗的排列的高度重视恰好可以弥补诗的音乐性的减少所造成的损失。现代汉诗本质上是一种反对“经典化”、“定性诗体”和“贵族性”的世俗化、自由化和平民化问题。因此今天的诗体重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遵循渐变的文体进化原则,强调诗歌及诗体的多元与和谐,这种和谐甚至应该包括古代汉诗(格律诗)与新诗(自由诗)的“和平共处”式的和谐。但是要重视古今汉诗的诗歌生态及诗歌功能的差异性。
(《现代汉语诗歌诗体的现代性》,《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期)
●刘川认为由于我们大量的诗人缺少了对当代社会的思考与关注,导致诗歌写作成为一个古玩行当、一个小作坊、一门维持传统的手艺、一个自娱自乐的沙龙,而越来越不为大众所接受。散文诗领域的问题与整个新诗界的问题一样,广大作者缺少集体向度,只有个人理想或个人意愿,没有将当代性当成创作的必要元素,从而将作为集体心灵表露的散文诗作品匠而器之,有其形,无其神,言不及义。所以认真探讨散文诗的当代性与未来性可谓无比必要。散文诗的写作是我们的在场证明与身份合理性。
(《高呼散文诗的当代性》,《散文诗》,2015年2月上半月刊)
●翟俊明认为很多诗人在写作城市的时候往往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的写作方式,这是必须要给予反思的。几乎每个人都在写作“乡愁”,如何在同质化的熔炉中脱身而出?诗人必须具有发现性!焦点社会现象背后的诸多关联性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的现实和文本的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构建“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
(《你可以奉献一段诗篇——当下的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湖南文艺》,2015 年3月号)
●李墨波认为所谓专业化的写作让诗人们深陷在影响的焦虑中,黑夜、大海、灯塔、星光……都成为诗人们需要规避的敏感词。他们人为地设置难度,增加阻拒,单纯地炫技,完全被形式所控制和异化,丧失掉写诗的大部分乐趣。一些诗歌之所以小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们在诗歌中所展示的趣味正变得越来越狭隘。他们对话的客体过于狭隘,他们不是面向生活写作,而是面向诗人和诗歌史写作,他们只和自己人呼应,他们的诗歌创作深陷在诗歌史的语境中无法超脱出来,他们在诗歌史的缝隙中求生存。诗歌成了诗人们羞于示众的隐秘趣味、自我陶醉的个人呓语以及地下接头的秘密暗号。诗歌小众,实际上是诗人的创作和生活窄化的结果。
(《好诗非要拒绝大众吗?》,《文学报》,2015年2月12日)
●赵勇认为在中国新诗史上,写诗大概是诗人的专利,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诗歌中,工人总是既“在场”又“缺席”。在场是因为诗歌中有了他们的身影,缺席则是因为他们的沉默或失语。工人诗歌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它们既没被公众广泛认知,似乎也没有完全进入诗歌界主流人群的视野。但工人诗歌是一次巨大的进步,甚至可称之为诗歌革命。从当今的工人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主体性的苏醒,看到个体经验不无悲怆的表达。他们把自己的歌哭提炼成诗,我手写我口,已不再需要代言者捉笔操刀。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不仅已开始说话,而且是在以最高级的语言说话。这种话语是对中国诗歌界的重要提醒,也是当代诗歌的希望所在。
(《工人诗歌:用最高级语言发出的底层之声》,《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2月10日)
●史习斌认为一般来说,诗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高度概括,其语言需要简洁凝练、蕴藉朦胧,而口语是一种自动化的生活语言,突出的是它的沟通功能而不是审美功能,所以口语与诗不大能够兼容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无视口语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更没有权利否认它存在的合法性,阻止其进行多方面的艺术探索。生活的松散自然状态与语言的口语化、自动化状态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用口语写诗、用生活语言传达密集的诗意就是可行的。口语诗会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惊喜,即使这种惊喜是百里挑一的比率,但她终究会来临。
(《口语呈现诗意的可能性探索》,《作品》,2015年2月上半月刊)
●邹建军认为一首诗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内质还是外形,这是一个在理论批评界引起争议而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并且也影响到创作界对诗歌认识上的误解。他认为,一首诗的成立首先要有内质上的发现即诗美的闪亮;其次要有在形式上的讲究即形成一定的外形结构,对所表现的内容有重要意义;再次诗的外形往往是由行与行、节与节、韵脚与韵脚、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最后内质与外形的有机统一往往是一首诗的最高境界。以此来看陈有才的近作,虽然可以基本上肯定其思想艺术上的特点,然而有的作品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论诗的内质与外形问题——以陈有才近作为个案》,《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陈超认为诗歌是由感性而生的。但是,再好的感性,也无法绝对保证我们写出一首好诗。诗是语言中的语言,这意味着从你感到的世界到你写出的“诗的世界”,中间还有与语言艰辛地提炼、磋商的考验。而缺乏技艺,你感觉的浓度就被磨损掉了。你必须从普泛的人类感受中提取出真正属于诗的特殊的东西,在现实经验与美感经验中谋求到美妙的平衡——体验和感性,当然要求诗人“能入”,但真正写好感性,其奥秘却还在于审美关照的“能出”。入与出,是诗歌旨趣中的“悖谬”所在,也是对诗人创造力的舒心的折磨。如果把握好这一分寸,就会使我们的诗在“可言之境”的上层,有力地暗示出另一个更鲜润、更神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博大的“无言之境”。
(《诗艺清话一百一》,《诗选刊》,2015年3月上半月刊)
●吴玉垒认为作为对“学院写作”晦涩难懂和作为对“口语写作”浅白粗鄙的双向反动,沈鱼和沈鱼们的写作,选择了一条既向大众阅读靠拢又不想放弃诗歌那份高雅的中间道路,写出了一批有艺术难度,也相对平和、明朗的诗歌,为诗坛贡献了不少成功范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魔鬼般地被释放了出来。半文半白半口语半翻译体加之某些修辞上的乏力,初读好像很有个性,再读却感觉疏离、恍惚。但诗人津津有味地耽于这种庸常性的制作中,一再把本属于那种平常的带有个人焦虑的浅层次生存状态和本属于牢骚级的大众情绪波动精心地嫁接在人生命运的枝桠间。然而,貌似“相像”的道路终究不能抵达诗歌内部,诗人所有的“功夫”以及诗歌所有要表达的东西最终都被牢牢地牵粘在了字面上。
(《缠绵在臆想的秋风和离别里》,《诗刊》,2015年2月下半月刊)
●罗振亚认为草根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化妆的诗歌。草根诗歌一般不拐弯抹角、矫揉造作,有时甚至舍弃了形容词与修饰语的枝蔓,只剩下灵魂内涵的树干,本色质朴却又强悍地直指人心。同时,对凌空蹈虚抒情路线的规避,和对日常生活情境与经验的俯就,使草根诗歌在无意间比一般诗歌更关注对话、细节、事件、过程、场景等因素,与直接抒情并举,将叙述作为建立、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酿就了一种叙事诗学。草根诗歌来自一个个独立的“小人物”,但它们拼贴、聚合在一处,却通向了人类深层的共性情感和经验,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精神面影。
(《生自草根,未必不可长成大树》,《中国艺术报》,2015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