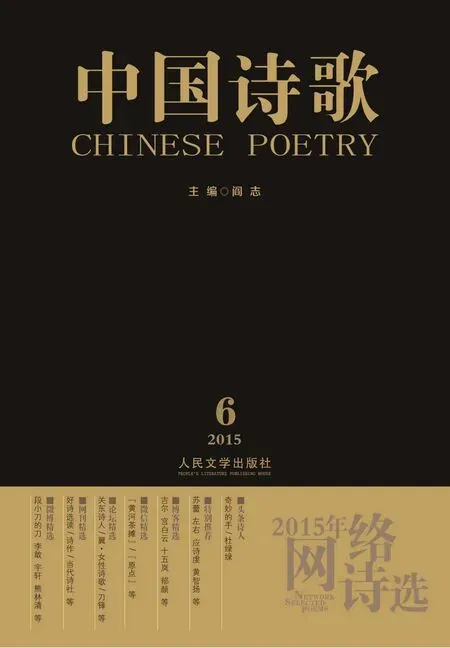网民写作现象及其他
2015-11-15赵卫峰
□覃 才 赵卫峰
诗评诗论
网民写作现象及其他
□覃 才 赵卫峰
动与静:网络诗歌状态简述
世纪之交以来,网络传播方式(网站、论坛、QQ、博客、微博、微信)为诗歌提供了一个宽松、开放和相对自由的写作、阅读、评议及传播环境,也让人们的参与与诗歌的形式、内容和审美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可以说当下属于一个庞然的“网民写作”诗歌生态,其“使命”,就是不间断、大批量地推出“网民诗人”及层出不穷的诗作,但诗作的数量与质量不等一开始便是持续的问题。
显然,不断被复制、被克隆的“网民诗人”或“写诗的人”带着他们的产品反复呈现,其庞大杂乱的诗作从某方面说的确扩大了诗歌写作,甚至为当代诗歌营造了一个充满可能、充满希望的高潮错觉。但真实的情况却是,网络与这群网民诗人让诗歌不断地“报纸化”,使诗歌像报纸一样每天不断地被印刷、流通,阅后即止。从这点上看,网络时代的诗歌生态,是诗歌不断膨胀又不断远离诗歌本身、诗体趋于弱化的时代。与以往任何时代的诗歌相比,现阶段的诗歌充满了网络的随意性、放纵性,真假难辨。网络在不断地推出诗人、诗歌,同时也在不断地致使诗歌“贬值”、失效。剔除两者近似相互抵消的对立之力,诗歌似乎并非表面的勃然复兴景观,相反,网络不断重复“推出”与“淹没”写诗的人,尽管也为我们挖掘了一些有天赋的诗和为推出年轻群体提供助力,但更多的是一种“无效之举”甚至有些“多此一举”。它在搅乱诗歌的秩序,又不能即时地重新形成可能的秩序。这种景象似乎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近年批评视角亦不断露出“泛诗化”、“浅诗歌”、难度降低之忧,并不断提出诗歌标准建设的原因。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有天赋的诗人把写诗仅看作一种自我精神调谐与个人行为,他们甚至不关心诗歌报刊这类传统传播环节与平台,但网络媒体适时帮助了他们的呈现,这是网络传播的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它为我们带来失效的同时也带来有效,一些沉静的好诗人、好诗歌不断涌现。这几年,90后诗人群体快步上路,除了这一群体自身的年龄优势、文化基础及起点优势外,网络的感染与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也可以说,90后诗人群体是一个网络化的诗人群体。虽然我们也相信,没有网络,90后诗人群体也能通过其他的媒介、方式上路,像70后、80后诗人一样,无网络的催动,而在时光的磨练中自成一体。那么,从这点来看,网络其实就是一种传播环境,属于外力。对于写作者,内功始终都是关键的。
网络时代的诗歌书写,对于写诗这一被称为技艺、手艺的艺术行为而言,无论对其准确性的分歧有多大,我们还是可以划分出两种迥异的类型,一是网民打字(汉字输入),二是诗歌创作。“打字”是网民存在于网络时代最鲜明的表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打字与他人交流、说话,它既是语言,又是行为。打字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言,只是进行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但是对于“写诗的人”(网民)群体来说,就是他们的“诗歌写作”。网民的诗歌写作,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惯性问题——没有区分清楚日常语言、说话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差异之处、接合之处,对他们日常所用语言的“处置”、提升更是缺乏相应的意识、技巧,“随意性”是他们的总体特征。
这似乎是诗歌网民不能“成为诗人”(当然他们或许并不真正在乎)、其诗写不能上升而总是平面化、自我复制化、情绪化的缘由。日常的“打字”是迥异于创作的,虽然任何诗歌创作都需要进行打字输入的环节,但真正的诗歌创作语言并不是日常的事务语言、说话语言、信息语言,它是一种有指向、有思考、有意味的诗歌思维“调试”之后的语言,它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够展现出超越日常的事务、说话、信息的审美性、价值性。从这一点说,网络环境对于广义的诗歌写作与传播而言,存在着如何看待、处理好日常与非日常关系的纠结。
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区间表现出来的频繁的热情的诗歌动向——此伏彼起的淹没与反淹没——对专业的诗人群体的影响亦是巨大的。对相对成熟和有成绩的他们而言,一方面,传播与交流使他们更加奠定了社会层面上的身份与地位,同时传播之“双刃”效果也如影随形,一些著名的写作者显出了停滞,一些写作者频频参与种种诗歌活动,当然——有一些写作者则充实与更新了自己。这种现象在与网络伴生的80后诗歌群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更年轻的80后末期及90后诗歌群体,网络传播方便和加速了他们的感觉提升,充分提供了关于诗歌的种种知识与信息,似乎可以预见,这一年轻群体的步子会更多,如果他们能真正有兴趣地持续,当代诗歌的开放、宽容和相对丰富以及在既有诗艺、诗思基础上的对诗歌经验边界的拓展,应该主要由他们完成。
诗歌的网络时空对于诗歌传统、既有诗歌文化模式的冲击是显然的,虽然其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攻与守的局面。但公开的纸质诗歌传媒的默许、认可、兼容与拥抱已然众所周知。话语权作为一种杠杆仍然对网络诗歌保持了距离,如果从最近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诗歌获奖作品看,我们会注意到,诗人的综合成绩与影响力,远比诗人的写作的更新更重要。网络环境最为凸显的现时表达,难道只能存活于网络环境中?当然这不只是观念的问题,也不只是出于诗人本身的因素。
说到观念,网络环境对于诗歌的作用其实仍然不那么可观。这说明网络现阶段更多是作为外力、作为工具的局限。但重要的是,网络环境正催动着诸多可能模糊的存在并努力使之清晰,譬如对诗歌“地方性”的强调,对日常审美的实践与探索,对西方资源的汲滤等。
远与近:网络诗歌环境里的读与写
网络的时代,读诗、写诗变得更为必要、显现。网络所带来的不是人与人之间“近”的关系,相反却是一种“远”,比任何强调地面距离远的时代都远。只是网络的“远”,它表现为一种声音与知觉的“近”。不管相隔多远,即便远在太空之外,甚至死亡,网络都能为每个人做到声音与知觉的“远在天涯,近在咫尺”(录音、影像)。几十年来,对于网络这种“远”“近”性质调换带来的异变,现代人的内心也产生了相应的需求变化。不管地面距离、他人声音的远近如何缩短、变化,不管人与人快速相见的愿望如何得到现实的满足,现代人更渴求一种心理上的朴实而又虚无的“远”“近”相适应。诗歌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它的本质也可理解为一种声音、知觉,对任何时代的人而言,诗歌一直都充当着一种朴实而又虚无的“远”“近”形象,真真切切地产生本身的意义。
在今天,网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远”的时候,它就时常需要一种非常“朴实的近”;网络诗歌的忽“远”忽“近”的特性,能够应和现代人心理上敏感的需求与变化。现代人大多要面对高负重的工作、生活压力,在工作、生活之余虽然有酒吧、KTV、影视、网游、聚会等娱乐、刺激且见效快的松弛方式,但夜深人静,如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平静,相反却更加的疲惫、挣扎与茫然失措时,“诗”就可能出现。
诗歌(指读诗、写诗)通过网络提供了一种“朴实的近”,能够让现代人进行自我治疗,消弭虚无,能够随时随地地提供一种内心的“近”。这也是为什么“为你读诗”、“读一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客户端流行的原因——读诗可以非常“近”地触及现代人自我返回的心理期待,让人安静,让人满足。
诗歌网络的“近”是一种物质、空间的“近”,具有物感觉体验的物理性,对于每个现代人来说,这种“近”时常向“远”转化。我们所抱怨的读不懂诗、不会写诗就是一种诗歌与人的“远关系”。诗对人来说是无用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是另一种诗歌与人的“远关系”。从这两个方面看,诗歌是被排除出人群之外的。人群不会写诗,读不懂诗,诗对人也没有实际的意义,指的就是诗歌非常边缘、无用、虚无,没有现代人渴求的具象性,与现代人群相隔甚远。但是,诗歌的这种“虚无的远”并未真的远离每个现代人的心理、审美、观念,它始终存在于网络扩张边界的边缘,并作为最虚无的实在,最绝望的希望存在,始终捍卫诗歌,让人不会遭遇真正的失望与消极。所以,不固定,时远时近,若即若离,网络诗歌自然会成为部分现代人劳累、疲惫的最安全、最宁静的入梦之途、栖居之所。
诗歌是一种即时的形而上学(加斯东·巴什拉),这种形而上功能在哲学上往往反映为自我黑夜或者自我深渊,它们具有一种宁静与透视属性。诗人写诗就是要沉入这两种自我和属性之中。他们运用语言、甚至是直接运用网络语言,就是要赋予黑夜与深渊一种语言的自我结构进行自由表达(读与写)。诗人与读者就在自我和黑夜、深渊、言语中获得个人存在感——通过诗歌的读与写之间的“远”与“近”感觉的体验。值得留意的是,在人们实际的感官知觉之中,一个人的表达比一个人的倾听更困难,一个人自己写诗的满足比让另一个人读其诗的满足更为深刻。由此可说,网络时代,写诗是种非常难得的能力,如果你能让人真正地注目,静心阅读你的诗作。
在当下,读诗、写诗行为事实上为部分现代人构建起一个“远”与“近”的转换通道。这种形而上的而又真实的穿梭之感,也成为了部分现代人相对真实和充实的存在形式。当今网络社会的大语境中,诗歌看似被推向了不需要的存在境遇,写诗、读诗也被看作与当今社会脱轨的行为,它永远只存在于部分人的身心。然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读诗、写诗无疑是最为愉悦的行为,它能够缓和现代社会、现代人诸多的焦虑、茫然和不安全感。
在网络时代,每个现代人都是一个网络的终端,阅读诗歌、接受诗歌变得容易。网络读诗、写诗对于部分现代人来说,是每日之后一个安心的入梦过程。这也是一直退居主流文化边缘的诗歌又一直可以作为精英艺术、精英文化存在的关键所在。
松与紧:网络诗歌及其选本
由于网络媒体的自由、开放,加剧了诗歌的自由与诸多不确定性,让诗歌处于相对“膨胀”、“虚荣”的境遇,对网络诗歌进行有效的节制、可行的审视、可能的导引成为很多人的想法与行动。将诗歌从虚拟的网络接收至传统的纸质平台,是行动之一种。
近年来,中国诗歌之传统的、公办的、专门的8家媒介《诗刊》、《星星》、《诗潮》、《诗歌月刊》、《诗林》、《诗选刊》、《绿风》、《扬子江》均积极介入诗歌的网络运行轨道并进一步焕然。其中,关于“网络诗歌”的选本,和《绿风》“网络诗歌精品特大号”一起,异军突起的武汉《中国诗歌》亦有“网络诗选”专号,它们均以不同的诗学态度对网络诗歌进行了可行的审视。
这两个刊物每年的“网络诗”选本根植于网络时代的整体背景下,进行年度网络诗歌扫描透视,从其所透视的不同诗人群体的知识背景、诗歌趣味、表达倾向来看,差异的选本态度实际上指涉的是两者不同态度的网络诗歌、现代诗歌发展规划、导引。我们不妨以2014年《中国诗歌》与《绿风》“网络诗选”专号文本对两个刊物所持的网络诗歌态度及倾向,略作观察——
1.网民写作。
网民是一个层次参差不齐的文化群体。藏身于网民中间的网民诗人,他们的诗歌写作实际是平民写作民间写作流变的新形式。这个新形式在网络的时代,继续后朦胧诗以来的平民意识、民间立场,继续为“底层”、“为打铁匠和大脚农民写诗”(李亚伟)。这种肯定自然体现了对网民写作的鼓励与可能的引导。
从《中国诗歌》对“网络诗选”栏目的设置,可见“独立”、“民间”这一公开倡导的立场的落实,如博客精选、微信精选、网刊精选、论坛精选、微博精选及特别推荐的设置,表现出刊物对网络诗歌的全面又集中的有标准的选择,以及力求展示网民写作的媒介、诗歌类型、流派等多样风貌的努力。“特别推荐”栏目采取集中评论推荐的形式,对10个诗人进行探讨,体现出置身网络又跳出网络的观察意图,表达了编者有为有心的独立诗学态度;这与“头条诗人”作为《中国诗歌》每期的重头栏目所倡导的诗学立场是一致的。
《绿风》“网络诗歌精品特大号”设置的栏目主要为:组诗部落、豆荚来信、时光匆忙、蝴蝶·蔷薇·鸟鸣、温暖情怀、秋风与月光、精美短诗等。这些名称明显体现和谐意识、温情倾向,传统背景下的审美趣味更多一些。同时这似也透露出《绿风》作为一本公办刊物的姿势,以及对网络诗歌状态的一定节制或谨慎。网络媒体的表现形式远不止一种,《绿风》采用论坛发帖的形式选稿,这相当于设置了一个相对狭窄的规训空间,对于网民写作而言,这种规定性显然是喜忧参半的。
2.网民及其背后。
《绿风》对网络诗歌的观察分化到单个个人的具象身上,纯粹以单个个人的形式观察每年的网络诗歌特征与变化。《中国诗歌》似乎重视群体性、区域性的诗歌归纳。我们知道,诗歌写作与地域关系相对保持密切,几十年来的网络诗歌也是如此,是不同地域的网络写作群体的综合呈现。对这彼此联接、交叉而成的网络群体,就需要凭借比之更小的群体单位进行具象观察。网络诗歌、网民写作的地域性群体表现,通常可以从个人所具有的知识背景、诗歌趣味、语言倾向来透露。2014年《中国诗歌》“网络诗选”中展示了甘肃煤城文坛论坛、藏地诗歌群·同题诗报、关东诗人、中国·天津诗家园等这些地域性群体。网络性的诗人笔名是网络诗歌的明显具象表达。从2014年《中国诗歌》与《绿风》的网络诗歌选本中,诸如随处春山、翩然落梅、冲动的钻石、古月灵秋、万世长青、湮雨朦朦、血色湘诗等笔名,可以看到网络时代的诗人笔名与以前的差异,在这之外,随意列录些笔名似乎我们都不会陌生,如湖北青蛙、水晶珠琏、训练小猪天上飞、茉棉、守护月亮之树、衣米妮子、甘谷雪痕、一只铃铛儿、典裘沽酒、举人家的书僮、大头鸭鸭等。显然的是,这些笔名有一定的网络特征,有的用英文、韩文或少数民族音译汉字取名。“网络性诗人笔名”可等同于网名,网名即是网民的称谓,而一个网民写作者就是网络诗歌的一个“具象”。这些网络性的诗人笔名在刊物上呈现,体现出刊物对网络性笔名的认可、接纳,也是对网民写作、网络诗歌的认可与接纳。网络性笔名在诗歌网络环境中的大量涌现,或许表明写作者的主体意识强度,也暗示出写作的相对自我及纯粹度,写作更易成为个人性的精神需要而非以此为业而功利化。
那么,由此亦可略见网民写作是很有效的,至少对网民自己来说。网络诗歌如果有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网络有效。当然这只是初级阶段,在初期,诗歌网络似乎是诗歌网民“玩”的地方。这种“玩”的态度当然会有变化,变化则在对比、交流中体现于对语言的态度、对情感表达的趣味上。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诗歌具有文化的、社会的属性,在网络诗歌形成的表达、运用方面都变得可操作时,即网络时代的网民都可以随意进行语言驾驭(诗歌写作)时,诗歌会在极限的位置下降而不是仍然上升,诗歌最终会变成通用的语言或符号,并且能够被社会大多数人获取、使用、操演,可以称之为“一种带有文化符号性质的语言游戏”。无数时代特性的语言,它们的诞生、变旧,及成为历史便是证明。如果自己不想沉底,不甘落后,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进一步“玩好”。
当然大多数的诗歌网民可能只想玩玩而已,自由自在地获取、使用、操演几乎所有的正常的、特殊的、新诞生的语言,像在“玩”一种随意的不需要严格规则的游戏般,信手拈来,“玩”各种各样的语言,这种随意性在传统纸媒那儿当然行不通。《中国诗歌》与《绿风》所使用的论坛、征稿邮箱的“选稿”形式,是对网民写作、网络诗歌有效性判断与把关的一种直接而必要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符合语言规则、语言思维,符合诗歌规则、诗歌思维的网络诗歌被留下来,它们是网民写作、网络诗歌的有效性的部分体现。两个刊物的年度网络“选本”由此所表现出的标准或关卡,深层看是鼓励与肯定中的鞭策,对于行进中的网络诗歌颇有意义。
如今,诗歌的文化“娱乐”作用随着网络环境的宽松不断得到挥发,在各种网络观念、网络意识的不断撞击交织的动态结构中,娱乐至上、狂欢不止成为各种亚文化实践、网络符号的标签。诗歌在承受网络动态结构表现出的各种问题、各种状况的过程中,一些网络性的时代特征是明显的。二十余年来“网络诗歌”在发展演变,其自身也不断地承受网络娱乐、狂欢的极端轰炸,不正常的“玩性”、日常性、生活性成为网民写作群体所认为的发展试验,不具规则、不受控制、泛滥的网民写作群体作为直接的参与者,时常让网络诗歌的娱乐化“试验”不断颠簸。
或许,最终诗歌会成为一种娱乐的工具、日常的用品、生活的装饰,同时也成为物质的有层级的标签、精神的有档次的安全套、梦想的有色彩的安慰物,但那是预期的事情。而目前,诗歌正在路上,正在经历网络,娱乐性为主,这可能是进步,可能是回归,也可能是一场不知所终的旅行……一切都需要静待时光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