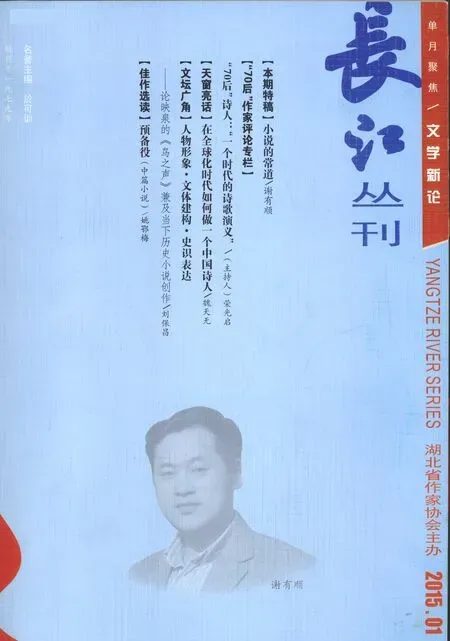批评还是溢美这是个问题
2015-11-15樊星
樊星
观点一束
批评还是溢美这是个问题
樊星
对于文学批评的不满,由来已久了。其实,真正的文学批评家是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是非判断的,可为什么现在的批评常常给人以要么不痛不痒、充满陈词滥调,要么过度吹捧、难以服人的扭曲感?因此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自由谈》杂志曾经倡导过的“骂派批评”名噪一时。那“骂”当然不是谩骂,而是批评家对作家直言不讳的批评。应该说,一直到今天,直言不讳的批评仍时有所闻,但比起此起彼伏的溢美之声,还是显得太少。原因何在?
一位批评家曾经告诉我,他为一位著名作家写过一篇评论,主要内容是赞美。到了文末,也就该作家作品中的硬伤提了一句委婉的批评意见。没想到就这一句批评引起了作家的不满。该作家因此发了一通抱怨,与这位批评家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类似的事情,文坛上常常有。那么,作家们为什么渐渐听不进批评之声了?是因为自我感觉太好?还是因为在这个广告无处不在的年代,在这个大家一团和气、见面彼此多说好话的年代,作家也不能免俗,喜欢多听到好话?尤其是,当围绕名家之作的溢美之词已经不断升温之时,那些小心翼翼的批评之声是不是就显得太“扎眼”了?另一方面,当批评家不断将溢美之声推向新高度时,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在无形中就伤害了批评的信誉?而当作家意识到批评家为自己开研讨会其实就是“吹喇叭、抬轿子”时,他们对批评家的尊重是否会大打折扣?
一切都不言而喻。一切也都值得忧虑。
现在的文学研讨会多。名家不必说了,新秀也急于崭露头角。也许,出于友情,出于面子,批评家在参加那些研讨会时应该说几句嘉勉之辞,但能不能不说“伟大”“了不起”“杰作”“里程碑”之类过头话?能不能在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研讨中重新彰显批评的理性与常识?从杜绝过头话开始,在理性的分析上下功夫,这是批评回归正常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作家,尤其是已经成名的作家,多几句或者少几句赞美,多几句批评之辞,应该无关大局吧。能够听得进批评之声其实是胸襟开阔、虚怀若谷、为人谦逊、坦坦荡荡的表现。而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一听见委婉的批评就马上变脸,其实是缺乏起码的修养与风度的表现。如此说来,营造良好的批评氛围,不仅需要批评家克服“多说好话”的庸俗心态,更需要作家从严于律己、从善如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起。只有形成这样彼此坦诚相见、共同携手前进的态势,才可能进一步繁荣当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
良好的愿望当然不等于现实。据我所知,有的批评家就因为一不小心得罪了名作家而悲观叹息。有的甚至已经淡出了文坛。我觉得这也大可不必。是非自有公论。只要自己的批评是出于文学的良知,只要作家在批评的写作中体会到了发现的愉悦,夫复何求!就像苏东坡《定风波》中写的那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