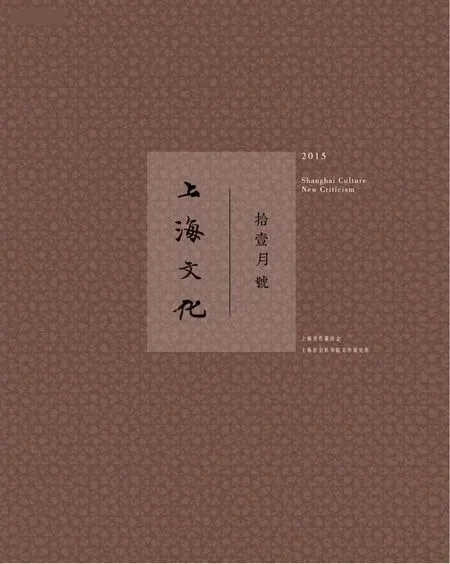风暴的形成
2015-11-14阿西
阿西
风暴的形成
阿西
1
现在,我冒险从诗的整体语境而不是具有话语霸权意味的“1990年代”来谈论李浩的诗,来追寻诗正在步行的词语路径,我还要尽量避免碰撞上当下性这个很拙劣的提法——那就是,遵循诗就是诗而不是任何其他这样的根本标准。李浩本来就有一种脱离的倾向,他的诗学世界几乎具有反向写作的一般特质——不受制于语言的羁绊或者束缚,而是解放词,解放诗,逆潮而行,向上游回归诗的本源。他如若真如鲑鱼返回词语的出生地,那必是遍体鳞伤血染江河的壮举。
他试图建构庞大气象的诗歌,一种构建在历史文化序列气场的恢宏与空茫——这是一次未知的诗歌之旅,我似乎不确定他是打开了生活之门还是陌生的语言之门。
乌鸦喜欢站在坟头上拉屎,并且大声歌唱。
兔子就藏在草丛里。仙人说那里是风水宝地,
是死人的天堂。次年冬天,天气干燥,
野外寒风四伏;我面对风口,放了一把火。
——《在坟场》
他把这种来自乡愁里的撒欢行为,不入诗的场景写成有些神圣的“义举”,关乎的不是遥远时代的记忆钩沉,而是一种决意于“风水宝地”的放火重生。语言的广阔需要诗的鼓荡之帆,与其说是诗的抱负不如说是词的放纵,而这本质上涤荡了时下酸楚的文人气写作。他尽可能绕过精致和雕琢的嫌疑,尊重诗的客观属性而不是痴迷于格物趣味。我知道李浩生活在靠近安徽省的河南某县,那里直到1990年代后期仍无法摆脱贫困对个体精神的桎梏与摧残。他胸中有一大块石头压着,正在形成风暴。
是的,一个放弃风和日丽的人必定会与小我之诗相遇并不以为然,李浩用他的内在气质努力和“今天写作”实现对立的诗歌格局——
拿起刀切开它,就会跳出一个活的夏天。
它露出黑色的牙齿,溢出红色的汁液。
它们就是地摊上的西瓜。我敢肯定:
它们一定是我种的西瓜。它们的肚皮上
布满的地图:一定是我将入住的房子;
一定是我种的竹叶菜,鸡冠花,含羞草……
一定是我养的石头,群山,雪一样的绵羊……
一定是村落南面的稻田和北面的果园。
——《大写意》
这首诗并不长,被我省略的下面几句将这个大写意抽象了。“大写意”就是写生活,几乎不是写诗。或者说这首诗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生活的窗户,得以看见实真的田野,但又比印象的田野更令人颤栗——这个田野上,正在溢出红色的汁液,露出黑色的牙齿。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实真,让我们忘记了诗,而更像是回到历史之中,回到没有被各种信息技术蒙蔽的田野。这个田野承载着人们的内在忧伤和朴素的浪漫情怀,这比把田野变形成文字的炼狱要更有意义。这是不是有点1930年代汉语的风尚呢?
还要谈一下李浩的诗学核心,这个看似原则性命题被他散文化的笔触一笔带过,却是值得反拆来细品的。“我喜欢把这个结果比喻成时间与大地孕育的花朵,在这朵鲜花即将开放的那个特殊的时刻,在这种迷离的精神状态中漫游的诗人,是将‘死亡变为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布罗茨基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写诗也是练习死亡”。李浩把诗比喻成时间与大地的花朵,并视为“死亡变为胜利的”重生,将布罗茨基的“练习”往前推进了一步。从这个角度引向深入,就会洞见人性无限的诗意空间,而诗终究要胜利于狭窄的恶俗,胜利于凄凄艾艾的小情怀小趣味。胜利源自于“心尖上的毒素”。
胜利源自于“心尖上的毒素”
2
这些年来,中国的诗人们几乎一致顺着艾略特、叶芝、奥登、史蒂文斯等外国现代与后现代诗人的写作经验,进入自己的写作,将中国文化的血脉简单置入大洋彼岸的语境之中,并且似乎形成了殖民性优越感,并称之为现代性的本土化。当然,在只有百年新诗史的演进中途,没有西方我们就无从写诗,但这也让汉语诗的写作如何形成自己的尊严成了一个问题。不能说这种文化的交融就是问题本身,李浩也列举出一些中外诗人的名字,但他是在思考如何跳开被经典化限定的诗学标准,写出汉语新诗的风貌。就诗的志趣来说,李浩不为时下流行语系所左右,且出其左右,继承传统为了反传统。为此,李浩的诗歌不回避任何词,甚至要去多多地启用一度被忌讳的大词——他的这个用意是否蕴藏着更大的目的呢,是否可以让诗获得大义、忘我之境界呢。如果这样,那么李浩的写作就不是伪先锋,就有了“霸占山河之气魄”。
“尘土抖落在豪华之上,我依然沉重。/脚步提不起我们的倾斜”。这个“豪华”很有些讲究,它在向汉语本身的华丽靠近,去大胆地靠近,而不是一味使用“黑暗”之类的重金属词。因为,过度使用“黑暗”的辞藻,说白了很可能是障眼法,并未触及本质的黑暗。当然,生活未必真的已经足够“豪华”,我们在“尘埃”中未必能够真的“豪华”起来。那么,我们到底有无必要去“豪华”一下呢?我们能否首先让语言先于生活“豪华”呢?李浩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倾斜”的时代,是需要“脚步”来纠正的,尽管他使用了不确定的“提不起”这样的表述。语言越是“豪华”越是虚构的形容,但也就更反证内心的“豪华”。在这个“豪华”的影子下,李浩的个人生活却正经历着必须克服困难的前程。我们再读读这首《牧人的黄昏》:
沉默是同样的,当你用别人的
母语自言自语时,我就走进岩石中,点燃这座黑暗的房屋。
那房屋现在流淌光亮的颂歌,
就像在神的爱内飞舞的柳絮。
我站在我那强大的保障里,物体就得以展示出它的气质。
我应该将历史中灰暗的细节
拍摄下来,在你的眼前扩大它。
如同帆布上的投影,酷刑
就是在这个时刻里,开始的。
我敞开额头上吹起的波纹,
雷电在我身上穿行时的疼痛,
现在已是神的爱内飞舞的柳絮。
这里有这样一组词“沉默——母语——黑暗——颂歌——神——爱——强大——历史——酷刑——雷电——神——爱”。这是很有趣的阅读实验,几个关键词串联起的“牧人黄昏”是一个从母语里歌颂爱和回到爱这样的精神皈依历程。就好像我们越是远离了故乡,故乡却越是扎根于心的土壤。李浩的故乡就是他的母语写作,而不是形式主义的牧场。所以,只要是他身临黄昏,就有雷电在身内穿行,并激扬起爱的渴望。这首诗以其浪漫的“大耗”之象,重现了形容词的魅力。当有人将形容词几乎判了死刑,名词和动词大行其道之际,李浩的冒险是否有效,是否能帮我们回到诗原始的粗粝呢?当然,就个人的气势而言,诗越是驶入没有设防的毛地,各种可能性也就随之而来。李浩的诗里大词随处可拾,正将诗带出主观现代主义的泥沼——“这里没有我的神,我没有故乡。这里是一片人造的奸邪之境”。这明显触及诗的大课题,触及个我与时代的困境,已经不是幻觉中的“豪华”,一点也不是,而这并不该归结为语言的特色范畴。
3
我的墓碑上只需刻上四个字,那个个人
回到诗人的简谱,这个1984年出生的青年诗人走着一条与同辈诗人几乎完全不同的迷途之途,他甚至连大学都不情愿读完就去选择“按自己的心愿生活”——个人化的读书写作。这样的选择不仅凤毛麟角,也很可能给自己不断带来新的难题。从这个角度看,李浩对自我的认知明显超越了普遍性,他属于早“醒来”者的行列。我这里用“醒来”这个词注释他写作的另一个重要方向——以个人存在对应诗的庸俗与普世曲调。他喜欢丹麦人说的一句话,“我的墓碑上只需刻上四个字,那个个人”。甚至为此将自己的写作向更深的孤独靠近,向绝对靠近。他以个人为信念,以使徒的存在感去忍受一切。“醒来”者不屑于身边的早晨和风景,不屑于邋遢的叙述,更不屑于被他人发现。他喜欢沉潜在那个个人的世界里,做一个神秘的黑衣人。
我回去,我打开关闭我的门。我进去,
室内的雪、阔达,而这不是我的。
我送走了很多朋友,却无法把自己送走。
我站回去、成了一个坟墓,而那气息
变换着。沉睡在光明之中的孩子,
是我洗净的肉身上,所留下的空地。
——《困境》
这首六行双行体诗泄露那个个人的天机——谁在困境之中走进“门内的雪”,这是否已经将“我”置于绝对孤立无援的境地,并且还送走了自己的朋友,让这个“困境”成为绝对的“空”,只剩下无法送走的自己。李浩并不是惧怕“困境”,反倒是期待这样的“困境”出现,他愿意静享孤独。我知道他是有信仰的人。因而,这个“困境”即使成了坟墓,坟墓里居住的仍是“光明之中的孩子”。这首小诗,三层空间,逐渐放大——从“门内”世界到户外“坟墓”,再到“光明之子”,那个个人始终是诗的核心与灵魂,这有点像神的居所——洗净的肉身。这种“困境”俨然是化境,也是无我之境,只有诗与心的二元合一的修为。
去年7月末,我和李浩曾在河北的一个庄园里同住两个晚上,聊的最多的是他自己的过往,是他那些埋在故土之下的贫瘠与愤懑,是他对诗所给予的关注与信心。是的,信心这个词是一个好词,尤其是对诗人来说。我常常想,我之所以如此年岁仍没有对诗有所建树,就是源于一直缺乏信心,虽然断断续续写了几十多年,几乎都是跟在别人后头,鲜有“那个个人”的存在意识。李浩十几岁的时候就有“那个个人”意识的确立,还有什么比这个确立更接近诗人的理想呢——
我忍受着,忍受着高墙,忍受着灯,
忍受着水管中哗啦啦的水声。
我学着倾听,强迫自己
安静,祷告无词。
风暴中你全部的隐痛,
已进驻冬日的星辰。
——《悼马雁》
马雁也是我最喜欢的女诗人之一,虽然她活着时我和她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李浩挖掘出的马雁可以看做一个自己的替身,马雁成为他此在的那个个人。这和一般意义上的“悼诗”有所不同。李浩自然不会忘记写什么都是在写自己这样一个简单命题,是马雁之死让他忍受着“灯”和“哗啦啦的水声”,让他“强迫自己/安静”,然后死亡才会“进驻冬日的星辰”,去昭示和开启新的天地,进入那个个人的写作地带。
“我想说出真相,但感觉徒然。”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已经在黑夜里发力,要形成强劲的风暴。“红色:啊,火。是的,烈火。”他的诗在黑夜里燃烧着词语的核子,正在接近诗歌的某个转折点——祛蔽和去弊,只当写出独属于那个个人的诗章。
你飞过大别山你飞过农田
你飞入橄榄树林飞入花园
你站在陡然竖起的石碑上
你以神的名义向深谷祝福!
这首《青春诗》酣畅淋漓地宣泄了诗人激荡的情怀,诗人在为那个个人而自豪。还有什么比那个个人所形成的风暴令人充满期待呢。
4
当然,所谓大格局大气象的写作,本身也是难度最大的写作。而就我读到的李浩这些诗来说,我想可能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去解决,以专业精神去解决——如何实现一首诗内在布局与外部环境的一致性,也就是那个个人的语言如何彻底打通现实习惯运行的语言,进入诗意干净的世界;是否在每一句里都保持着诗神自由通达的行走状态,要知道诗必须最终足够自由才能足够准确无误地完成诗;诗抵达了虚无并最终能穿越虚无,让读者品鉴到诗的造化的同时,亦进入心灵的造化,并使之让人敬畏和亲切。也许暴风的真正形成还需要大气环流的剧烈运动,还需要外太空引力的悄然变化,甚至需要地壳运动学。就李浩的诗来说,他如何将这些地理要素整合成有序的人文精神,然后造成天衣无缝的一个完整诗性空间,接下来的时间和光合作用同等重要。
听啊,天空在我的脑子里叫嚷,
我的世界,蓝里面透露蓝。
啊,那不是希望,无非是微风
——《白色峡谷》
这篇文章很难说对一个有新可能写作倾向或潜质的诗人来说有何裨益,但李浩诗中传递出的大气、恢宏和飘逸又深邃返璞的气息,已经在读者这边引起更多的阅读兴趣。一个诗的风暴已经开启,从“微风”开启。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