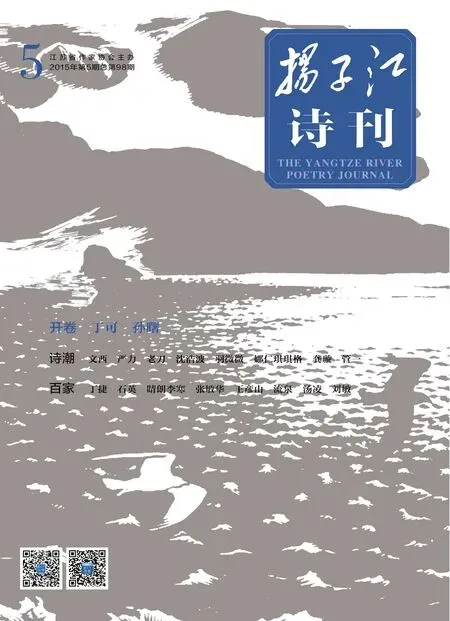乡魂苦吟成离骚——丁可诗歌谈略
2015-11-14孙曙
孙 曙
乡魂苦吟成离骚——丁可诗歌谈略
孙 曙
挽歌或绝唱
请容我先给丁可的诗歌换上景片,这是两则新闻,其一是《两会观察:10年消失90万自然村 中国古村落亟待保护》,其二是《〈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首发 贾平凹:乡土文学终将消失》。前一则说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算下来平均每年消失80个;后一则报道当代乡土文学的扛鼎人物贾平凹说了,乡土文学终将消失。其实,村庄不但是在消失,而且没消失的也日益“空心化”,只剩下些“九九三八六一”人口。乡土文学也在“空心化”,乡村叙事的作者集中在50后、60后,至多稀落地延伸到70后。丁可的诗歌其背景就是乡土社会的溃败与乡土文学的断流,丁可是乡野僻壤一位被忽视的优秀诗人,他的乡土诗是乡土与乡土社会的挽歌或者说绝唱,他以自己杜鹃啼血式的苦吟,将乡魂吟成离骚。
几乎成了丁可的标签和同名的是《母亲的专列》,这正是一首挽歌,悼念母亲的丧歌,孝子的哀歌:
母亲的专列
这是您惟一的一次乘车
母亲 您躺在车肚子里
像一根火柴那样安详
一生走在地上的母亲
一生背着岁月挪动的母亲
第一次乘车旅行
第一次享受软卧
平静地躺着 像一根火柴
只不过火柴头黑
你的头白
这是您的第一次远行啊
就像没出过远门的粮食
往常去磨房变成面粉时
才能乘上 您拉动的
那辆老平车专列
我和姐姐弟弟妹妹
陪伴着您
窗外的风景一一闪过
母亲 您怎么不抬头看看
只像一根躺着的火柴
终点站到了
车外是高高的烟囱
此诗广受诗人们的好评。送母亲去火葬场,抒情却几乎是零度,以母亲的专列这一陌生化的隐喻结构全篇,直到结尾句“车外是高高的烟囱”,才将事实明示,但全诗已结束,全篇蓄积的情感能量便往无边的深空跌落,不可止抑,悲不胜悲。全
诗母亲的两个喻体“火柴”与“粮食”,与两组对比——背着岁月走在地上与乘坐专列、母亲拉粮食的老平车专列与去殡仪馆的专列(不断出现的“惟一的一次”、“一生”、“一根”、“第一次”、“一一”强化了这种对比),丰满了母亲这一农村妇女的形象,善良、低微、安详、奉献,也无尽地表达了对母亲生活的辛劳勤苦的伤悼和孝子的哀痛。
在“地母”这样的神话里,早就埋下了母亲与大地、乡土的同一性,《母亲的专列》这首诗对于丁可诗歌来说,不单单是献给母亲的挽歌,也成了献给乡土的挽歌,哀民生之多艰,伤乡土之颓殒,克制到缄默与缄默下的热念与震裂到脊骨与时代的疼痛,成了丁可诗歌的象征;而其他一些感万物悦亲戚的篇什,则成了古典中国在当代的绝唱。
批判意识与乡土主体性的确立
丁可,生于1955年,童年曾在徐州生活,1964年随父返乡,此后一直生活在徐州沛县,高中毕业后务农多年,曾做过大队宣传队演员,1978年在《新华日报》发表处女作,长期在沛县文化馆工作。一直在当代文学体制的边缘,这颗诗星却以其坚定而从容的运行与闪光,引人仰视。丁可的诗歌创作几乎是在与外界无交流的隔绝状况下完成的,其诗歌能够保持一个独立于众声之外的独唱,几乎是一个奇迹。是的,丁可是有这样的诗歌《祖国,有一朵棉花向您微笑》,作为一个文化馆工作者,丁可应该还有其他的完成工作任务的宣传政策的作品,但丁可诗歌作品的多数,还是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姿态,独自演进,像哪吒削肉还母剔骨还父一样,外在的严苛变成了自己内在的自律的严苛,日渐远离“圣词”、“大词”,完成自己与意识形态话语的疏离,完成与颂歌体的分离。这是50后一代优秀作家共同的道路。
这种独立来自于乡村社会的赐予,一个农民之子,低微、贫贱,在各种忍受中才变成了“公家”人,丁可的目光里多了一份对社会的审视和批判。请看这首早期之作《刘少奇与好面》:
刘少奇与好面
1958年秋,刘少奇来江苏沛县敬安公社视察。为了呈现乡村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凡是刘少奇有可能光临的农家,公社提前送去白面。
确实是好面 麦子碾成的
惨淡的白 照耀着强颜作欢的
土陶面缸 葫芦面瓢 带缺口的碗
送面来的干部反复叮咛 这面先不要动
听指令后再开始和面
刘主席走后 面还要收回的
刘主席向敬安的田野走来
刘主席走进飘着炊烟的乡村
他揭开一户农家的锅盖
看见两个笑脸一样的葱花油饼
欣喜地对公社书记说
要把农民的幸福生活向毛主席汇报
刘主席走了
炊烟散尽 灶下只剩下冷灰
分到白面的农民都很听话
与白面短暂亲热的瓦缸 面瓢
火焰 配合得让领导很满意
作为奖赏 公社书记指示 两个葱花油饼可以
进入这个农民的肚子
其余的白面
没有来得及变身成面疙瘩汤
发馍馍 窝窝头
从面瓢瓦缸里爬起 返回公社食堂
直到十年后
被更名为“刘卫黄”的刘少奇
在开封蓬头垢面地死去
靠回味好面葱花油饼充饥的
那个敬安农民
双腿依然浮肿
农民和主席,共同的悲剧命运,作者在审视体制。“从把意识形态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到把意识
形态作为思考和反思的对象,表明人类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50后、60后作家大多没解决好创作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其实很简单,只要做到丁可说的:我不能不说人话,我的诗歌不能不说人话。丁可的批判性不但是政治性的,也是向着他热爱着的乡村与农民的,在《两个杀鸡人之死》和《两个老人的战争》中,为了芥子之利,邻人相互辱骂,甚至拔刀相向,软弱、善良下的愚妄、麻木、冷漠、残忍甚至疯狂,丁可揭示乡人人性中的恶与愚,这样的笔触,肖似拿着手术刀解救国民性的鲁迅,在这样的诗歌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现实主义,他坚定地走汉语文学中鲁迅等先贤开创的道路——真正的现实主义必然是批判性的。
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传语中,我们看到了国家意志,城市化成了党的先进性、国家的正当性的背书;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进展,新话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进入政府方针,各种乡愁工程开建,各种乡愁创作开写。其实,在这样的话语里,乡村是被“望”“看”与“见”的,它没有获得和城市一样的主体地位。而丁可的乡土诗歌,正是在乡土的主体意识上与之有别。乡土文学研究的大家丁帆先生说:“只有当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时,‘乡土文学’包括‘乡土小说’才能在两种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凸显其本质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的反衬下,“乡土”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意象被显现。对于丁可的诗歌,其价值确实是在城市化与工业化中凸现出来,但其创作对乡土文学概念的补充是:乡土也是本体,是本原,农作、自然、人伦不但应该是一种生活的独立主体,也是生活伦理、文学创作等精神生活的本体。丁可的灵魂是乡土的,自然,他最终的选择已定,他要回到乡村:修理一下乡下的老房子/咱们撤出城市/回到当年迎娶你的小院/回到柴草化蝶的炊烟下/回到小小虫的吱喳声里 鸡啼声里/回到不硌脚的月亮地/回到玉米中间 南瓜花中间/回到爹娘的遗像旁/回到离他们的坟茔近些的地方(《向故乡撤退》)。故乡,不是“泡在乡愁意识形态的福尔马林液里一条想象的脐带,一条苍老的脐带”,而是丰盈的生机处处。
强烈批判意识的现实性和以乡土为精神主体,正是丁可在当代诗歌精神中的独立价值与意义。
传统技艺的现代生成:叙事性与澄明
“传统在我们身上生长、挣扎、变得弯曲,最后将层层叠叠开放出来,如同花朵。”在丁可的诗歌中,你会发现其所使用的都是汉语新诗的传统技艺,但却面貌一新,与上一世纪90年代以降的新诗潮的一些诗歌探索与致力几乎同向同步,丁可用传统的诗歌语汇语法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姿态。现在虽然时髦到“后现代”、“后后现代”,但这些对丁可这一代人来说,无疑是两个世界的事。而且,对于现时代的中国,虽然GDP什么的排到老二了,但其精神建设的主题应该是现代性的建设,在社会包括文学等各个层面根植与确立人的立场。对于诗歌来说,体现在话语中首先是宏大声音的摈除,由于当代中国将抒情狭隘化到颂歌,所以新诗潮对诗歌的变革首先是对抒情的冷藏。我们看到,丁可的优秀诗作基本上都是如此,抒情几乎零度。
新诗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叙事性,这“‘叙事性’也不能仅仅理解为语言对‘物’的关涉,也许把‘叙事性’看成是文本和其置身的历史现实语境的相互渗透、修正更为恰适。”“叙事性”也是对先锋诗歌种种语言游戏的拨正,也是对诗歌叙述性传统的回归,在《诗经·公刘》《荷马史诗》等诗歌之源叙事性就在,新诗史上臧克家的《三代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都是叙事性的乡土诗歌典范。丁可诗歌的叙事性几乎成了他的诗歌标志,这种叙事性建立了他的时代人物志,清理坟头烧了一小块地皮被政府抓去罚款的秦北京(《一小块地皮》)、“垃圾堆上捡到开发商丢的死鳝鱼/她说还能喝汤 她很快活”的女清洁工(《她很快活》、“满身酒气,叼着烟,骂骂咧咧 /挨门挨户催缴提留款”的村委会副主任王六指(《王六指》)、体重比一袋水泥还轻的六十多的农村老人一上午要把30袋水泥扛上六楼(《扛水泥上楼的老人》),还有他日晒雨淋推着三轮车卖土豆煎饼的妻子黄二云(《我们家的小人民币》)等等,底层生存的挣扎煎熬一一如现,没有议论没有抒情,纤毫立现的经典写作的白描功夫,让诗歌获
得切入生活并让生活超越琐碎与瞬逝的能力,让卑微者永恒让痛苦显现神光。
在丁可的诗中,除了乡土人物群像外,还有可以称之为生灵的乡村动植物群谱,有《五只驴子》《那只蜣螂》《一只野兔》《一朵小棉》《小鸟》《刨地时刨出一只小青蛙》等等,那些被虐待等待屠杀的驴子、那些被售卖的泛着白肚皮的小鱼、那拔出的秸秆汁液开出的一朵小棉花,丁可是一位悯生者,《一对小鱼》哀悯所视不但是“几百条鱼婴儿 互相挤压着/都是尸体”,还有那日出等到日偏西的卖鱼人。作为诗歌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些创作中,其最优秀之作已经脱离了普泛的悲悯,而是达到一种文字时空中突然闪光的对视,超越了文字和生命局限的那种神圣的澄明,达到“对斯蒂文斯所说的‘精神的高度和深度’的全部尺度敞开的一瞬间的生动记录”,如《一只野兔》“我看见你在田埂上张望/灰黄的颜色 站立着/两只耳朵耸起/田埂两边是安静的玉米”,如《三只燕子》“飞起来吧 燕子/蹭着街边的秃头槐树飞过/我走过去 又转过身来望着/你们还蹲着 像三块穿着黑衣服的小石头”,这几句与达到物的澄明的弗罗斯特的经典之作《红色手推车》一样,达到了澄明之境,“澄明”也是新诗潮的诗学追求之一,虽然新诗潮的诗学中“澄明”与“及物”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作为一种诗学追求,丁可也在进行着这样的诗歌实践。
丁可对诗艺的打磨和取得的成就又不止以上所述,还有其对语言清简到极致的追求、诗歌结构的多样化、反讽的使用等等。“单质诗语所塑造的抒情主体往往体现不出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而复合诗语则具有哲学甚至宗教的底蕴”,丁可的诗歌正是在“复合诗语”上与传统乡土诗歌有别,不但在他的诗歌中追求镜像层次的多重,而且其诗中已出现思考生死之作,死亡在成为最终的悲悯,如《挖坑的人》《陌生的父亲》等,期待着在丁可的诗歌中,最终能够出现一片哲思的海景,诗歌语言能够成为诗歌话语。
作为一名县籍诗人,丁可在文坛的待遇也是文学体制中“县级诗人”待遇,近四十年的创作,丁可才出过两本诗集,一本还是香港出版社出版、自己打印的《啼叫的月光》,一本是一个文学奖资助出版的《母亲的专列》。生活蹇迫人情冷暖他已饱尝,对于诗歌对于文学,他也有了自己坚定的执守。也可以说与文学中心的疏离,也正成就了他,当上世纪80年代乡土诗重新复苏时,他就没有参与《山雀子噪醒的江南》这一类田园牧歌的合唱;当上世纪80年代末海子死后,所谓新乡土诗“麦地诗歌”鹊噪一时,他也没凑热闹。丁可就是丁可。屈原的泣血《离骚》将亡楚铭刻成了超越时空的光迹,丁可的乡土诗也走着同样的荆棘之途。
年登花甲,名利于我何有哉?老妻、家园、诗歌相濡以沫一生的都还在身边,夫复何求?子曰:六十而耳顺。耳顺者,惠也,达也。谨以此文为丁兄寿。
○ 诗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