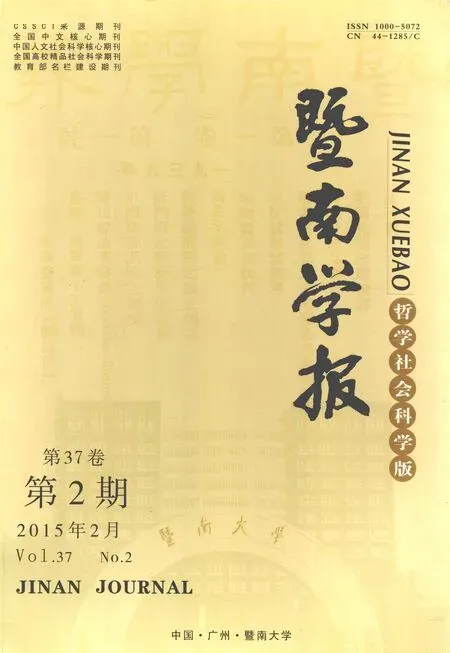道阻且长:二战后“南侨机工”的复员与南返
2015-11-14夏玉清
夏玉清
(云南师范大学 华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道阻且长:二战后“南侨机工”的复员与南返
夏玉清
(云南师范大学 华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南侨机工返国运输军事物质是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历史事件。抗战胜利后,南返居留地成为南侨机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南侨机工南返给国民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并导致国民政府与南洋华社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南侨机工及南洋华社的南返要求,国民政府会同各方制定南侨机工复员方案,1946 年10月,在国民政府、“华侨互助会”和南洋华社共同努力下,第一批机工踏上南返之路。受制于战后复杂的国内外因素,机工南返较为曲折和艰难,但在国民政府组织和协调下,基本上将登记的机工送回南洋居留地。
南侨机工;复员;国民政府
“南侨机工”的返国及其军事物质运输活动是南洋华侨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事件。抵达昆明的“南侨机工”在接受短期培训后,被分批安排到“滇缅公路”沿线及缅甸腊戍、仰光等地从事军事物质运输工作。档案显示,“南侨机工”克服气候、疾病、轰炸等困难,承担着国外军事物质接转、国内军事物质的运输等工作,是中国正面战场的国外军事物质运输的主要承担者,其中,有1000多名南侨机工在运输途中牺牲。
抗战胜利后,南返复员与家人团聚成为南侨机工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战前机工顺利回国不同,机工复员南返之路并非坦途,而是困难重重且耗时较长,战后的1946年10月第一批机工才踏上南返之路。南侨机工为何不能顺利返回南洋,其南返进程如何,机工南返问题成为研究南侨机工的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对于机工南返问题的研究较少,其研究或以报刊资料论述机工南返的概况,或以口述方式回忆机工南返的艰难历程,尚较少有学者以历史档案对机工南返的原因及南返之前各方准备等问题展开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档案和报刊资料入手,考察南侨机工复员的历史背景、复员之前各方的努力以及机工南返的进程,进而探讨国民政府、“华侨互助会”以及南洋华侨社团在机工南返中扮演的角色。
一、南侨机工复员南返的历史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的南侨机工亟待复员南返与家人团聚,但直到1946年10月第一批复员才动身南返,此时距离抗战胜利结束已一年之久。南侨机工复员南返历时较长主要是由于战后国家间的人员的往来受战后国际环境、中国国内局势、东南亚社会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制约。
首先,战后南侨机工南返受制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文皆称“联总”)的制约。就国际环境而言,二战胜利后,战后国家之间的人员来往受制于联合国成立的国际机构——“联总”的管理和安排。二战前,各国人民为躲避战争而迁往他国的人数众多,就中国而言,中日战争时期,居住在南洋的华侨纷纷返回中国躲避战争。“战时原居国外之华侨,被迫返国或流浪其他区域者,为数甚众。由于太平洋战事爆发,日本相继攻陷越南、缅甸及南侨群岛各地,此等地方,向为华侨积聚之区,其中激于爱国义愤者,皆先后归返祖国。”根据“联总”的规定,避难华侨属于难民范围,因此,在中国避难的华侨返回居留地须中国政府与“联总”协商才能成行。根据“联总”的战后遣返难民安排规定,在中国避难的华侨返回居留地的程序如下:所需交通运输工具如轮船的安排须按照“联总”的规定,中国政府将需要返回居留地的中国侨民送到规定的口岸如香港、广州、厦门等地,然后由“联总”与居留地国家商妥后由“联总”派船把人员送到原居留地。
南侨机工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而参加军事物质运输工作而来,而非难民。但根据“联总”的规定,“南侨机工遣送出国须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洽商方能解决”。由此可见,国际之间的人口流动,无论是战时来中国避难的华侨还是战时返国参加军事物资运输的南侨机工,南返时都须遵守这一规定。为办理和协助难民遣返,1945年初,中国政府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其具体职责是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商办理中国国内难民及战时归侨南返事宜。
其次,战后初期中国国内复杂多变的局势。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局势复杂多变。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而言,其不仅要承担着国内大批难民返乡和救助工作,还要负责组织办理难侨返回居留地的工作。该机构起初将重点集中在遣返难侨回原居留地,而没有把南侨机工复员作为专案问题处理。另一方面,解决南侨机工的复员南返问题需要多个部门如侨务委员会、外交部、交通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协调,此外,因战争破坏的国内交通亦亟待恢复,因此,交通不畅也是制约南侨机工复员南返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战后南洋各地限制入境的政策。战后,英国、法国等国家重新返回东南亚,企图重建战前殖民体系。因此,各政权对移民入境加以限制。但各地政权的移民政策亦有所不同,“对于侨胞复员事宜,有规定返境条件的,有规定返境手续的,有规定返境之生活问题的,甚至有藉词排斥,故意作难的”。而作为南侨机工主要来源地英属马来亚,其入境政策最为严格且极具变化。首先是入境手续复杂。申请返回马来亚的难侨“限时必须经由当地中国领事代表转送英国领事馆和新加坡民政署核办”。其次是英属马来亚不仅限制南侨机工的入境名额,而且南侨机工还须提供居留证明、居住经历,居住时间等证明,因此,上述问题的处理皆需要中国外交及领事部门与英属马来亚政府协商和交涉才能完成。
二、南侨机工复员南返方案的制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没有对南侨机工复员南返做出安排,南侨机工亦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复员请求,而是时隔十个月后,在南侨机工和南洋华侨社会各方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最终于1946年6月18日制定南侨机工复员方案。
(一)南侨机工复员申请的提出与第一次机工复员会议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4月13日,负责侨务的主管机关侨务委员会召开南洋华侨遣返会议,其内容主要是针对缅甸华侨及因战争来祖国避难的华侨的南返问题。
1945年10月3日,“云南省华侨互助理事会”在昆明召开南侨机工返国纪念大会,约500华侨机工参加,在纪念大会上,“云南华侨互助会”制定并通过《马来亚应募返国服务侨工复员办法建议书》,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南侨机工复员的请求。其复员南返的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华侨机工完成了历史使命,理应与家人团聚,且抗战结束,“万民均已着手复员,而侨工代表海外数千万侨胞返国,尤当使其复员,重返平时生活,自当重返南岛,复命慰励海外父老兄弟姐妹”;其次是华侨机工返回南洋重整就业。因“侨工中半数有财产,家属远在南洋,七年阔别或有巨变,亟须重整重建,于情于理,政府亦须送其即返南洋,各安本业”。再次是南侨机工失业较多,生活困难,例如“战后美军纷纷东调,服务于美军机工三百余人留滇人员相继失业”。南侨机工失业者700余人。在《马来亚应募返国服务侨工复员办法建议书》中,“华侨互助会”就复员登记、政府对服务机工的奖励以及政府外交交涉等事宜向国民政府提出详细的建议。
《马来亚应募返国服务侨工复员办法建议书》以两种途径送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一是委托“云南省华侨互助理事会”呈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二是“南侨机工大会”推举代表李卫民赴重庆呈交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除此以外,时任驻中国滇缅公路代表南洋侨领庄明理也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机工复员的八项请求。
对于南侨机工的复员南返的请求,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时做出响应。1945年11月7日下午三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委托“侨务委员会”在重庆(林森路)召开第一次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会议。参加会议的部门及人员有侨务委员会(甘云)、交通部(杜湘)、运输管理局(臧其吉)、外交部(叶洪泽)、侨务委员会(王开尘)、善后救济总署(欧阳治)、“南洋总会”滇缅公路代表庄明理先生。经过协商,会议通过以下决议,首先是救助失业侨工,由“后方勤务司令部及战时运输管理局尽量优先录用”,对于失业者由“行政院拨专款救济”;其次,决定外交部和“善后救济总署”分别办理交涉入境和遣送等。
但该会议主要是针对南侨机工的救济问题,而对机工的荣誉和奖金没有涉及,也没有一个总的协调机构办理机工复员问题。一个多月后,即1946年初,“侨务委员会”将第一次南侨机工会议内容呈送给国民政府行政院,但对于机工奖金数额存在分歧,行政院一直没有告知“侨务委员会”,机工复员南返问题被搁置,一直到1946年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再次委托“侨务委员会”主持召开第二次机工复员会议。
(二)中国和南洋各方呼吁及机工复员南返办法的制定
1.中国南侨机工和南洋华社的呼吁及行动
1946年6月18日,“侨务委员会”组织召开第二次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会议。该会议是在南侨机工、南洋社团、陈嘉庚以及中国国内公众舆论的呼吁和努力下召开的。
首先是南侨机工复员南返的强烈要求。根据第一次机工复员会议的安排,“华侨互助会”负责机工复员登记工作,并于1946年3月将复员机工名单呈交给行政院,但一直未获答复。为促使国民政府早日批准机工南返,1946年3月2日,“华侨互助理事会”派常务理事白清泉、总干事邱新民携带《机工登记名册》亲自赴重庆请愿。他们先后到行政院、救济总署、外交部等部门,但“都是个别的承诺,而没有总的协调和批示”。于是,1946年3月13日,二人决定向五届二中全会诸中委请愿。最终,国民政府行政院承诺,决定对南侨机工复员南返专案办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亦同意优先将南侨机工送返南洋。另一方面,督促外交部门入境交涉。鉴于“各地义民归侨且早已遣送还乡,而独机工等尚流离失所,无所依靠的”,1946年5月5日,在昆明南侨机工召开“南侨机工返国七周年纪念大会”。参会的全体南侨机工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名义致电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讯向英方交涉请准予入口,俾侨工等能早日返回侨居地回复旧业,重见父母兄弟”。
二是各地南洋筹赈分会和南洋侨领的呼吁和请求。抗战胜利后,南侨机工在中国失业的情况传入南洋后,引起南洋华侨社会的极大关注。曾经资送机工回国的各地筹赈分会,纷纷致函国民政府驻星领事馆,1946年4月26日,柔佛、新山筹赈分会致函新加坡总领事馆,请求其“电大部(中国外交部)向有关机关调查,设法遣送流落之华侨机工得早日返马。”1946年6月8日,南洋侨领刘伯群、许生理二人请求驻新加坡侨总领馆代电,分别致电外交部、行政院宋院长、海外部、侨务委员会、交通部、救济总署等机关,请求将“滞渝、昆机工乞速设法提前资送南洋”。对于社团的请求,驻星领馆迅速反应,1946年6月4日和5日,两次发电告知中国外交部,称“该批机工为国辛劳,壮志甚嘉,…此间侨胞至为关怀,拟请设法遣返南洋。”
三是陈嘉庚的呼吁和行动促使驻星领事馆和中国国民政府积极行动。在南洋侨领屡经交涉请求未果的情形下,陈嘉庚作为机工动员和招募的组织者,开始为机工南返呼吁、并在南洋采取行动推动了中国国民政府解决机工南返事宜。
需要指出的是,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已不如战前融洽和密切。陈嘉庚组织南洋慰劳团返回南洋后,陈嘉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日渐疏远,1940年6月,护送“南洋慰劳团”受伤成员蒋才品的西南运输处人员抵达新加坡后,在给国民政府的密电中,称“陈嘉庚似已左倾”。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也深知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疏远,“本总会曾发电向最高机构,如蒋委员长、军事委员会,或行政院,要求机工复员。然自民二十九年冬,余报告陈仪祸闽之后,中央政府即于本总会断绝消息,虽曾汇款数千万元,及发去函达不下数十次,一字绝不回复,迨日寇失败后,余回星再试亦然,固知虽由本总会要求,亦无效也。”尽管如此,陈嘉庚一直关注南侨机工复员问题的进展,认为国民政府会顺利解决该问题,1946年6月,陈嘉庚决定采取行动督促国民政府迅速解决机工南返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复杂的局势对机工南返愈加不利。1935年3月15日,庄明理返回新加坡。告知其为机工南返问题交涉的无助,并称国民政府办公机构大都移回首都南京,“迨至前月(1946年5月)政府已全往南京,潘君亦往上海,白仰峰等已南返,黄树芬、柯报仁及其他,与马来亚筹赈会有关系等人,或先后来洋,或他往,可以说政府及华侨要人,在重庆已空无一人矣”。另一方面,南侨机工请求陈嘉庚协助南返,1946年5月6日,在重庆的19名南侨机工联名致函陈嘉庚,告知其在中国的“生活穷苦,莫不思归心切,虽经数度向当局请求,每次均答以侯拟,力予拖延。数月已逝仍无消息,似此恐无返归之一日”,请求陈嘉庚设法助机工复员南返,与家人团聚。
鉴于“国民政府对于机工遣返,或敷衍延搁,或藉词推诿,空雷无雨”,陈嘉庚认为机工南返之事不能拖延,在此情况下,陈嘉庚决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召开会议,联合马来亚各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946年6月1日,陈嘉庚在《南洋商报》等华文报纸上刊登《南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通告(第十九号)》。《通告》呼吁马来亚各地筹赈分会筹款协助机工南返,“至诸机工原为爱国而特往服务,亦有各地筹赈鼓励而成行,今日战事已终,目的已达,其父母妻子忍苦盼待,七年于兹。政府即不资助南返,我侨安能坐视?”并决定于1946年6月16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协商解决机工复员南返问题。
1946年6月16日,来自槟城、太平、峇株巴辖、巴双、彭亨、新加坡六地的代表在吉隆坡召开会议。各地代表认为遣返机工是国民政府应尽的义务,无须为南侨机工复员筹款,大会制定出督促中国政府遣送机工的办法。首先是推选产生由五人组成的南侨机工救助小组,包括新加坡的陈嘉庚、槟城的庄明理、巴双的陈可用、彭亨的何志峰、峇珠巴辖的蔡伯祥;其次,决定1946年6月18日五人集体拜见驻星总领领事伍伯胜,讨论救援机工办法;再次,以马来亚华侨筹赈联合会名义,致电行政院,要求“资助华侨机工复员”。最后,要求驻星总领馆告知中国政府,机工成立家庭者“则其妻及子女均加以资送”。
1946年6月19日,陈嘉庚为机工南返事宜,亲自与四位选出侨领代表到驻星总领馆并拜见伍伯胜,此为“陈嘉庚十余年来第一次亲来本馆”。五位代表当面提交1946年6月16日吉隆坡会议决议案,并要求总领馆“若逗留国内之机工,不能于二个月资送南归,”根据大会授权,请求“总领事本人经往南京一行,亲为侨民请命”。
为确保和督促机工复员能够顺利南返,1949年6月18日,陈嘉庚以“马来亚华侨筹赈援助华侨机工复员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要求“政府应给资助救济及南回,本会同此请命,除商星总领馆代恳外,谨电奉闻”。
陈嘉庚亲自到驻星领馆交涉及二个月期限必须送回机工的要求,驻星领馆伍伯胜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先后多次致电中国外交部,请求迅速制定机工南返方案。伍伯胜认为,陈嘉庚虽然“借此口实攻击中央,但无论如何,遣返机工南返,中央事在必办。”而中国外交部帮办也认为黄光华称,南侨机工遣返“如不获适当解决,南洋各地侨情汹涌,总领事馆难以应付,可能引起不良后果”。
除了来自中国国内机工的南返要求和南洋社会各界的压力外,国民政府内部也提出必须办理南侨机工的复员南返问题。侨务委员会认为“机工在抗战时期,相忍为国,今胜利复员,一般侨胞多已返回居留地,而此批机工则流落内地,贫病困苦,失业受屈,不一而足”。如不妥善资送,“实无以对海外侨胞”。海外部官员亦认为,“南洋侨团开始攻击甚烈”,为降低国民政府在南洋的负面影响,“保持政府威信,平抑众愤”,“确无再推延遣送责任之理,目前奸党在海外对此事又乘机煽惑。如果不办理机工南返,“将来政府无法在南洋推行政令亦!”
2.第二次复员会议和复员办法的制定
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1946年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侨务委员会会议厅召开第二次机工复员会议。参加者有行政院、海外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侨务委员会、外交部等六个相关部门。会议通过《南洋华侨机工资送返原居留地办法》。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由行政院“指拨专款援照归国华侨复员辅助之规定,从优辅助旅及服装费”;二是要求“侨务委员会先发给证明书”,并与外交部免费为华侨机工办理护照;三是规定具体的遣送办法。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将华侨机工送至出海口岸(广州、汕头、厦门集中),再由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负责商情联合国救济总署接送至原居留地。
1946年6月21日,“侨务委员会”将机工复员会议决议呈报给国民政府行政院。由于分工仍不明确,1946年7月3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再次召开会议,协商办理机工南返分工安排,参加会议部门有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等部门。会上通过决议,规定了机工南返的具体办法及各部门的具体职责。规定侨务委员会负责办理登记及证明事项,外交部办理护照及对外交涉,行总、联总分别根据双方规定办理遣送事宜;关于南侨机工之遣送,侨务委员会办理调查及登记手续后,其全部名册须经由行总转送外交部核发护照并交涉准许入口事宜,然后方由行总、联总分别办理遣送,并以广州为集中地点。最终在各方努力下,南侨机工复员南返办法正式出台。
三、机工南返之前各方的工作和努力
南侨机工复员办法虽已制定,但机工南返之前还需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除了相关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之外,还包括机工复员及家属名单登记、入境交涉、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商等具体事宜。
(一)华侨互助会:复员机工的登记、奖金及荣誉证书的发放
1.华侨机工的复员登记
机工复员南返一方面“必须知道有多少人要回去,有多少人证件遗失了,多少人有妻子儿女”,另一方面,机工登记工作也为办理入境交涉、奖金、荣誉证书提供确定人数。因此,在南返之前,必须做好机工登记工作。根据机工复员南返办法安排,侨务委员会负责机工复员登记工作,侨务委员会将机工登记工作委托“华侨互助会”办理。
早在1946年1月15日,“华侨互助会”理事长胡春玉就开始安排人员进行机工复员登记。主要是在南侨机工分布较多的昆明、贵阳(毕节)、重庆三地设立登记站,“华侨互助会”派人专门负责办理登记工作,贵阳由陈金有负责登记,川滇(毕节)线由刘敏修组织,在重庆由陈烈辉负责登记工作,此外,“华侨互助会”在主要交通线设有联络员。康文风负责昆遮线,机工林朝云负责昆沪线,机工陈忠烈负责重庆(川滇线),主要是代各地机工办理登记手续。
需要指出是的,为确保服务在岗的机工及偏远地区机工都能够参加复员登记,陈嘉庚要求国民政府,“在昆明、重庆、贵阳、桂林或柳州,设立机工接济所,登记收容各机工”,还要求“政府通令由各机工传知外,并在各省登报或交通路站张贴告白,限期一个月内报名集中,并通令各车站免费运送”。
根据陈嘉庚的要求,侨务委员会在南侨机工主要集中地云南省采取以下措施:为避免机工遗漏登记,首先在昆明各报刊登机工登记启示;其次在沿滇缅公路重要城镇设立通讯站,派专人登记,在滇缅公路沿线,皆有由机工组成的工作人员为机工登记服务,其中,在楚雄由钟五峰负责登记,在下关由韩高元负责登记,在永平由郑佐国负责登记,保山由许麟负责,芒市由叶仕球负责,遮放由宋杨才负责登记。
机工登记工作原计划一个月结束,但实际上达十个月之久。首先是因为南侨机工分布在整个西南地区,有的机工在边缘山区且交通及信息不畅,“华侨互助会”需随时等待远道而来的机工登记。其次,在机工登记中,申请登记者情况多变,给登记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例如,有的因证件遗失而须重办证件,有的初不登记后又登记,有的因在中国建立家庭须为家属登记,在其登记时遗漏家眷需要重新登记等等。例如,机工郑亚妹,初来登记时一人登记,后来其妻子要求随同南返。又如机工郑光昌,因“该机工原在渝结婚数年”,本拟独身返侨居地,然后再来迎接其妻子,后因“该妻由渝来昆,拟随同南返”,登记人员不得不为其申请和重新登记。再如机工陈亚叶,在中国结婚建立家庭,初期独自登记,后因“该侨工眷属由家乡来昆”,登记人员只好为其重新办理登记等手续。此外,为确保南侨机工身份的真实性
“华侨互助会”共计登记三批复员机工,第一批登记共1203人,其中包括重庆地区190人,昆明区(包括昆遮、昆泸两区)772人,贵阳区192人。该批机工来自英属马来亚的有1061人,经审核符合机工身份共1154人。第二批登记机工251人,携带南返的机工妻子104人,机工子女86人,共449人。第三批登记机工中,除由云南华侨互助会登记的125名机工外,还有各省侨务局直接上报给侨务委员会的123人,经过登记工作人员审核,其中,广东侨务局登记9人,华侨青年服务社广州分社50人,海口侨务局登记36人,上海侨务局1人,南京27人。第四批侨务委员会218人,共计1748人。
2.代发放奖金和机工荣誉证书
除了办理机工登记之外,“华侨互助会”承担发放奖金和荣誉证书的工作。为表彰南侨机工对抗日运输的贡献,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向每位南返机工发放奖金200美元。1946年9月14日,“侨务委员会”发布回国服务华侨机工奖金公告。首先规定发放时间,1946年10月1日至11日在重庆和昆明发放,10月7日至17日在贵阳发放,其次,根据当时汇率折合国币67万元发放,最后,发放人数是第一批登记的机工,共计1154人。
根据侨务委员会的公告要求,1946年9月18日,云南侨务处致函“华侨互助会”委托其代发侨工奖金。首先告知《侨委会发放奖金办法》,其次是要求其“发放名单分寄各通信站或其他人士代为多处张贴,设法普遍通知各地侨工依期往原登记地区领取奖金”。最后,要求“发款时应有贵会逐日派员出席参加审查以使妥善”。
在发放奖金过程中,“华侨互助会”人员努力为机工服务,但有时还被云南侨务处误解。“华侨互助会”曾向云南侨务处申请放弃发放奖金的任务,后来,云南侨务处恳请其继续办理,“假令半途而废,致使上峰将来机工之德意及机工应享之利益均受损失,而贵会之义举亦将不能贯彻,咸感失望,尚希即日继续工作,有始有终,完成善业。”最后,华侨互助会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完成了该批机工奖金的发放工作。“华侨互助会”还负责代发荣誉证书的任务。为表彰南侨机工的贡献,国民政府的三个部门为南侨机工颁发证书,其中有侨务委员会、交通部、军事委员会运输管理局。机工荣誉证书均由“华侨互助会”代为发放,在发放证书中,少数已回南洋的机工须通过邮寄发放。需要强调的是,“华侨互助会”的工作人员本身也是南返的机工,但他们任劳任怨,顺利完成了机工复员前最为繁重且耗时的机工登记、奖金、证书发放等工作,其工作成绩也得到云南侨务委员会的认可和肯定,称华侨互助理事会“为侨胞服务,对政府效劳,予机工福利,义举侨众,中外同钦”。
(二)外交部:入境交涉及办理护照
首先是对南侨机工的入境交涉。与战前移民自由进入南洋各地不同,二战后,东南亚各政权对移民入境限制。荷属东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地入境相对宽松,而英国马来亚入境条件尤为苛刻且多变。因此,南侨机工入境须经中国外交部门交涉。
1945年9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就中国侨民返回英属马来亚向英国代表交涉,当时英国外交部口头承诺,交通恢复后,“凡有适当证明文件,或文件遗失,经本部查明属实,不附任何条件均可入境”,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告知“南侨机工服务团”,“英方对于华侨返回马来亚,现并无限制,惟申请入境者,须由当地中国领事馆代表转送新加坡民政署核准。”但由于机工正在登记、手续不能及时办理等原因,机工南返错失了入境良机。1946年6月18日,《南侨机工复员办法》制定后,中国外交部委托驻新加坡总领馆负责南侨机工的入境交涉,1946年7月2日,驻新加坡总领事馆伍伯胜致函新加坡移民署,请求允许南侨机工入境,但英属马来亚新加坡以局势困难为由,对入境华侨机工的出生地、出生时间以及居留证(Certificate of Admission)等实行限制。根据其入境条件,中国外交部将南侨机工第一期名单转交给新加坡移民厅审核。与此同时,1946年8月27日,驻新加坡总领馆伍伯胜抓住时机,与抵新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香港办事处主任Clarke1商谈,Clarke1同意优先输送南侨机工。
需要指出的是,陈嘉庚对驻新领馆的督促加快了南侨机工的入境交涉。1946年8月21日,是陈嘉庚要求中国政府两个月遣返机工的日期,陈嘉庚“未见有人遣送回来,迟未成形,殊属不解”,因此,陈嘉庚要求驻星领馆伍伯胜返回南京交涉。面对来自陈嘉庚的压力,中国外交部电新总领馆,要求加快进度督促英移民厅审核机工资格,经过中国驻新领馆的交涉,1946年9月20日,英属马来亚殖民当局“准许按照名单准许所有机工协同眷属进入马来亚”,该批机工共1335名。
1946年9月21日,中国外交部致电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和侨务委员会,要求迅速办理遣送南侨机工,“机工返马入口手续,此间均已商妥,乞催促行总将滞留渝、昆等地机工,先行遣送来星”。至此,从1946年6月18日制定复员办法后,历经两个半月时间的艰难交涉,在中国外交部和驻新领馆的努力下,南侨机工的入境问题得以解决。
其次是为办理护照。在中国服务期间,南侨机工的护照等相关证件大多已经遗失且均已过期,另一方面,南返机工的家属也需要办理护照,中国外交部对南侨机工及家属办理及签证实行优待政策。对于在出发前发给机工及家属临时护照,“护照费免收或酌收工本费,即由此机工集中地之昆明特派员公署核发”。在贵阳、重庆出发的机工及家属,外交部派两广特派员派人于当地办理;在签证方面,外交部命令云南及两广特派员至广州现场办理,在发给正式护照之时,“同时取得入境签证”。
(三)“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协调及安排
根据南侨机工复员办法,“行总”负责协调及将各地南侨机工运送至出海口广州。因此,善后救济总署及时与“联总”协调,首先将复员机工名册转交“联总”,并请求优先签署并准备出国船只。同时,将机工名册分发昆明、贵州、重庆输送站,要求各输送站优先将机工运输至广州。为做好衔接工作,在机工抵达广州之前,“行总”派专门人员赴香港办理和协助交接手续。
1946年9月27日,“行总”派两名外籍专家萧阑德(T.D.Sherrard)专员和李降宁前往香港,其职责是与“联总”香港办事处洽办机工南返事宜。在与广东分属及联总香港办事处协商后,“行总”提前告知外交部两广特派员,以便与其派遣人员联合办理南侨机工出国手续。
四、南侨机工的复员南返进程
(一)“欢送回国服务南侨机工复员大会”的召开
华侨机工复员南返之前,昆明、贵阳等地政府和民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大会。云南作为南侨机工主要工作和生活之地,云南省各界举办“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南返大会”。欢送大会由云南省社会处倡议,“南侨机工激于爱国义愤,相率归国参加抗战实际工作。热诚可嘉,八年苦战,西南各线运输工作,亦由侨工担负”,社会处为表示慰劳及欢送起见,发起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复员南返大会。1946年10月18日,云南省社会处致函各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并决定于1946年10月21日开会协商欢送机工事宜。1946年10月21日,来自云南省各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14个部门的代表参加了欢送南侨机工筹备会议,会议确定欢送大会时间为1946年10月25日下午三点,欢送地点在云南省党部大礼堂;欢送大会经费由社会各界捐赠。
1946年10月25日,云南省各界“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南返复员大会”在昆明西站举行。除南侨机工及家属外,还有政府机关代表、昆明中学师生代表以及昆明各社会团体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欢送大会。大会分别由中国国民党云南省支部主委杨家麟和“西南运输处”第四区公路局局长葛沣致辞,南返机工和云南省政府等互赠锦旗,最后,昆明市社团向南侨机工赠慰劳品和服务纪念章,并于下午以茶点招待南侨机工。
(二)南侨机工的南返进程
南侨机工南返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国民政府统一安排集体返回南洋居留地,另一种方式是独自返回南洋,例如,在印度服务的机工庄清海,是自费从印度加尔各答返回英属马来亚。1946年12月12日,华侨互助会总干事白清泉,从昆明乘飞机携带家眷抵达广州后,在广州滞留半月后,1946年12月27日,白清泉携带家眷经香港乘船返回新加坡。
大多数机工根据国民政府统一安排返回居留地。首先由国民政府统一安排车辆从昆明、贵阳、重庆等地抵达广州,其次机工在广州办理相关手续后,由专人安排进入香港,最后,救济总署与“联总”协调后,机工乘坐至新加坡的轮船。现就档案资料所见,论述从昆明启程的机工南返的进程。
据“华侨互助会”的登记,南洋各属机工及眷属计3042人,其中以英属马来亚人数最多,机工和眷属共2485人。因时局动荡及路途遥远,为确保机工顺利抵达广州,“行总”做出周密的安排。首先成立南返机工组织机构,由白清泉、林朝云为机工南返总顾问。各批返国分别成立组织机构。其次,为确保有序及路上安全,南返机工须持侨务委员会发给的乘车证明。在出发之前,各批领队持有侨务委员会发放的关卡证明,要求沿途“军、政、宪、警及各关卡,查验放行”,再次,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在机工出发前,1946年10月21日,外交部提前致电广东广西特派员公署,告知机工出发时间,并要求外交部人员,在为南侨机工及家眷办理出国手续时,“应尽量予以便利”,并要求其“与行总广东分属及联总香港办事处取得联系”。
根据复员登记的顺序,南返机工共分为三批出发。第一批:南侨机工和眷属共421人(机工219,眷属202人),以梁一轰为总领队,1946年10月26日由昆明西站出发赴广州;第二批:机工及眷属共156人(机工71,眷属85人),以王振美为总领队,1946年11月15日由昆明西站出发至广州;第三批:机工及眷属306人(机工177,眷属85人),以刘善哉为总领队,1946年11月29日从昆明西站至广州。昆明的机工抵达广州的交通方式是,先乘卡车至广西柳州,然后在柳州乘船,沿西江抵达广州。
由于国民政府的组织安排有序,由昆明出发的南侨机工顺利抵达广州,第一批于1946年10月28日抵达广州,第二批历时8天于1946年11月23日抵达广州,第三批于1946年12月13日抵达广州,共历时14天。
南侨机工及眷属抵达广州后,提前到达外交部的人员集中办理护照等入境证件,然后由“善后救济总署”安排机工抵达香港,机工及家眷乘坐准备好的到达新加坡的轮船。由于战事及环境复杂,香港有大批避难的归侨也亟待南返,因此,“善后救济总署”没能为华侨机工安排专门船只南返,而是与其他难侨同船返回新加坡。
复员南返的南侨机工的人数究竟是多少?限于资料的原因,我们仅能从驻新加坡领馆给中国外交部档案及南返机工的个人回忆,得知南侨机工抵达新加坡的部分情况。
1946年11月20日,驻星总领馆伍伯胜致电外交部,告知由香港至新加坡芝巴德轮于18日抵新加坡,船上有机工50人。1946年11月27日,驻星领馆再次致电外交部,抵新加坡的“芝巴德”轮上机工27名,连眷属共51名。1946年11月28日,420名华侨机工抵达新加坡。据南返新加坡的华侨机工陈瑞昆回忆,1947年12月3日,其所乘轮船中,南返机工179人,家眷104人,儿童97人。据其回忆可以看出,机工抵达广州后,有的机工“自行他往”,而没有返回新加坡。因此,南侨机工返回南洋的具体人数难以确定。
1947年7月8日,“联总”宣告结束,遣送国际难民的工作由“国际难民总署”负责办理,中国对应协调机关是云南省社会处,因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云南省社会处规定,“如行总、联总介绍,赶办不及,则应为自费出国”。
因南侨机工返回中国参加抗日运输工作,在日本占领南洋期间,机工家属及亲人受到牵连,有的被日军杀害。另一方面,因战后新马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南返后的机工生活极为艰难,新马华侨社团发动华侨社会各界救济生活困难的机工,例如,“南侨总会”要求各地社团为南返机工提供救助,槟城华侨社团主动成立“援助复员机工小组委员会”,主要负责安抚南侨机工事宜,因槟城机工“多为槟城华侨司机公会”会员,因此,机工抵达槟城后,“膳宿等项由司机公会负责”,槟城筹赈分会则“给予相应生活补助金,单身者60元,有家眷者100元。统计约100人,共花费约万余元”。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对南侨机工复员南返的考察,可以看出,战后的机工复员南返具有以下特点:
(一)华侨机工复员南返受制于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制约。与战前南洋与中国之间移民相对自由往来不同,战后,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第一,机工南返深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安排和制约,第二,南侨机工原居留地的入境限制需要漫长的交涉和协调。此外,战后的国共内战的环境也使得国民政府在战后没有及时将机工复员纳入专案办理。
(二)南侨机工南返手续繁多,耗时较长。南侨机工复员南返手续具体包括:华侨居留证、护照,身份证明、入境申请等事宜,另一方面,南侨机工荣誉证书及奖金的发放耗时较长,此外,随同华侨机工一同南返的家属及子女也需要办理以上手续。
(三)机工南返需要多部门的协调配合才能得到解决。包括侨务委员会、外交部、驻新总领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等多方协调配合才能成行。1946年10月至1947年间,国民政府陆续组织南侨机工复员南返,其中国民政府、华侨互助会、南洋华侨社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国民政府各机关的协调配合行动是机工顺利南返的主要执行者。华侨机工复员办法确定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先委托侨务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对机工复员做了具体的安排。其中,中国外交部的入境交涉成功是机工复员南返的关键。中国外交部不仅为南侨机工办理护照等事宜,而且还负责南侨机工及家属南返的入境交涉事宜,特别是驻新领馆抓住时机,多次与英属马来亚政府交涉入境问题,因此,入境交涉的成功是南侨机工顺利南返的重要前提。而在中国国内,善后救济总署积极与“联总”沟通协调,及时将南侨机工运至广州。因此,国民政府各机关的协调配合行动是机工顺利南返的重要保障。
2.“云南华侨互助理事会”人员的努力和付出。在机工复员之前,国民政府须为机工办理机工登记、发放证书及奖金的任务,华侨机工互助会主动承担了本应由国民政府承担的工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华侨互助会是由南侨机工组成的社团,该会经费全由该会自筹,在后期,互助会运作不堪重负,其运作所需经费皆由机工自己负担,而且互助会工作人员本身也属复员南返的机工,但是他们义务为南侨机工服务,忘我工作,顺利完成了机工登记工作,保证了外交部能够及时将复员名单送交新加坡移民署审核。
3.南洋华侨社会的督促和推动。抗战胜利后,南侨复员事宜引起南洋华侨社会的关注,机工顺利复员离不开华侨社团及华社侨领的推动。例如,在“南侨总会”的组织下,陈嘉庚组织专门人员呼吁和督促国民政府办理机工复员。不仅如此,南侨机工抵达新加坡后,“南侨总会”动员各地社团救助南侨机工,为南侨机工提供了急需的经济援助。
总之,在中国内战爆发及南洋各地政局动荡的环境下,经过国民政府各部门、云南省华侨互助会以及南洋华侨社会共同努力下,国民政府顺利将登记的南侨机工遣送至南洋居留地。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
D634.3
A
1000-5072(2015)02-0038-12
2014-09-22
夏玉清(1970—),男,山东兖州人,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南洋华侨机工研究(1939-1946年)》(批准号:2014YNSD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