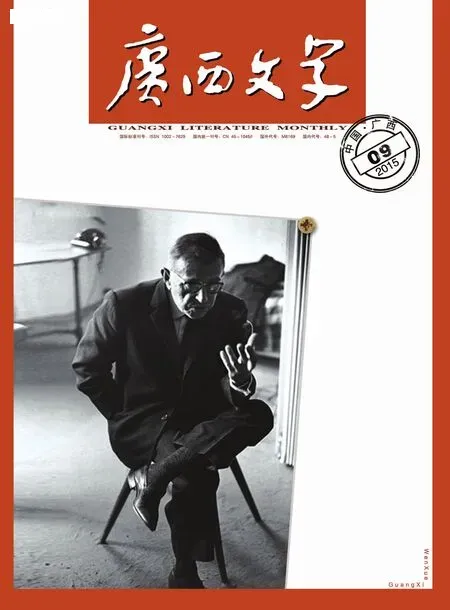天堂图书馆
2015-11-14刘景婧
刘景婧/著
是的,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天堂也许只属于活着的文字,死去的人。时间在这里是可操控的。它既缓慢,又迅速。如同一只身材臃肿步履蹒跚的巨兽,在永无尽头的茫茫公路上缓缓而来,却又在恍惚之间飞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路的两端,它是自由的,永远在重复,永远在生活,永远在等待着,你踏进空间的那一步。
2007,夏,女巫,女巫
我离那条河已经很远了。
那一年,我才二十岁。二十岁的青春漂浮在大河之上,在凌晨三点的静寂中看见十五岁的杜拉斯:头戴一顶玫瑰木色的平檐男帽,穿一件茶褐色的低领真丝连衣裙,一双镶金条带的高跟鞋不合时宜地把少女纤细的脚踝紧紧套住;她站在1929年的轮渡上,表情高傲冷酷,眼睛却似笑非笑,如女巫般静静望着汹涌的湄公河一泻如注地奔流入海。这个女巫的形象,一直到杜拉斯七十岁的时候,还清晰地展现在她面前,告诉她在那一年,她一生中所有的悲剧即将迎来一个集聚点,而这个集聚点,正是由一个中国男人牵引而来。我看见十五岁的杜拉斯和七十岁的杜拉斯以一体两面的形象互相注视,年轻的美貌深藏阴影,被岁月损毁的面容背后却有着对时光的释然与安详。七年后的今天,我意识到《情人》只有七十岁的杜拉斯才能写出,因为只有在七十岁过后,爱情才不是浮泛在生命之河上的小浪花,而成了沉在河底的石头。对杜拉斯来说,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像讨论死亡一样讨论她少女时代的爱情。
这本布满灰尘的小书,里面满是枯冷、受虐和死亡。人物缥缈,只剩形象,大海深广无边,纠缠着黑暗与尖啸。在人生最空茫的时间,爱不是珍重,而是绝望,我不知道这样的青春是开端还是结束。只有痛苦是饱含激情的。这个世上存在真实的黑暗。“恶”的历史绵延深远,母慈子孝、爱人相守,美好在现实中往往只是假设。恶是一个深渊,流着肮脏、贫穷、冷漠的口涎,把所有碰到它的人都往嘴里扯。乔治·巴塔耶曾写过一本《文学与恶》,用文学的反叛精神探索着一切人性的禁区,同是法国人的他对杜拉斯的作品似乎有一种先天的预见。关于爱情的罪恶、家庭的罪恶,巴塔耶说:“童年王国的道路上充满着天真与纯洁。这在赎罪的恐怖中又重新出现。纯真的爱情在真实的内心里可以找到。而纯真的爱情就是死亡。死亡和瞬间的狂醉一样,都反对以理性为基础的善的意向,但在反对善的时候,死亡和瞬间已成为最后的结局。死亡又是瞬间狂热的标志……生殖和死亡左右着生命的不断更新。因此,对愉快的生命我们不能只有一种悲剧性的看法。悲剧也是愉快的前兆。”同样的,杜拉斯也在小说中写道:“我在堤岸公寓里度过的时间使那个地方永远清晰可见,永远焕然一新。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我相信我隐约间已经感觉到对死的渴望。……自从我离开童年期,离开我那个可怕的家族,我看到我不再是孤独一个人。我要写几本书。这就是我在现时之外,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里看到的,而我的生命正是在大沙漠的特征下在我的面前展现出来。”
这种在罪恶与生命间纠缠的复杂关系,这种在爱情和亲情里类似战争硝烟般的真实,如果没有王道乾的译文,杜拉斯的黑暗恐怕不是轻易被中国的读者所接受的。虽然王道乾在《翻译后记》中提醒读者们要警惕小说中“极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但很明显,他是深爱这痛苦的。事隔多年,王译中那些绵延、轻灵的短句,那股冷峻内敛却又饱含激情的潜流,仍然可以把我轻易地拉入1929年的时光,让我想象杜拉斯女巫般的呓语中肯定有着某种令人着迷的神秘。
今夜我又想起了杜拉斯。雨落在河里,瞬间不见。多年后我却看见痛苦如莹白的沙粒,纷纷扬扬地在另一片幽蓝的海水中落下。海潮在海的内部穿扬而过,划开一道长长的银光,沙粒就在这银光中翻飞,如同阳光中飞舞的微尘。海潮过后,银泽下坠,慢慢洒到我长长的眼睫上,犹如那翩翩而下的冬霜的细末。
2009,秋,暴风雨的海中涌出巨兽
那是一个深秋的雨天。板棍街如一个剖开的老葫芦,被一条墨绿的粗线沿中间划开,粗线在瓢泼大雨中渐渐扩张,终于涨成一条半新的水泥路。隐隐地,有鞭炮声、唢呐声和唱歌般的哭声从远处飘来,时断时续,仿佛被雨淋湿了,声音都憋屈在水里。过了一会儿,一条长长的白蛇在路的尽头慢慢显现,缓缓地在同样悠长的老街上蠕动;两旁破败空寂的青砖老屋,古旧木门上横眉倒竖的门神,配合着送葬炮烛的刺鼻气味,在雨水的浸润中现出死寂和狰狞。这就是我的故乡,我活了二十二年却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故乡。2009年,我背着海子的诗集,第一次双脚踏在乡村的土地上,就看到了死亡。
然而板棍的三年,却出乎意料的平静。在平常的日子,板棍如同一座荒废的古堡,安静得可以听见飞鸟的声音。最热闹的时候要算清晨或傍晚。许多孩子沿着长长的老街嬉笑打闹,老人们则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前,默默地吸着旱烟,或絮絮地聊天。板棍的黄昏和水龙头里哗哗流出的浑浊江水一样,似乎从未清澈过,惨淡的落日黄,让一切人事——眼前的古旧街道和老屋,远方的山黛和水田,都染上了浓稠的晕黄。这晕黄层层渗入板棍的每个角落,甚至人们眼角眉梢的阴影,都被一种莫名的悲壮覆盖。但悲壮也会转瞬即逝。昏黄的天在刹那间变作暗红,紧接着,冷风就一阵紧过一阵地横扫而来。
我是2012年5月27日得知外婆的死讯的。
那天,我搭上一辆泥迹斑斑的中巴,前往距离板棍四公里以外的北江,参加外婆的葬礼。我第一次发现死亡是一件平静的事情。我的外婆静静地躺在三舅家的堂屋中央,身上盖着白色麻布棉被,被浓烈的香烛气味环绕,如同一段无知无觉的木头。外公静静地坐在屋外一张宽大的木椅上,一边吸烟,一边远远望着道公的唱念做打。一年之后,外公也躺到了外婆躺着的那个地方,只是那张宽大的木椅上,再也没有一位神情平静的老人,默默地吸烟,远望这个繁杂的世间。送葬之前,亲人们按照家乡的习俗,穿上白衣白帽,排着长蛇般的队伍,在道公的指引下前往村边的明江打了一桶水。当时,正是傍晚时分。落日掉入浑浊的江水,也落入深深的木桶,黄昏在桶里摇啊摇,把人的眼睛都摇花了。一旁的村童旁若无人地围观着,用客家话大声地嬉笑打闹,乡音如鞋,清晰地印在故乡的天空。这时候,黑夜正缓慢地从大地深处走来。
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手握钢笔,指尖冰凉,书写着死亡。小屋的书桌上躺着海子的诗集。一串串语言在乡村之夜集体游荡,幻象如马,自由奔腾于广袤的天空和大地。故乡不再是遥远的想象,我看见深夜的黑风狂啸肆虐,明江的河水浑浊沉重,自然界中所有幽微的生命,都以永不复现的姿态汹涌、自灭,唯独留下人类可鄙的贪婪与愚蠢,在曾经充满灵气的大地上密密攀爬,再以“文明”为诱饵,催促人们互相厮咬、吞噬,直至死亡。然而生与死的秘密都埋在河流两岸的甘蔗林中。海子的“实体”和“元素”如天体在星空中疯狂旋转,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老病死,生生不息,大地和天空的原始能量在亘古的绝望中铸就了乡村的底色。
西方精神的本质力量在于对世界和自身黑暗百无禁忌的探索。海子的诗歌如遥远山洞里的水,一点一滴,从深渊而来,纯黑艳丽,流经无数人的心脏,最后汇成血色的河流。他用自己的生命与天才,把中国当代诗歌熔铸成了一只只灼烧着人类心灵的、诡异却庄严的乡村之眼,以天空和大地中所有实体的形象,对人类精神的深渊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探索,揭开了东方文化一直规避着的黑色禁忌:精神力的突进和死亡内核之间,有一条曲折蜿蜒的路径。精神写作到了某个程度,会突然跌入幻象阶段。原始力量此时会以可怕的面貌出现在写作生活中。但是,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它危险,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当精神力企图用密集的想象来构建宏大的幻象帝国时,幻象就开始不断旋转生长,原始力量催逼着它,意念在脑中形成,写作者唯有不停地以各种方式描绘它,耗尽精神和体力,不到完成它的那一天无法停歇。这是一种极端的“赌徒式”写作。世俗生活此时完全被精神写作所压抑,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呈现疯狂状态的写作者。结局是辉煌而凄凉的。当作品完成,幻象成形,精神主体的耗尽和高度旋转的状态却已无法改变。没有了生机勃勃的精神主体,原始力量就会引出“死亡乱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这“死亡乱象”会取代“诗歌幻象”不断旋转生长,最后,必将引爆自身。
《太阳·七部书》是以爆炸开始的长诗。海子用诗剧里的角色分担了原始力量带来的压迫。大地如母,带来承担;天空如父,带来飞翔;人类如战士,终于觉悟而反抗。而刑天是反抗的极致。在各方力量的拉扯中海子用太阳王做最后的冲击。然而这最后的冲击似乎没有成功。1988年至1989年的冬春之交,也就是海子从西藏回来之后,他诗句中那股强劲的生命力与拆天拆地的霸气忽然间丧失了。丧失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就只是不屈的带血的挣扎。这挣扎绝望而苦痛,海子在夜以继日的幻象吞噬中深陷恐惧。在此,我有必要提及海子在1989年1月17日写的《叙事诗》。在这首诗里,“死亡幻象”已经成长为一个完整的梦境,它对内心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一次次的铤而走险,一次次的挣扎横渡,一次次的跋山涉水。动荡与休憩,爱恨与挣扎,都只有自己知道。此时,海子已没有了“太阳王”炸裂般的生命力,他只能用残存的力气肉搏黑暗。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认为海子的死是彻底的失败,我自己却有一种奇怪的感应:对海子来说,1989年3月26日的黄昏之死是他“蓄谋”已久的事件,他的死恰恰表明,死是有尊严的,如果写作的生命已经耗尽,如果世俗对他已毫无意义,那么,他还不如用无所畏惧的死去战胜原始力量的恐惧。
在海子的苦难面前我羞愧难当。
我们的时代,大多数的文字都在忙着怀念或感伤,用的还是“历史”的名义。缺乏新鲜涌动的血液,缺乏直面大地的勇气和信力,缺乏开拓前行的果敢与专一。而海子总是用切实的行动和锐利的眼神引领我看见时间里真实的挣扎——那是一个广阔、曲折、与众不同的世界,生命需要在剧烈的疼痛中感受存在,在切割中感受最深处的激情与韵律,在挖掘中体味最黑暗的隐秘。人类精神走过了那么久远的路途,深渊是真实存在的。幻象写作正是在原始力量的深渊旁游走的过程。当原始力量如海啸般席卷而来,深渊和死亡一样,无法回避,它们是高贵的,值得我们拿出真正的勇气和行动直面恐惧。
海子,南方没有蓝色的雪,只有黑色的暴雨倾盆而下。在雨中我又想起了你,想起我善良的外公外婆静静地安眠在故乡的甘蔗地。也许这就是命运。可以平安老死,也可以壮烈逝去。这些在寂静中燃烧的诗句,常让我误以为是生时已死的你给人间捎来的信。大地如母,用温暖的雨水滋养万物,却被长年的阴冷与黑暗血洗内心。海子,海子,我在三年的岁月里经历三重死亡,而你是第三重。如果黄昏的尽头是黑夜,那就让暴风雨的海中再次涌起巨兽,让向死而生的乡村大地,元素再生,循环不息!
2012,冬,夜雨开始下来
我又梦见2009年的黄昏。
惊醒的时候,夜雨开始下来,在冬日十一点的寂静中。我们离2009年的板棍已经很远了。那座小小的房子,一棵年纪很大的苦楝树紧挨着我们的大窗户,瘦瘦的枝干上经常停着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在白天忽然像几张大树叶似的飘下来,在夜里又会发出打嗝似的怪音。故乡令人寂寞。在故乡老死的卡夫卡,同样睁着一双犹太人的大眼睛,寂寞地看着我的生活。
“我觉得有必要写一些文字,在这卑微的时间缝隙中,在这热熏而动荡的人生竞赛中。生命总用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来绊倒你,并习以为常。生之苦役早已如西西弗斯滚动的石头而绵延不止。文字被碾得粉碎,碾出血。现在,我们必须靠鲁迅而活着,像一群没有脊梁的血吸虫,疲惫时吸他提神,困顿时吸他活命。我们弱不禁风的灵魂啊,可笑之至的灵魂!当你摆脱了乡间的懦弱与懒散,当你跻身小城的密集与刚硬,当你自以为意气风发,当你自以为无处不在。在人生的两个极端中,时间的虚无其实无处不在。”(2012年9月11日)
“我的内在生命依旧暗浊而沉坠。现实的忧虑化作梦境中重病的母亲、童年时的坟地、久不相见却一脸怪异的朋友……身心疲惫。被过度劳累和过度懒散同时挤压着的大脑和身体开始出现极端反应。我久不写作。借口都是在为生计奔忙。——实际上只是为世俗所控,宛如生之奴隶。”(2012年11月4日)
“昨夜九点多钟,高三有一男生跳楼身亡。只留下三封遗书和一张字条——‘没有人和我做朋友,没有人理我。’今天,高三集体沉重,高一高二却热闹如昔,甚至把死亡当好奇。太阳照常升起。这世间的繁荣昌盛,和个人内心的尖锐荒凉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我总在想,一个自杀的人的心会长成什么样。是不是布满了蓊蓊郁郁的茧子,有翅的茧,坚硬的、柔软的、动物般的茧,从心的根部缭绕而出,紧抠住心脏,往每一根毛细血管深处蔓延伸展,继续延展出无数的、带翅的茧,堵住了生命的每一个出口?用这样的心来面对这个冷酷的世间,会不会愈加畸形变态?”(2013年5月23日)
我们都是以这样一副面貌踏入生活的。
生活庸常的惯性缓慢,坚定,有力,如一头巨兽,细细啃噬你的骨头,当你注视它时,它会缓缓抬头,让你一下子看到它慈善的脸,和苍白空洞的眼睛。卡夫卡妄想逃离生活。他形容消瘦,双眼突出,以绝望的姿态活在这个凡俗庸常的世界。世界视他如怪物,他也视自己如怪物。敏锐的洞察力让卡夫卡举步维艰,似乎他无法掌握凡俗的、简单的思维,只关注人在极端困境中的各种动物般的反应。他在作品中不停地挖坑、洞和地道,只是为了让自己睡个安稳觉。这个世界林立着巨大的真相,恐惧是耸立在真相身后更为巨大的阴影。卡夫卡瞠目结舌地看着人流如蚁,在阴影中密密攀爬,穿梭不已,却从不在乎被命运的大手抠住喉管,一遍遍碾压。他隐隐感到,跨越尘世最简单直接的力量也许不是智慧,而是麻木与惯性。清醒是令人疼痛的罪,梦想是它最好的导火索,很多人终其一生不愿引爆,卡夫卡却用沉默的写作一遍又一遍地将它点燃,只是为了炸掉那些在内心深处疯狂舞动的恐惧,让良心清醒地在血泊中战栗,让文字成为纯粹的、踏实的绝望,以黑色的姿态在纸上张望。真相巨大黑暗,话语无法倾诉,只有写作。就这样,卡夫卡对自己的命运默默进行着一场安静的、不动声色的抵抗。这就是我最初看见的卡夫卡,零碎的、以偶然揭示一切的卡夫卡。
叶廷芳译文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如实译出了卡夫卡思想中的阻滞处——在文字流畅清晰的表象之上,笼罩着一片阴沉的、令人压抑的滞重体验。这种体验根源于卡夫卡毕生所追求的“理念写作”。支配性的、透视性的理念;写作只是表象,抽丝剥茧的思想才是重要的。作品是完全精神化的东西。所有人物、对话、动作和表情,都笼罩在密集而异于常人的思绪中,犹如沙漠旅者眼中清晰可辨的海市蜃楼,其实质却只是无法掌控却无所不在的光和热。这是一种艰难的、没有退路的尝试。成败无可预料,因为无人有勇气这样去写作,丧失所有读者、独语式的、挖掘式的写作。没有人能真正进入卡夫卡。他是一座孤岛,从来不指向拯救的真正路径。他只是列出可能性——生命在一切极端困境中的所有可能性。能稍微碰触到这些可能性并能融合自己的表达,就已是卓然的成功。但卡夫卡仍在那里,以天才和疯子的形象继续站在那里,把对人类精神的极致超越与追求站成一座孤岛,冷眼看着世间一切夸夸其谈的懦弱和虚妄。
雨声细密,扑打空气,如同飞蛾扇动翅膀的摩擦声。它们再次向我扑来,快速、庞大,粉碎的却又融成一片的坚冰。生活又一次以坚不可摧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仍在这个小城里生活的人们,安居乐业,并不感到毒素和绝望;我只是一个逃亡者,抓住一切机会迫不及待要逃离毒素的可怜人。只有卡夫卡知道,每个人都无法背井离乡,每个人都要背负着自己所有的过往,在这个“故乡”,生活下去。
2014,春,大风之夜
听奶奶说,七十年前,荷城曾经开满了遍地的荷花。
那时,月光和水光一样皎洁,粉白的荷花如云如雪,在月光中绵延,在水光中肆无忌惮地环绕天地。水中泛轻舟,曼歌采莲子,在田田荷叶的包围中,农家的女孩即使住着破院草屋,也有着和江南女子一样的美丽情怀。而明江沿岸一派山乡水色,村野风光,扛着锄头的农夫和骑着水牛的乡童,脚步一如既往地散漫自由。你可以驾一叶扁舟,看群山幽蓝厚重临江而立,猜测一下这由十万大山而来的峭拔之气到此究竟还剩多少;或者当船过河滩大弯,你看着两岸风貌陡然一黯——原来是前方一屏高大的山岩遮住了日光,会不会心中一惊?甚或当湿冷的山风穿山过隙,泠泠而来,如无形的巨手将人类推向远古,你是否会看见暗红色的花山壁画在幽暗的山影中逐渐放大、清晰,仿佛一个谜团的答案呼之欲出?
今夜,我坐在时间的深处,想起七十年前的荷城,仿佛想起那些落满尘埃的古书,疏落中总有些旷古韵味。蜿蜒吐纳于世俗时间里的深渊气息,是时间洞穴里的黑色隧道,神秘而缓慢地流过了几千年的日子。古中国的文字沉浸在神秘的历史呼吸中,一种深、静,控制了语言的流速,思想得以在其间驻足,生根发芽。这些深邃灵动、从生活和灵魂中洗沥而出的、黄金般的文字,深植在中国的泥土中,干净朴素,充溢着生命的热力,环绕起来,组成一个个寓言,如秋后的稻田那般丰饶。它们是最大的财富,是灵魂中的欢乐,是能够怀揣在心中、从容地踏过残酷的命运,平静地走到坟墓里去的文字。这样的文字,距今不过八十余年,仅够一个人的一生,却已和当今的文字两样了。当今文字多流于浮夸,语流迅疾而无根底,实在不如古时的文字,留得住时间。古中国的韵味到如今也两样了。大概只能往深山里寻,那里总有一屏太古的寂静绕山而生,其间水汽纵横,莽莽苍苍,高远的天际被大山顶住,天空硬生生被山尖划割为几大块。从这样浑然一体的荒古中流出的文字,正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底气与自由。而这父亲般的坚实底气,是西方文学不能给我的。
西方文学里有残忍而真实的尘世,从不被高蹈出世的思想所引诱。它用大海的呼吸冲刷陈迹,让灵魂真实鲜活地在刀尖上舞动;它喜欢把整个外部世界直接拉入内心,甚至不惜将其捣碎、重组,让它带着内心的海水湿淋淋地呈现,以便让世界与内心相应。我曾经在凌晨三四点的酒鬼笑骂中,在白天忽远忽近的声浪中,看着圣·奥古斯丁的白胡子在菜市场的各种腥垢之气中忽隐忽现。时间似乎是没有维度的,甚至空间也没有,我们借着文字,得知自己都在尘世。而我总是试图从光阴里寻出意义。环境的污垢似乎不能真正说明什么,只是由它影射而出的灵魂的污垢让我震惊。诱惑来自四方,它甚至不是邪恶,而是荣誉、理想或者自以为是的光芒。哪一种生活是我们想要的?你以怎样的标准评判别人的生活是丑陋卑污的而你自己的生活又是纯洁高尚的?世间是一面巨大的哈哈镜,每个人都在自以为是的痛苦中哀悯自己,并在哀悯中搜刮着自以为是的无辜与崇高。在这个烂泥塘中沉浮挣扎,谁也不比谁幸运,谁也不比谁光荣,而内心的光明需要多少次的洗净双手,才配得上垒起一块洁净朴实的砖瓦。人生的多艰,实在于灵魂的苦痛。这苦痛又细微、又真切,如同菜市场上那些死鱼的眼睛:圆形、凸出,在凝滞的白色、褐色、黄色灰色中印着一抹惨淡的灵性曾存的证据。前一秒,它们还在简易的铁皮池子中硬生生地弹跳;后一秒,它们就在血污的砧板上被剁成了十几段烂肉。生命无外乎此。
但是我们对生命知之甚少。甚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对大多数人来说,从生到死,生命都是混沌污浊、不明所以的。古人说,未知生,焉知死?东方文化中的两极(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弊端,在西方的《圣经》中得到了成全:西方用文学和宗教引导大众从死的恐惧中催生生的渴望。然而,“死生亦大矣”,西方返照内心的属灵生活发展到极致,也不得不回望东方文化对自然和现实的宽厚思考,因为西方文化对个人内心信力的训练到达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某种莫名的掌控欲,令他自以为世界在其心中。当意志力企图取代生命的自然力,就很容易忘记初衷,自以为无所不能——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瓶颈所在。对西方属灵文化的恐惧,对东方宽厚精神的奢望是现代人内心一个隐秘的弊病,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过那种尖锐的深渊苦痛,不能透彻地穿越西方文化,你就无法彻底回归东方。正如五四时期,前辈们如果未曾沉湎于散漫深厚的东方文化,未曾在国仇家恨中品尝过东方文化的阻滞血腥,就不可能渴望西方尖锐的属灵精神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肿滞进行一次全面的切割,甚至极端的摧毁。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生命;对我自己来说,七年的时光也不仅仅是时间。它是一心追求西方属灵生活却在现实中头破血流的尴尬,是生命在浑浊冲撞中变得干净清晰的过程。生长的时刻,无须喧哗。现在,古中国的辽远让我们步步深入山鬼的深处,那里潮湿、冰凉,有暗极而亮的天光,幽蓝深处的青白,最后,是平常时节的平安。这时,山雨就下来了。我于满室风雨的寂静中,窥见了天地深处真正的生命,和一颗澄明净澈的心。
是的,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历世和撕扯,生长和衰败,生命和自由,文学和命运。生命如一条宽广汹涌的大河,在我面前徐徐展开。当命运的潮水随整日整夜的大雨汹涌而来,黑暗就适时地吞下了整个世界。生命在夜的幽深里涨满了身体的堤岸,它无声、狂暴,侵吞一切。脚步在无声的狂怒中踏出回响,一个模糊闪烁的世界开始成形。我想,那就是天堂图书馆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