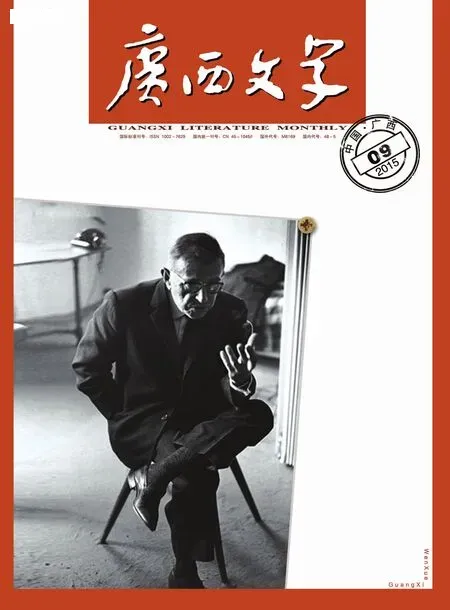钉子被移来移去时
2015-11-14林虹/著
林 虹/著
一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我推开窗,深呼吸。九月的风里,全是热气,高大的榕树枝桠,有蝉在“咋啦咋啦”地叫,好似“开心开心”,很热闹。我一点也不嫌它们的聒噪,那是爱的声音,人间最美妙的声音。它们知道生命短暂,当爱则爱,一点也不迟疑。它们还知道向死而唱,比起人类,它们自成体系的生命哲学,是向上和向乐的。还有一只鸟,在上午或下午的某个时段,叫着“你莫怪,你莫怪”,叫的是桂柳话,慢悠悠的,如此清晰,一听就乐。我很好奇这只鸟,它怎么会说桂柳话呀。它在向谁道歉呢?因此,只要我被烟熏得晕沉沉时,就推开窗,听这些有趣的叫声,特别是这只道歉鸟,它让我想起乡音,想起百里之外的家乡。奇怪的是,从不见它的踪影。它和蝉一样,隐伏在枝桠。
这是一个有趣的世界。
如此,我开始原谅这些缭绕的烟雾,淡淡的烟味。那是一张张葱绿的叶子,也曾有阳光和雨露的味道,以及月光和露水、虫鸣和微风,世间最好的景致曾伴它们成长,最后才成为这些烟味,也是修炼过的。如此,才不辜负了它的本质——爱我,就给你智慧。这只是我的个人感悟,我曾经多么讨厌这些烟味,在一次次创作会上,我被熏得头昏眼花,心躁无比,有老娘不如拂袖而去的念头。是的,多少次,我就是这样,老娘拂袖而去了,那样的冲动,结果就被窗外的声音化解了。“你莫怪,你莫怪”,“咋啦咋啦”,“开心开心”。当我会心一笑,我知道,拂袖而去,终究还会回来。莫非,它们知晓我内心的秘密?因此,声声如佛,看我得道多深。
我不禁笑。
导演抬头看我一脸闲适,甚至笑意融融,不解。“你想出什么好点子了?”而他,眉头紧锁,手指夹着烟,一圈呼出的烟,还未散去,正笼罩着他年轻俊朗而又疲惫的面容。昨晚的创作会开得很晚,走出大门的时候,星光稀疏,月色寂静,南宁的民主路上,偶有车辆开过,便剩下满街灯光。我从没见过民主路这么安静,白天车来人往,喧哗得让人想要逃离。此刻,我喜欢它的安静。导演问,要不要送你?我摇摇头,酒店就在附近,走过去就好。于是,我就慢悠悠地走着。我的脚步是沉重的,内心有牵绊,当然不能释然,虽然月华正当。如果我能有今天的得道,从一些鸟鸣中体悟,我想我会是走得很轻盈的。那么,那点创意,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说不要紧,也是要紧的,舞剧《瑶妃》毕竟是我的第一部大戏。就如怀了孩子,总想着他长得健康周正点。至此,已经走到最关键的一步——和导演的二度创作切磋,开始舞台执行台本的创作。二度创作,原本是导演的事了,我可以不参加,毕竟舞台的呈现,于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这个年轻的导演有他不同的创作理念,他组建了一个年轻的创作团队,从舞蹈编导到音乐、舞美、服装……都是充满朝气的,像灌满了浆汁的玉米,长得满目生机蓬勃。因此,彻夜奋战,也不是不可以的。这样的队伍,你会被感染。
除了文学指导德高望重,是的,他虽资历最深,却不比这些年轻人缺乏什么。他的思维和精力、阅历和经验,给这个团队注入了鲜活的力量。而我,作为编剧,混淆其中,也属正当年的那种。导演需要我的文学表达,何况,对于一个剧本的解读,他也想在舞台的呈现上,听到我更多的诠释,以便更快地把这个文学脚本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在舞台执行台本的创作时,同时也在完成场次的叙述,用简洁而又有美学意义的词语,表达这一场剧的内容,让观众一目了然,又过目不忘,甚至回味无穷。他让我去看看赵明的舞剧《红楼梦》。
这是个好的建议,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编剧,这是我最好的学习范本。此前,我开始创作舞剧《瑶妃》剧本时,也像棵灌满了浆汁的玉米,感觉体内的力量无尽,生长是如此快乐。我借用小说创作的方式,一气呵成,当然,早期的资料已了然于心。当我把一个晚上写出的剧本递给领导,她惊讶我的速度。而其中的框架构建、思想维度、情节呈现,居然有些地方和她的想法不谋而合。这让她惊喜。因此,我得到了这个剧本再深入改编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立项,申报经费。至此,我就开始了对这个剧本的不断修改,最后,搬上舞台。
我开始在网上找赵明的舞剧《红楼梦》,这个大师颇具胆量,挑战了这个名著。要知道,《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博大精深,情节丰富,人物繁杂,拍成电视都几十集,文本厚得都可以拍死人。赵明却把它搬上舞台,可想而知,这是多么有勇气有智慧的事。可是赵明成功了,他将《红楼梦》重新结构,提取黛玉葬花、海棠诗社、太虚幻境等有代表性的场景搬上舞台,用肢体语言完美诠释了这个名著。当然,导演特殊的思维方式介入,是舞剧的亮点,比如在诠释“黛玉葬花”这一场,是花葬黛玉了。这是个有意味的转换,这种文学意向的颠覆,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而舞蹈赋予的力度、视觉、冲击力、空间感,给人耳目一新的体验,化繁为简,简而有味,便是舞剧的魅力所在。
而舞剧《瑶妃》,能借鉴的,或许就是在于人物的诠释了。以人物的命运贯穿,讲述明朝时期一个瑶族女子的传奇人生。然,传奇无处不在,谁没有自己的传奇呢?关键是瑶妃李唐妹是明孝宗的母亲,她养育了这个有作为的皇帝,且是在后宫偷偷养的。这才是重点,一个坚强有智慧有担当的瑶族女子,她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这有意义的一笔。在时间的褶皱中,听见了她吟唱的一首歌。我找到这个剧的动词,爱。以爱贯穿剧。讲述瑶妃的爱,爱儿子,爱宪宗,爱家乡,最后提升到爱国家。比如舞剧《妈勒访天边》的动词是访,整个剧就是在寻找太阳中展开的。而导演似乎不赞同我对这个词的提炼,觉得这个词还不能承担他想要表达的,他认为还有更贴切的词来诠释。
二
那么这个词是什么呢?大家都在冥思苦想,香烟在这个时候,必不可少,它能提神,也能激发出潜在的、沉睡的智慧。
导演提到一个词,行进。这是个行进的民族。他的提议如醍醐灌顶,给大家在黑暗中打开一道光亮。我们不能拘泥于史实,思维必须跳脱出来,才会有新的东西涌入。导演说,要呈现瑶族的元素,它的精神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不屈不挠、不断行进的民族。一个为生命行走的民族,它永远都是积极的、向上的、勇敢的、坚强的、充满智慧和无所畏惧的。唯有行进,才能看到这个民族的变化和延续;唯有行进,才能体现这个民族的韧性。他的发言得到大家的赞许。文学指导进行了更深入的诠释:这个民族从大山走向远方,有的走得更远,还漂洋过海,这说明了瑶族的智慧,这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民族。对,开拓!导演应着。讨论突破了瓶颈,进入了白热化。香烟、咖啡和茶,还有窗外的鸟叫声,喧哗如此真切,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像弹一串音符。
导演像打了鸡血,这是他第一次导演舞剧,挑战难度很大。而我,第一次编剧,还属菜鸟级,这样的合作,我们从未质疑过对方。场记不停地给大家加茶、咖啡,张罗买什么盒饭。编导、音乐、服装、舞美也在讨论中碰撞自己的思想火花,以求寻找和剧目的最佳切合点。
我说,我想要有一场经典的舞蹈,类似于《白毛女》的窗花舞,让人过目不忘。导演深知我意: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一个剧,只要有一首音乐和一个舞段被流传,成为经典,那么这个剧就成功了大半。我说要有一个女子的瑶族小群舞,美丽的瑶寨,瑶族服饰,蝴蝶歌,长鼓舞,场面欢快,舞蹈优美有特点。最好是打着瑶家油茶,月夜,火塘,意境很美,情思雅致。导演说,大杂烩?我知道你想把瑶族的元素呈现出来,可是也不能硬贴,要和剧目的气韵一致才好。我坚持己见。导演问,你想怎么加?我说,在瑶妃进宫后,和宫女们跳梳妆舞时,以长鼓为由,讲述她在贺县桂岭的生活。或者,在遇见宪宗时,和他说起她在桂岭的快乐生活,那么打油茶,唱蝴蝶歌,跳长鼓舞,也是合情合理的。导演说,你以为这是在拍电影?镜头一切换,场景就变了。这是舞剧,空间就在舞台上。他说得有道理,那么这个女子的瑶族小群舞就没希望了。我已经在脑海里想象她们的舞蹈动作了:火光下,她们在打着油茶,蝴蝶歌流淌其中,优美的身段,在打油茶的起伏中,像剪影一样充满了意境。而长鼓舞,也适时而出,这种欢乐恰好和瑶妃在宫中的思乡呼应,是一种视觉冲突。
我有些怅然,走出楼道透气,从窗口看去,外面红尘滚滚、热气腾腾,充满了烟火气息。为什么要穿越六百多年的时光,在一个瑶族女子的身上寻找一种坚韧的品质?因为她是广西唯一的瑶妃,因为她在和命运的抗争中,闪现了一个瑶族女子的聪慧和美好,这是可贵的、稀缺的。即使她消失在六百多年的时光深处,她依然是被传说的。我曾去过她的故乡——贺县(今八步区)桂岭白石村,她的儿子明孝宗给她建了衣冠冢,追封她为孝穆皇太后。衣冠冢陈旧沧桑,朝廷赠送的石羊、石龟散落田间,印证一段从未尘封的历史。我问在田间劳作的妇女,知道瑶妃吗?她们指指衣冠冢。是的,她在这田间地头静默了六百多年,如果时光流逝,她不被掳进宫,是不是和普通的瑶族女孩一样,过普通人的日子,结婚,养儿,劳作,和喜欢的人白头偕老?
就如此刻的我们,置身红尘中,也是循着命运的轨迹前行的。那些看不见的时光中,终究有些不可知,是我们无法探究的。不问不想,也是好的。就如昨天黄昏时,我在对面的市场漫步,一个卖杨桃的女子叫住我,买点杨桃吧,我自己种的。我在她的摊位前停下,杨桃卖相不是很好,我也不喜欢吃。我没有买的意向。女人又说,你尝尝,不甜你不要。她满脸的笑,有点急切。是的,这个时候,倦鸟也归家了,她的杨桃还没卖完。她用刀割了一小块,递给我。指甲的缝隙里,有污垢,手晒得黧黑黧黑的,和她的脸色一样。这是个常年在日头下劳作的女人。我尝了下,是挺甜的。要完吧,不多了,难遇到自己种的杨桃。我看着她热切的眼神,说,好吧。她欢喜地捡着杨桃,唠叨着:我家离这挺远的,原来想着要照顾孩子,在路边卖,被城管赶,有次没来得及走,车也被城管没收了。这不,就老老实实来市场了。远是远了点,但踏实。我把这些卖完,就回家了,孩子小,盼着我呢。她的一番话,没有抱怨,一个能和生活和解的女人。我拿过一袋沉甸甸的杨桃,说,你早点回家吧。她说,还有几个香瓜,卖完了就回,出来一趟不容易。我问她,香瓜也是自己种的?她说,不是,贩来的,小本生意,自己有点事做,赚点小钱,心里踏实。这是她第二次说到踏实。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一种满足的光芒,是真真实实的。
真好,我看着暮色中的女人,只有一个当了母亲的人,她才会为了孩子这么去打拼的。
我把杨桃给了酒店的服务员。那个绾着头发用深蓝色蝴蝶结扎着的女子,总是笑意融融。我在大堂的墙上,看见酒店员工的一个亲情园地,那上面有员工和家人的来信选摘,她的照片下,是她的儿子,圆嘟嘟的。她写给儿子的信充满了温情,这是一个在外打工母亲的思念,朴实而动人,我因此而记住她。她和我聊起孩子,一脸的幸福。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我和他父亲到城里来打工,到时把他接来城里读书。她说着,眼里闪着光。
母亲的爱,是世间最无私最温暖的。我的思绪又回到瑶妃的身上,我要在这个剧中,如何体现她的这种爱?她和在后宫偷偷生养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有一段感人的双人舞?我回到会议室,大家依然在讨论剧情的结构。我提出的这个构想,得到导演的赞同:这是瑶妃教育孩子学习瑶文化和汉文化的一段戏,我们有一个瑶族双刀舞的构思。我对这段双刀舞很感兴趣,而从北京舞蹈学院进修回来的四位编导,阵容强大,我对他们的编舞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年轻,还因为他们有不俗的创意。而编这段双刀舞的编导亲自领舞,这是这个剧的一个看点。而这段舞蹈,就切入在瑶妃和孩子的双人舞之后。
年轻有个性的编导说,这是一段雄浑、有力度、有生机的舞蹈,展示瑶族男子刚毅、勇敢的魅力。音乐创作接过话题,是的,这段舞蹈的音乐我已有了构思,加入铿锵的鼓声,将会很有震撼力。“为什么不是长鼓舞?”我提出。长鼓舞才是瑶族有代表性的舞蹈。而长鼓一直贯穿整个剧,从瑶妃离开瑶寨的长鼓离情,到遇见宪宗的长鼓定情,到幽居后宫的长鼓思情,到亲人团聚的长鼓叙情,长鼓就是这个剧的一个象征。导演说,是的,是这样,但是在最后一场戏,我们会有一个场面宏大的长鼓舞。而双刀舞,相对于小皇子学习瑶文化,我觉得更贴切,那是勇敢和信念、力量和不屈的象征。
如此,我就沉默了,看着窗外的榕树,蝉依旧在“咋啦咋啦”地叫着,还有“道歉鸟”,隔一段时间会持续叫上一阵子,然后沉默,如此反复。没有人注意听它们的声音。我的耳畔一边是鸟鸣声,一边是音乐制作哼唱的蝴蝶歌。“留的西,拉的咧,蝴的蝴,蝶的蝶,黄的蜂……”
三
“留的西,拉的咧,蝴的蝴,蝶的蝶,黄的蜂……”这是瑶族的蝴蝶歌,我喜欢它的歌词,很有意味,而旋律也带着强烈的瑶族文化印记。因此,它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六百多年前的瑶族同胞,他们唱的山歌是什么样的,已无从考究,而艺术的虚实结合,让蝴蝶歌重新得到了诠释。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我对瑶族山歌的印象,最早来自仙回瑶乡的茅坪村。我出生成长在仙回瑶乡,如今,瑶族同胞的生活和汉族已没什么区别了,只有在偏远的茅坪村,还保持着过山瑶的风俗。当年我父亲中师毕业,就分配在茅坪小学工作。我曾去过那里,瑶族人淳朴憨厚、勤劳踏实,他们靠山吃山,有着坚韧果敢的开拓精神,和这个舞剧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
然而,小时候,我更多的是对这个民族的神秘感兴趣。比如,听得最多的是,会法术的过山瑶胞,一根黄茅草压在路边,丢失的东西就会回来;两根筷子叠起,心术不正的人就寸步难移;能在异地听到熟悉亲人的声音……我听着这些,就感觉那些穿着瑶族服饰的人很灵异,是带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他们来自一个神秘的国度。所以远远看见那些盘着绣帕,穿着精美刺绣瑶服,背着鱼网袋来赶圩的瑶胞,我就躲得远远的,生怕自己不小心会沾染上那种神奇的事。事实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出门上山之时,总会扯根黄茅草给我们扎上,说是避邪。这样的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有些事情无从解释的,我相信每根草都有它的灵性和神性。
父亲从瑶山回来,会跟我们说起那里的情况。父亲说那里的瑶族同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神奇,他们和汉族人一样劳作,按节气耕种,生活的风俗也差不多,他们纯朴、善良、勤劳,张口就能唱山歌……是的,是这样,这是我在茅坪村所看到的。那时,我住在小林香屯的一户人家里,他们家的房子建在山坳里,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阿婶和阿叔六十多岁了,一直生活在山里,他们在山上种八角、毛南竹、柚子,养竹鼠,采野木耳、香菇,割松脂……日子像山泉水一样平静纯净。夜里,他们坐在火塘边,阿叔默默地抽着水烟,阿婶在一旁剥着豆壳,有时给阿叔添点茶。孩子出去打工了,他们俩每天都是这样,话不多,各做各的事,一种平静的幸福。这种平静就是相濡以沫。我和阿婶聊天,阿婶,你戴的帽子重吗?习惯了,结婚戴到现在。阿婶很祥和。一直生活在山里,有没有想过出去看看啊?阿婶笑着,老了,不想去了。阿叔在一旁搭话,你阿婶的山歌唱得很好的,见到哪样唱哪样。阿婶有些羞涩。我问阿婶,唱下好吗?好。阿婶很爽快,清了清嗓子, “啦依呀啦……”,歌声清冽干净,一点杂质也没有。我惊讶阿婶的声音。阿婶说,以前上山时唱,做工时唱,觉得日子没那么静,没那么苦。那时啊,鸟儿听了都会停下叫声呢。没想到阿婶还这么有趣。阿叔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说,是挺好听的,唱得我都没法接。
很久以后,我还想起这样的歌声。因此,我提议在“行进中的民族”这一场戏里,用上这样的拉法调。音乐制作听了我的哼唱,很感兴趣。他说,这样没有杂质的原生态音乐,是这一场戏里的音乐之魂,太稀缺了。而编导,已经在陈述他的舞蹈构思了。
编导说,背景是一幅和舞台一样大的瑶锦,一座升在半空的群山,露出瑶族男子的脚,他们迈着矫健而有力的步伐,从山里走出,走向广阔的外界,而群山随着音乐缓缓升起。行进中的瑶族男子,诠释了这个民族的勤劳、勇敢和刚毅。瑶妃李唐妹出现在群舞之中,怀抱长鼓,边舞边走,寓意她走向大明皇宫,走向她未知的命运。他的想法,很新奇,首先是悬在半空的幕景,露出的脚,这吸引了大家。导演很惊喜,嗯,有创意,说,往下说。编导用手撸了下头发,这场戏要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瑶族元素要用足。因此服装和音乐、道具和舞美,都要有自己的亮点……
这是个燃点,第一幕是一个剧的起承转合,很关键。就如写小说的第一句话,调子和内容的走向,都已在其中。因此,服装、舞美、道具开始了各自的陈述。
“啦依呀啦……”说起故乡,就想到了在南宁生活的父母。我停止敲打键盘,望着窗外九月的天空,望着父母生活的半岛方向。我知道,此刻,他们正在侍弄着那几垄菜地,绿豆、红薯、玉米、韭菜、藤菜……长势正好。他们保持着瑶乡人和客家人的勤劳,保持着见门开山的本性,和土地的情感,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乡情。父母已年近八十,依然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们做了个重大的决定,在南宁安家,买房,装修。这是一个远离故土的城市,于他们是陌生的,他们得重新开始熟悉、适应。每天,他们两个人一起散步,沿着荔滨大道,默默地走着,有时聊天,有时沉默,累了就在路边坐一坐。看着邕江水不停地流淌,而五象大桥上的车子像梭子一样,对面的良庆区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他们看着近处的高楼,其中的一户,是他们的家。从前,他们在小城生活,出门就遇见熟悉的朋友,聊聊天,散散步,一起聚聚。毕竟是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熟悉、亲切、安心、舒适。而今,他们必须坐上一个白天时间的班车,才到达这个城市。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熟悉的乡音,没有熟悉的可去之处。唯有的,就是他们的三个儿女及家人。
而我,远在贺州,每次来,就和他们去江边散步。所以,我熟悉他们的路线,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心底的从未说出的思乡之情。我们坐在木棉树下休息,那时,是四月,木棉花开得轰轰烈烈,母亲对这种花极为感兴趣,怎么会没有叶子啊?花怎么开得这么多啊?树怎么这么高啊?她欢喜地要我给她和这些花拍照,各种姿势,乐此不疲。年近八十,保持着这样的生活态度,我是很开心的。我们坐在树下休息,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母亲感叹,唉,多熟悉啊,像我们老家院子里的鸟声。是的,我也这么感觉,老家院子的鸟,也是这么聒噪和淘气的。落在院子里,叫个不停,还闲庭信步,从它面前走过,也不避让,一点也不惧怕。我们和这些鸟相处甚欢。那个院子,留下多少我们的美好时光,积累起来,比铺开我们从南宁去往昭平那一整个白天的路程还多。
母亲听到鸟的声音,便是在这个陌生城市的乡音。她一个熟悉的朋友也没有,父亲也一样。父亲说,如果,你们有一个留在昭平生活,我们就不会考虑来南宁了。是的,我知道父亲的想法,老了,终究是想在家乡生活的。可是,他们依然保持了年轻时的那种干劲,在晚年的时候,重新开始适应一座陌生城市的生活。父亲的性格里,有着客家人的吃苦耐劳。而母亲,有着瑶乡人的坚韧勤劳。他们在仙回瑶族乡,白手起家,建了房子。然后,又带着我们到县城生活,在县城建了两次房子。然后,又到南宁买房。一个瑶乡人,一个客家人,骨子里迁徙的本性,让他们不屈于生活固有的东西。行进,创造一个个新的起点,即使生活重新开始,也努力让它开始得更丰富和美好。
我也被父母影响着,感染着。比如写这个舞剧。父母说,好好写,这样的机会不多。是的,我知道,对于一个半路出家的编剧,能有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他们也会问到我想来南宁生活的事,他们希望我也像他们一样,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行走至自己人生最好的状态。
因此,我对这个舞剧的诠释,对瑶妃个体命运的坚强抗争,有一种新的感悟。作为编剧,我呈现了这个意思。而导演,他能和我的想法有共鸣吗?
四
事实是可以的,我们都看到了黑暗中那一抹温暖的光亮,感受到了来自生命里那种原始的力量维度。比如在太监张敏这个角色的处理上,这个有良知有温度有担当的太监,在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为此,我还查了他的原籍,福建厦门人。这是一个我敬重的太监。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那种脸谱化的坏,比如明朝的宦官郑和,他的七下西洋,对航海和贸易是有贡献的。张敏在奉万贵妃之命溺死瑶妃的孩子时,做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留下孩子,告知万贵妃孩子已死,并偷偷带食物给瑶妃,一起养大了这个日后成为举国拥戴的明朝皇帝——孝宗。当然,还有那个被宪宗废弃的吴皇后,这个善良的吴皇后,经常偷偷接济和看望小皇子,以至于孝宗登基后,把她当母亲一样看待。还有那个不知名的宫女,万贵妃让她端药给瑶妃,要坠下那个孩子,这个好心的宫女回去告知万贵妃,瑶妃没有怀孕,只是生了肚胀的病。以万贵妃在后宫的势力,太监和宫女如此这般,是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的。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总有些温暖的事和人,让灰暗的现实充满了光亮,而一些朴实渺小的生命,却散发着人性的光芒。
这些温暖的人,改变了小皇子的命运。这些温暖的人,也温暖着瑶妃。在后宫,六年,小皇子藏在密室里。瑶妃和他在那个仅能从透气窗看见一方天空的密室里,相依为命。长鼓舞,瑶族山歌慰藉了乡情,还有瑶绣,盘在小皇子的头上,简直就是回乡了。窗外的海棠树上,有鸟鸣,是的,鸟鸣,和故乡的一样。这些声音的出现,成为每天的乐章。而阳光那么好,终有一天,他们能站在那些光下,看鸟飞过,看海棠花开,倾听鸟鸣。
那一天终于来了。瑶妃和小皇子不仅站在阳光下,还站在大明的江山面前。
我无法和导演说出那些诗意的鸟鸣,如何在舞台上呈现。而肢体的语言,能替代鸟的翅膀。而鸟鸣呢,如此隐喻,是否晦涩?
编导说到了光,一灯如豆,光的温暖晕开,是瑶妃命运的转折。是的,这也切合了我的心思。舞台上的光源就是命运的光源,总有一束,是能照亮出口的。
导演终于宣布可以休息了,我下楼出去透气。
九月炎热的阳光晒在水泥地上,又反射回来,热腾腾的。正值下班时间,行色匆匆的人群,在绿灯亮起的刹那,像海水一样涌出,他们奔向自己的目的地,神色各异,焦虑的、安详的、闲适的、疲惫的……我也被裹挟其中,在人群中茫然地向前。那样的时候,我常有愁绪从心里涌出,人生都在不停地赶路,生怕自己放慢了脚步,就会落下。这个繁华的城市,于我是这么远又那么近,想起父母说的,你要来这个城市,和我们在一起,要努力啊。母亲说,找到适合你的工作方向,就去争取。我嘴里应着,可是心里却是怯场的。茫茫人海、滚滚红尘中,看似有路,其实不然。母亲说,你要拿出我当年的勇气来啊。那时,我从城里下放回去,和你们生活在娘家,被人歧视,生产队里有人要排挤我们。我找到乡里的吴书记,反映情况,才不至于无处安家。我知道的,母亲身上有一种韧劲,像弹簧,越压越有力度。这种生活态度我是欠缺的。我习惯于顺其自然,像我写的诗歌《钉子》:钉子沉默寡言/它已习惯语言的缺失/习惯被敲打,被移来移去/我们彼此习惯/它知道/我不是这颗钉子就是另一颗钉子/钉子的命运就是钉子本身。
如果,像听见鸟鸣一样,听到钉子移动的声音,那么,命运的褶皱里,总能看见自己的纹路在哪里。
六百多年前,瑶妃一定听见了钉子移动的声音,所以她才不会认为自己就是那枚被移来移去的钉子,认同钉子的命运。所以,大明的历史才不会改写。所以,才有孝宗那“弘治中兴”的辉煌盛世,才有他成为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嫔妃皇帝的一段佳话。他和张皇后相亲相爱过着民间的爱情生活,才羡煞了那么多人。
是的,即使不能到这个城市生活,也不能缺乏对自身命运的认同和妥协,即使是一枚被移来移去的钉子,也要在移动时,清晰地听到它的声音。我在阳光下,又看见那个卖杨桃的女人,依旧笑眯眯地吆喝着:杨桃,杨桃,自己种的杨桃,不甜不要钱。她黧黑的脸上,充满了阳光的颜色。或许,是她散发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所致,我觉得那种颜色很美。我走到她的摊前,她认出了我:是吧,我种的杨桃好吃吧,要不要再买点?我笑着,好,来两斤。我拎着这袋杨桃过马路,过往的喧哗声,有着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我居然极其享受。是的,即使那些带着热浪的尾气,那些飞扬而起的尘埃,都是这美好的一部分。
因为,我又听到了那些蝉的叫声,“咋啦咋啦”,“开心开心”,“你莫怪,你莫怪”。真是有趣,白花花的阳光下,我不禁抿嘴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