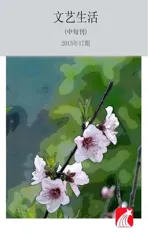程朱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2015-10-28刘云裳
刘云裳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程朱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刘云裳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格物致知,出自《礼记·大学》,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前提,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从宋朝二程将其拿来用作阐述自家认识论与修养论,无论在程朱理学抑或陆王心学的学说中其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程朱与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内涵分别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本文主要简述这种区别,并试图分析两者区别背后的学术原因及社会背景。
二程;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
对于“格物致知”这一重要命题,程朱与王守仁都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这种差异体现在关于“格物致知”的具体对象意涵、思维方式以及由此阐发出的知行关系的理解上。在这一问题上程朱与王阳明的不同理解背后体现的是理学与心学两派理论基础的根本不同。
一、不同理解的具体表现
(一)对名词“物”与“知”的不同理解
《大学》中虽提及“格物致知”,却并未对其具体内涵做出说明,二程首先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认识对象——“物”,二程与朱熹都认为“物”即事物。朱熹说“物,犹事也”。且这个“物”包含的范围很广,“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天下的万事万物,既包括花草树木等自然事物(“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又包括仁义礼智等伦理之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须要常格的尽”),皆在理学家格物的范围中。程颐就曾在《遗书卷十九》中强调“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世间万物皆有理,均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说明程朱对于需格的世间万物是无差别对待的,显然他们更强调忠孝礼义这些伦理纲常之事。“格物,‘须有缓急先后之序’,最紧要者莫过于‘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而对于另一个名词“知”,朱熹说,“知,犹识也”,即包括知识的知与道德的识两部分。小程同样将知分为“见闻之知”与“德行之知”,并认为知本是人心所固有的,不过因为外物的纷繁变化而致迷失,因此要通过格物将内心固有的先验之理完全发挥出来。
王阳明则训“物”为事,“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如此便将物的内涵内化于心了。心,意,知,在阳明看来不过是异名同物,所以致力于知,也就等于致力于心。另一方面,阳明将“知”具体发挥为“良知”,孟子就曾提出过良知之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阳明进行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良知即是人内在的道德之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会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是一颗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是天理昭然之明觉,良知就是天理。
(二)对“格”与“致”内涵的不同理解
在对名词“物”与“知”内涵理解不同的基础上,程朱与王阳明对于两个动词“格”和“致”的解释也相应的有所不同。程颐训“格”为“至”,“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又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就是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让心与理合一。朱熹也大致延续了小程的解释,在《大学章句》的补格物致知传中做出了具体阐述,认为“格”有二意:一则训“格”为“至”,“格物”便是“至于物”,二则训“格”为“尽”,“格物”即“知尽”,“知尽”即“穷理”。正如他在《补大学格物致知传》中所提到的那样,先“即物”,后“穷理”,以求“至极”,如此“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也”。对于外在于心的事事物物,人们需接触到,与物发生关系后研究其理,把握其规律以达到极尽处,与万理合一。而对于“致”,朱熹的解释是“致,推极也”“致者,推致之谓……推之而止于尽也”(《大学或问》卷一)将从格物所得之理,推致吾心之理,推及人心的知识使其达到无所不知的地步。
但将“物”的内涵阐释为内发于心的王阳明并不同意程朱的释义,对“格”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认为“格”非为“至”,而为“正”,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所以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体之正。”如此,格物不是向外探求,而是从自己本心开始,做到正心诚意,自能让我心之灵明得到彰显。而对于“致”,王阳明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之义’,‘知至’者,知也;‘至也’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就是推致,就是将发于我内心良知之是非好恶推致于事事物物之间。表明王阳明学说思想中心的“王门四句教”就将致良知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谓致良知,就是“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合二为一,进行主体自我的道德修养,从而合乎良知,体达天理,使心回复到明洁的状态。
(三)对知行关系的不同理解
在朱熹看来,格物与致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阶段,要先格物再致知,通过人们对世间万物一件一件的格下去,积习成多,自然就脱然贯通。而王阳明将格物致知统一简化为致良知,人们只需正心诚意,达致自心良知本体,将内心良知推至世间的事事物物。故将格物致知投射到知行观上,程朱均将知行分离开来,认为知与行有先后之分。“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即知先行后,还以生活中的事情作例,“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只有先知道了事物的规律法则,才能做出合乎规律的行为。只有达到真切的知,必然会有所行。朱熹在二程的知行观上又有所补充,认为除先后关系外,知指导行,因而知在行先;行又巩固完成知,所以行重于知。若论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
而对于程朱析知行为二的做法,王阳明就曾在其著作《传习录》中明确的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样只会导致“终身不行,终身不知”的后果,创新了“知”与“行”的概念,独树一帜的提出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说。在他看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心之知就是心之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二、不同理解背后的学术原因及社会背景
(一)学术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程朱到王阳明,格物致知的内涵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在得道的方式上,程朱强调循序渐进,在致知中达到对天理的领悟,阳明则在简易的瞬间中,通过察明内心完成对天道的理解。究其深层原因,其实主要是理学与心学之间思想碰撞的具体表现。虽然朱熹明确的说过“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但随后他又说道“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还是将心与理截然二分。格物是就“外物”而言,是物物上穷其理,是零细说,致知则是就“吾知”而言,是吾心无所不知,是全体说。在他看来,心与理一虽然可以成立,但是要建立在“解蔽”“涤除玄鉴”的基础上。理是客观永恒存在的,“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是理”。天理静洁空阔,无有不善。心却因会受到人欲的遮蔽,存在着善恶之分,因此否认心即是理。另外还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论点,虽然天下都是一理,但万事万物所秉受的理不同,“只是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这也为格物致知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作为崇尚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阳明无疑是会反对这种说法的。陆九渊就鲜明的提出“心即理”的论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如此一来,程朱向外探求天理的做法就显得不必要了,“切己自反,发明本心”即可。阳明也同意象山先生的观点,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的“格物致知”不是像程朱那样从外界推向内心,而是致良知,充分发挥我内心的灵明。早年的王阳明也曾按朱熹之法苦格竹子七日未得,反而大病一场。亲身实践失败多次后,他发现“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故在王阳明的体系中,无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之分,“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草木瓦石矣……盖天下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正如《明儒学案》中所说,“朱子以后,学者以知识为知,而以为备于人心者不过是‘明觉’。而且,因为理是天地万物共同的东西,所以就成了这样的认识:一定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以后,吾心之明觉才会与之一致无间。即是说,即便怎样提倡‘无内外’,实际上无非是完全根据外来的闻见来填补自己的灵明。阳明遗憾的,正是这一点。”而致良知说确也解决了朱熹之说一人无法穷尽天下之物与难以将心中之理与外物之理相统一的难题。
(二)社会背景
而从社会背景上看,程朱思想在宋明成为主流思想,影响极广。但朱子追求的格物致知思想造成了当时的士大夫在修养上知行分离,“没逆词章”,“支离决裂”等弊端。格物致知并没有达到当初程朱对其能助人“明明德”的希冀,反而成为他们追名逐利的工具。“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便是当时学术界的风气。王阳明对朱子学造成的“学术之弊”的不满促使他对程朱的修养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新的思考和发展。他的致良知说倡导人们涤除人欲,遵从儒家道德规范,也是对当时重视名利,轻视实践的社会风气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试图挽救的一种努力。
[1]冯友兰.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两派之不同[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S1).
[2]高全喜.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吕思勉.理学纲要[M].香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B244.7
A
1005-5312(2015)17-0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