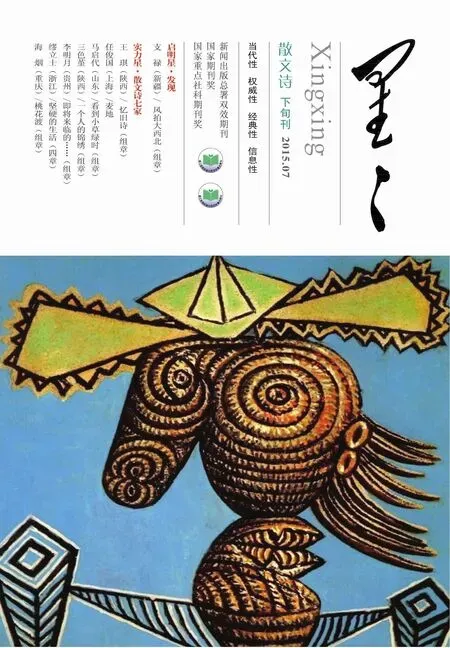写给打工诗人(三章)
2015-10-27韩嘉川
韩嘉川
写给打工诗人(三章)
韩嘉川
写给一个叫皮村的地方
据说那里没有路灯,甚而连狗都不叫。
叫的狗显然还在它们的故乡,不像诗人,已经遍布世界所有可以打工的地方。
在一份中国农民的遗产上,他们被以产业工人的名义,在城市边缘烟熏火燎的老屋里,修筑那些粘滞的梦想。
那时候的皮村,铁锈一样的黑浸蚀了所有的空间,喘息依然在途中闪烁其辞。冬天的麦苗一样,收获的期待还在远方,一个太阳出汗的地方。
在城市边缘的村庄,固守着农耕时代的尊严,并以基因的方式,让打工者用煤油灯的火苗,擦亮那些锈蚀的黑,那时候的皮村,没有狗的叫声闪烁。
是的,没有狗叫醒夜的地方,诗人们在吟诵诗歌,且时常忘词儿要低头看看手上的纸条。就像永远记不住城市的道路一样,置身其间,时常忘记来的地方。
在一份太阳的遗产上,煤与巷道在地下燃烧成诗,在瓦斯与煤矸石的裹挟中,与粉尘和思想的碎屑一起升上地面。
而雾霾困兽一样蹲伏在那里已久,将风声与远方的色彩掩进了默片时代。
水泥与铁与聚乙烯与苏丹红还有二英,让隔着山石与溪流风踪水迹的书写,比远还远隔着一面厚重的墙。
当你伸手将滴水的衣衫晾晒在地下室的那一刻,霉变的阳光散发着生活真实的气味儿,仿佛背带裙在柳梢轻拂的湖岸上飘扬。
狗以平等的家庭成员身份,享受一份丰盛的早餐时,新烧的青花瓷闪烁着日子的质量。
在一份岁月的遗产上,秦砖汉瓦缝隙里的苔藓,擦试着收藏者的流眸,而将月亮与螺丝帽,留给诗人去吞咽。
木轮车毂的吱响与铁轨流荡的光泽所组成的射线,沿着一声声雁鸣划向天边,留下土墙与漏檐,让孩子们用褴褛的童年守望。
在皮村,一个狗不叫灯不亮的地方,人们站立与匍匐在地,没有什么两样,至于手里是石器长矛还是起子与电脑也不重要,诗人是他们唯一可以找到的古老尊严与奢望……
狗不叫的地方,诗歌是他们唯一可以发出的声音。
故乡,一个遥远的意象
一声隔着早晨五点钟响起的汽笛,亢奋地吐着黑烟,发出沉重的呼唤的时候,我挣破梦的茧缚,睁开了双眼。
那声呼唤发自一座城市的西海岸,铮亮的铁轨磨损了很多时间,包括以百年的脚步响地踏着碎石垒砌的路基的晨雾,包括我爷爷童年的目光丈量的那一段斑斑锈迹。
太阳以黄昏色的庄严,落向西边的地平线,那里有村庄,有小河,有青纱帐掩起的偷情故事里走出青年男女的泥沙路,有午后的阳光抚摸土地的喘息有细风纤草抚摸羊的呓语……
太阳落下去的地方,还有高大的树和归巢的群鸟。
岩石垒砌的女墙与杉木搭建的木屋在林子深处,雨后的落叶与水洼铺陈着大地色彩斑斓的眉眼,而意绪饱满的白雪涂抹着季节的终点与起点。
枣红色的牝马驻足在冬天,炊烟用古老的思索方式,描述旷野的辽阔与悠远。
隔着教堂的钟声铺在大地上的影子,太阳落下去的地方,森林与山崖的记忆组成的河流,用蛙鼓、虫鸣与秋风的姿容做故乡的反光,然后在窗棂纸上,写下星月的地址。
裹挟着苞米大豆荠菜与蒲公英的乡野泥沙路,隔着奔驰的高速路,还有高铁与空客,故乡却始终黏连在一对摩托的轮子上,甚至生满冻疮的脚上。而驰骋的历史碾过了留守的废墟,将儿童的懵懂系在没有腿的课桌上。
岁月翻身醒来的时候,晨曦与黄昏对接在百年的轮回上,铁轨的斑斑锈迹,磨损着“遥远”这个意象。
老酒滋味
坎肩、苇笠、蓑衣,还有老槐树蓄积的蝉鸣和涝洼地里呱噪群星的蛙鼓。
苞米、瓜干、胡黍,加上秋天苇丛中的滴滴雁鸣与北阡巷陌赶海人漂在波浪上的渔歌。
柳梢的眉眼儿盯瞩着河水的纹理,把春天流经的饥饿描摹得栩栩如生,让坡地泛起满脸的菜色……
那时候,娘扶着门框,用黄昏的浆果酿制一声声温暖的呼唤。
草垛、泥墙、窗棂,还有夏日傍晚的风翻动枯黄的书页一样翻动的乡村的影子。
碌碡、磨盘、簸箕,加上栖落的鸟儿将各种声音汇聚,念头一样蓄积。
婆婆丁马齿笕和苜蓿草布置的春天,将记忆镶嵌在苦菜花瓣上,让思维从此晾晒在荒山野岭……
那时候,娘扶着灶台,用水蒸气与菜团子酿制一声声温暖的呼唤。
风的镰刀收割着麦香,也收割着娘脸上的光泽;沿着麦芽的气息,即使千里之遥也能寻到娘的怀抱。
季节的手扬撒着洋槐树的花瓣,也扬撒着炊烟熏黑的老屋的影子;沿着年轮的印记,即使在岁月窖藏的深处,依然能摸索到心灵的故乡。
那时候,娘在村口的高坎上,扶着一轮太阳的晕光,让呼唤地老天荒……
就像冻疮让我想起北方,想起冬天昏黄的油灯光晕里甜兮兮的地瓜味儿;沿着窗棂的空隙,岁月的叙说用霜冻白雪,还有星光的闪烁。
那时候,娘在炕头上,将针尖在白发里磨了磨,继续纳儿行千里的鞋底……
一杯老酒,蓄满了娘呼唤的醇厚味道。
一杯老酒,端起来竟是两眼热泪汪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