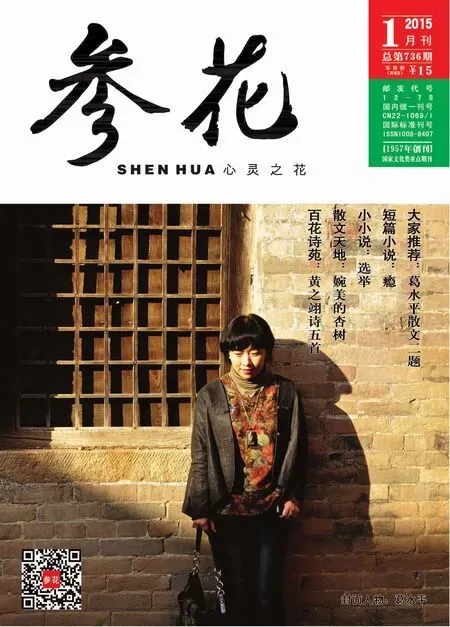蛤蟆吵湾
2015-10-27周国恒
◎周国恒
蛤蟆吵湾
◎周国恒
在老乡老家,蛤蟆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在夏夜里,我们把蛤蟆在池塘里的成宿不停的聒噪叫吵湾。
我的故乡,一入伏天,走在村中的胡同里,小蛤蟆崽直撞脚面。
故乡,有点像是人们的肚脐眼儿,平时不痛不痒的,安安静静地呆在那儿。时间长了,那地方会长出一个小泥丸来,黑黑的,像个小蚂蚁,有时它就忽然像有了生命似的,轻轻地叮你一小口。
自己就想,原先那地方还曾连着一截脐带,还曾经连着母亲的身体,连着那个给予我生命的地方,那就是让我牵心扯肺的故乡呀!
我的故乡,我的生命,我的童年,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心灵年轮的第一刀就在那里深深地刻下了。
我老家属于河北省沧州地区,我所在的村子是许多年前修运河时留下的一块高地,大概有百十亩。四周低洼下去一房多深,土都被挖去加固了河堤,村前村后留下了十几丈宽的洼地,一点也不规整,像被狼撕扯下去几块肉似的,隔沟望去,就是一片片肥沃得要流出油来的田地了。据老人们讲,一百多年前这还是一片荒地,是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把这个村子打造成了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
每年春天运河都会排汛,我们村前村后就会成为一片泽国。村北水浅的地方水勉强能到胸口,只是村子南面有一小片地方水特深,有人说能有两房多深。
从远处望去,我的故乡掩在一片墨绿的浓荫里,村前村后的坡上种满了柳树,有垂柳,箭杆柳。柳树这东西喜水,只要是水源充足,一尺来长的树枝子插进土里,用不了十年准成一棵大树。再多的树也改变不了中原大地夏日里的那股燥热,三伏天要是一连溜儿有个十多天不下雨,整个村子就像被放进一个巨大的锅里炙烤着,身上热得就好像骨头里的油都要冒出来。
春天的水里从运河过来点鱼苗,还没等长大呢,一到麦收水就干了,水边上看到的都是鞋钉子大小的小鱼。等着麦收一过,几场大雨下来,村子前后又是一片江南景色。这时候的水里全是小蝌蚪,密密匝匝的,一罩篱准能捞上半斤来。小时候我经常蹲在水边,看着那些生命的小精灵,又黑又亮,尾巴在树荫下的水里甩来甩去,我曾无数次慨叹生命的奇迹,蝌蚪变青蛙,几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些小精灵突然就长出两只脚来,小尾巴一点点变短。一进入伏天,蛤蟆就多起来,蹦跳着走出水面,进入村子,弄得满胡同都湿漉漉的,好像刚刚下过了一场小雨。
在三伏天,蛤蟆吵湾可称得上是我们家乡的一绝,中午天太热,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安安静静的闭气吞声,只剩下知了在树顶上迎合着炽热的阳光,玩命地聒噪。太阳一落山,那些刚刚获得生命的小蛤蟆就开始躁动不安了,先是东一声西一声的,试着调调嗓子,听着那声音带着些胆怯,还有些像牙牙学语的小孩,带着点奶声奶气的味儿。天一黑下来可就大不一样了,压抑了一天的生命就像是沉默百年的火山突然被扯开了一条口子,先是有几声领唱的,呱——呱,呱——呱,接着就有几百只蛤蟆跟着唱和,用不了一会的工夫,村前村后,村左村右就连成了一片,大有百里长江横渡的气慨。一张张大嘴巴,对着有月或者无月的星空诉说着生命的乞求。铺天盖地的噪音,像一团团蚕丝,夹裹着满天的燥热,围着你的脑袋缠呀,绕呀!让你一点也透不过气来。要是在你心静下来的时候,听那满世界蛤蟆的吵闹声,会别有一种不同的感受,那里有阿炳凄婉伤感的“二泉映月”,也有优美磅礴的“广陵散”,有柴科夫斯基苦闷彷徨的“悲怆交响曲”,还有贝多芬那热情澎湃的“第九交响”。千万只大嘴在那夜幕笼罩着的巨大舞台上演绎着各自生命中的酸甜苦辣。
童年的我,特别是在月夜的时候,经常独自彳亍在柳树下,池塘边,或把迷茫的目光撒向深遂的夜空,或对着燥热的黑暗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那时忽然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蛤蟆。
(责任编辑 张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