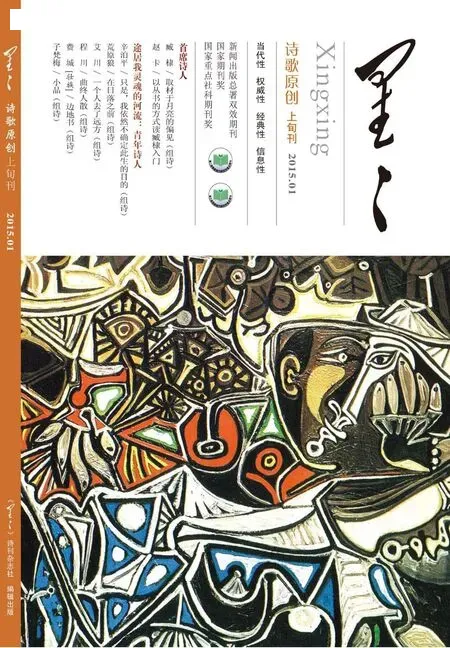我们的泪水寄存于江河(组诗)
2015-10-27王夫刚
王夫刚
我们的泪水寄存于江河(组诗)
王夫刚
母亲的晚年功课
夜不成眠曾经不被母亲视为一种疾病。
年轻时,她忙于劳动,生儿育女
并没有觉得黑夜
有多么漫长;黑夜的漫长
有多么可憎和不胜烦扰。
到了晚年,这个问题
才逐渐浮出水面:母亲的身体
越来越糟,叹息和担心
则越来越多——她每天至少吃三种以上的
药片,偶尔还让我去买安定
并且特别叮嘱:“药店不让买多。”
而我则习惯了清晨醒来
问她昨晚睡好了没有。
夜不成眠曾经不被母亲视为一种疾病。
但现在,不仅沦为一种痛苦
而且变成了她的功课
和我的请安内容。母亲乘坐长途汽车
来到济南(一个三甲林立的地方)
带着高血压,冠心病
和乡村的清凉,希望换个地方
在梦中与自己相安无事。
抱着马路边的小树哭泣的人
抱着马路边的小树哭泣的人是个男子。
马路对面观望的也是个男子。
女主角已经走远,背景的表情
已经由愤怒变得模糊。
公交汽车越来越少,打着空车灯的出租车
一如过江之鲫穿行于灯红酒绿。
抱着马路边的小树哭泣的人是个男子。
他没有喝醉,也不肯
喊住那个渐行渐远的名字——
他的包里装着一封不再需要写完的
信(也许是一颗滴血的心)
他一边哭泣一边打电话
让快递公司到有一棵小树的地方
来取邮件。抱着马路边的小树哭泣的人是个男子。
曾经付出、已经失去的爱值得一哭。
他拒绝爬到小树上面去
(虽然失去了爱,但还不打算自杀)
抱着马路边的小树哭泣的人
是个男子,无人值守的信号灯下
小树因为细弱而有点
无所适从:它还没有长到谈情说爱的
年龄,也不懂得安慰。
抱着马路边的小树哭泣的人是个男子。
马路对面观望的也是个男子。
他久久盘桓只为一个疑问
哭泣的人,哦,你为什么抱着一棵小树?
布尔哈通河
布尔哈通河的夏日,水上漂着北方。
布尔哈通河的夏日,彼岸
埋着婉容。金达莱是鲜花
也是无需国籍的歌声
唤醒早春:那任性的孩子还在奔跑
那任性的天空,就要下雨。
教科书上的布尔哈通河
流经少年的作文,以母亲河的
身份——那时他还不知道
每一条河流,都有一个
源头;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子嗣
要在哈尔巴岭的深山清泉中
遇见两个人的微微一笑
需等30年:谁在故乡完成自身的
流淌,谁将在故乡之外
永远做客。布尔哈通河的夏日
楼房高过柳树,少年却已
回不到桥上,雨过天晴
爱是布尔哈通河,也是布尔哈通河流域
花开花谢,监狱出身的剧院曲终人散。
退回来的信件
退回来的信件长着一张无辜的脸。
退回来的信件
长着一双夭折的翅膀。
它曾飞越千山万水,但地址
变成了遗址,收件人
变成了查无此人(此人是谁)
它把去时的路重新走了一遍
回到家乡——像一个考砸了的孩子
悄悄藏起卷面上的祖国。
退回来的信件已无秘密可言。
失效的问候,失效的见字如晤
失效的某年某月某日。
无疾而终的旅行属于失败的范畴。
幸运的是,失败已经很多
已经谈不上疲倦和无限沮丧。
寄存之歌
最初,我们的身体寄存于无中生有的想象。
寄存于母亲的子宫,父亲的怀抱
寄存于婴儿车,幼稚园
小学校,寄存于成长的风和肇事的
好奇。最初,我们的记忆寄存于表格,证件
迁徙,计划生育的一票否决
寄存于谎言和对谎言的适应。
最初,我们的衣服寄存于衣柜,手机寄存于数字
道理寄存于时光,春天寄存于雪莱的
提醒。我们的欢爱寄存于男女
歌声寄存于哑巴的喉咙
我们的美和丑陋寄存于失物招领处。
最初,我们的天空寄存于祖国
我们的孔子寄存于《论语》
我们的牌坊寄存于教科书;我们的笑话
寄存于一本正经;我们的轻浮寄存于竞相推出的重磅
最初,我们的健康寄存于药店
愤怒寄存于粥中;我们的诗篇
寄存于报纸的蔑视;我们的泪水寄存于
江河,骨灰寄存于洪荒。
最初,我们的身体寄存于无中生有的想象——
没有父母,没有家乡,没有历史。
离家最近的火车站
带着自己改制的发令枪,老朱和妻子
连夜开始了逃亡的人生——
不能坐车,不能走大路,不能近家乡。
留在身后的是,被一枪击穿的
信用社主任,他的上司。
警车包围的案发现场。
版本不一但持续发酵的市井新闻。
以及年迈的父母,托付给亲戚的幼小孩子。
逃亡,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旅程
老朱弃了发令枪,只带着
妻子——这个被他的上司
侮辱过的女人,支撑着他走了很久
走了很远,他乡渐成故乡。
在被夸大的绝望中,老朱越来越
讨厌天空;在绝处逢生的
希冀中,老朱不写信,不上网
不用电话,他跟妻子约定
如果走失了,离家最近的那个火车站
将是他们寻找对方的唯一地点。
不幸的是,15年后
他们真的走失了:修鞋匠老朱
通缉犯老朱,在警察面前撒腿就跑
而且,跑得无影无踪。
他的妻子,后来就到
离家最近的火车站——几年前刚通铁路的
地方,摆了一个披星戴月的小摊
生活的传奇在于,她等到了
老朱出现,当然——警察们也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