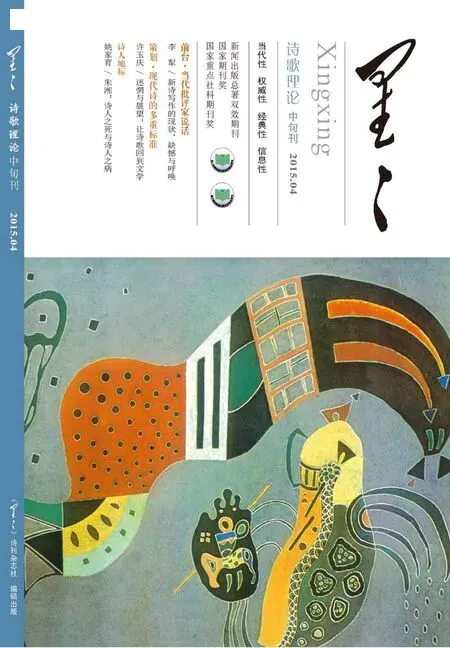潜在的“眼睛”
2015-10-27卢桢
卢 桢
潜在的“眼睛”
卢 桢
对写作者而言,写诗就是选择一种视角表述他所感知到的世界,其中“眼睛”的作用不容小觑。日常生活的缤纷物象、周遭人物的市井百态、活动空间的经纬方圆……都要借助眼睛的摄影功能加以捕捉,进而透过抒情者智慧的想象力,从瞬间物象被点染为诗歌意象,成为具有意味的客观中介物。可以说,用何种“眼睛”进行观察,就代表了诗人选择什么样的文化视角进入诗歌写作。他可以用纯粹客观的,透过单纯记录式的“冷抒情”,在诗行间定格一幅幅瞬间展开的视觉印象;也可以是融含丰沛情感信息的,因象生义,睹物思情,为心灵建立隐喻。从《好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把桃花和杏花分开》《在监控器下上班》这几首诗中,我们可以发现:诗人们往往能够在日常人的观察视角之外,透过潜藏于心灵中的另一双“眼睛”去发现世界,探索隐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另一番风景,诗歌的秘密,大抵也要通过这一双眼睛方可破解。
看《把桃花和杏花分开》,诗人刘高贵抓住了春天的细节:“把桃花和杏花分开/就是从春天里找出三月和四月”。由视觉定格出的种种印象,将抽象的“春天”变成具体的、可知可感的情
感信息。“眼睛”仿佛具备了某些拣选的功能,它可以忠实地依照我们的心灵诉求,帮助我们从芜杂的视像抵达个体演绎出的心像。从拔节声中“指认出大麦和小麦”,“从亲情里找出父爱和母爱”其实并不困难,那双潜在的眼睛总会使纷繁客观的印象向一个中心不断凝聚、集合,从而形成显扬的张力。即使“人海茫茫”,“你总有办法/将朋友和路人/一一区别开来”。“人海茫茫”是诗人对“人群”这一模糊印象的整体定位,在往来如织的人群中,个体通过瞬间、无序的视觉联络便能找到友情的存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情怀”。
以情怀为主导,诗人可以将自我灵魂附在他人和外物之上,不断对产生的视觉经验进行反思,以此来激发他们的诗情,以情趣实现对事态的强势渗透。看王妃的《好时光是用来浪费的》,诗歌的空间中存在着一双潜在的眼睛,眼睛的主人组合着貌似脱节的一幕幕剧情,看似对事态的随意扫描和经验拓影。它在“池中开着的睡莲”、“附着在一片落叶上的一滴寒露”、“焚香品茶抚琴读书”等“他者”的时光和自我的想象中游弋徘徊,散点透视着自然界和人生中的绵密细节,为读者播放出“好日子”的种种具象。阅读了旁人的经验之后,抒情者吐露了他对“好时光”的读解:“和婆婆对坐在阳台上/拽着她细碎的话把子,把新收的花生/一粒一粒,小心地剥出来”。一个极其凡俗的日常生活片段,却神秘无声地滑入抒情者的诗歌视阈,通过“剥花生”的细节,现代生活的亲情经验在诗人心中神秘地完成。诗人以独标一格的个体立场回答了“到底什么才是好时光”的命题,凭借其艺术直觉捕捉到那些易于从指缝间匆匆滑过的、凡俗中的瞬间之美,也从人们对“好日子”的种种经验预设和先在判断中抽离而
出,找到专属自身的心灵节奏。
与前两首诗相比,张守刚的《在监控器下上班》无意回味那种闲适的情怀,而是多了几分精神的紧张与不安。诗歌突出叙事效果的营造,抒情主人公有着由乡入城的打工者身份,她“总感觉有双眼睛/在背后偷偷地看”,甚至在工作间隙走进洗手间,神经质地“怀疑厕所里/也装上了暗处的眼睛”。在这里,“暗处的眼睛”成为全景环视监狱式的偷窥者,无论它是否在执行监督打工者的工作,都对那些潜在的被监视者们造成极大的心理威慑力,甚至使他们产生恐慌,如同抒情者那样“脊梁阵阵发凉”。被摄像头监视是抒情者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这与乡村世界中那种简单、直接的人际关系大相径庭。离城越近、离心越远的打工者们体验着从地理到心理的迁徙经验,诗人借助“摄像监控”这个现代城市普遍存在的物象实现了对城市人机械、冷漠、缺乏情感一面的批判。在这里,“潜在的眼睛”无涉与闲适经验相关的任何情怀,它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为底层精神作出注脚。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