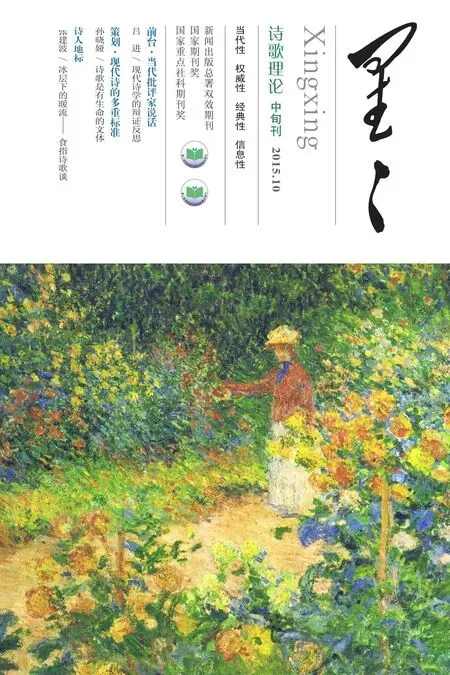诗歌是有生命的文体
2015-10-26孙晓娅
孙晓娅
诗歌是有生命的文体
孙晓娅
主持人语:
何谓诗?何谓好诗?在高度分化和碎片化的当今诗界已然难于达成高度的共识,我们不时听到诗歌同行之间不同立场尖锐对立、剑拔弩张的言论之争。这大概也属正常,“理不辩不明”,但同时,关于诗歌的共识的破裂、常识的缺失也值得每一位诗歌中人重视。因为,诗之为诗,总还是要有一些恒常、不变、标示底线与边界的东西存在,否则,“诗将不诗”。本期学者孙晓娅的文章即包含了一种重申诗歌之“常识”的努力。其所谈到的诗歌与生命本体的内在关联、诗歌语言的创造力与生命力等问题都是关乎诗歌评价标准的真问题,同时对于当前的诗歌写作而言也具有现实及物性。
——王士强
内在生命的力量与意味
1931年,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梁宗岱写道:“我以为诗底欣赏可以分作几个阶段。一首好的诗最低限度要让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惊佩于他底艺术手腕。再上去便要令我们感到这首诗存在底必要,是有需要而作的,无论是外界底压迫或激发,或是内心生活底成熟与充溢,换句话说,就是令我们感到它底生命。再上去便是令我们感到它底生命而忘记了——我们可以说埋没了——作者的匠心。”[1]梁宗岱在此提到的新诗美感的三个境界可以与新诗发生、发展和趋于成熟的过程形成对照,也表达出部分新诗理论先觉者心目中新诗应该达到的“理想高度”——凸显诗歌的生命感,淡化诗人的匠心。这让我想到里尔克所说的“心灵作品”,它们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必然的关联:更深的意义上,诗歌的韵律节奏对应着心灵的律动,诗歌是对心灵的记录,诗歌给了心灵一种最为合身的形式,淼不可测的心灵以诗的形式被浓缩,生命的感受在这种可实现的转换中获得。
诗歌的生命感在于触及、表达了心灵,向内汲取力量的同时,诗歌亦延伸着对生命的各种可能的表达。“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那支粗壮的笔躺着。/我要用它去挖掘”(《挖掘》),完成《挖掘》(1964年)一诗时希尼曾感叹:“正如帕特里克·卡瓦拉所说,一个人涉猎诗歌并发现诗歌是他的生命。”诗歌是诗人的生命或者说诗人用诗歌挖掘生命,这不是盲目夸大诗歌的意义,诗歌能够真实体现诗人的声音、特质,所有的表达方式都是挖掘生命感受的工具。由是,浸染着创作主体生命感悟是好诗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这种生命感还应该秉赋马拉美所强调的诗之“谜”,即诗应该体现出“艺术的神气的魅力”,这种魅力“释放出我们称之为灵魂的那种飘逸散漫东西”。马拉美绝非在宣言诗的神秘主义,他的本意旨在抵抗野蛮的物质文明的侵袭,维护生命的内在的自由和尊严。针对工具理性主义所营造的美学氛围,马拉美声言:在诗歌中只能有隐语的存在。对事物进行观察时,意象从事物所引起的梦幻中振翼而起,那就是诗。帕尔纳斯派抓住了一件东西就将它和盘托出,他们缺少神秘感;他们剥夺了人类智慧自信正在从事创造的精微的快乐。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趣味,这种趣味原是要一点一点去领会它的。暗示,那才是我们的理想。[2]诗歌的写作体现着一种特殊的生命的快乐,马拉美认为只有采用间接的暗示的方式才有可能揭示出生命的秘密、从事创造的快乐。
不独西方和中国的现代诗注重诗歌的生命意蕴,中国古典诗歌早已有此传统。就此,叶嘉莹先生曾多次给与肯定,在强调古典诗歌有生命的同时,她尤其看重诗歌的生命可以感发生命。她认为:杜甫读到战国时期宋玉的诗赋会感动,辛弃疾读到晋朝的陶渊明的诗也会感动,诗歌本身有一种生命,那个生命到现在也是活的,只要你真正能够理解这个诗人的生平,他的情感、他的生活背景,你就会感动。而且不但是你感动于他,这个时候你所感动的就不只是杜甫当年的感动,你的感动是被他感动了,可是这个时候就带着你自己的感动了,你自己的感动就有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了。所以诗歌里边不但有一种感发的生命,而且是生生不已的,是一可以生二,二可以生三的。
叶嘉莹先生曾经在不同场合、采访中谈及这段话,其中还蕴含了一个言外之意:优秀的诗歌与创作主体是合一的,如此由文本而来的“感发”才会延续意义。如同密茨凯维支在上个世纪的巴黎讲述斯拉夫文学时,谈到拜伦对东欧诗人的启迪时说:“他是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反思当下,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当代社会的读者日趋向平面化、娱乐化、单向度的生存方式靠拢,兼具难度与深度体验的诗歌,难免被疏离边缘,这个现代工业社会带给诗歌的危机,早在1820年就被皮科克预言为“诗歌的终结”——诗歌将日趋堕落,终将从现代社会消失(《诗歌的四个时代》)。究其实质,这是灵性和人性的危机,为了挽救这一悲剧的发生,华兹华斯、雪莱等诗人以创新的精神做了反思,他们强调实现诗歌的现代性必须走向内心,在探索中寻找新的价值观。新的诗歌的价值观本无统一性的规范,但是诗歌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好诗永远不去迎合大众,要葆有独立的个性、大胆的创造精神、强旺的生命力、与灵魂沟通的能力;好诗最终都是向内寻找力量,解答生命的意义,挖掘内心某种“存在之存在”,延展多重意味和寓意,让生命在诗歌中重生,而优秀的诗人终究是那些向内寻找力量并能够“像自己所写的那样去生活”的诗人。
语言的创造力与诗歌的生命力
诗歌是个体生命与个体使用语言之间的一种关系,想改变生命就试着改变语言,语言改变生命,生命也改变语言,语言在永远不停地流变之中发展,好诗就是对流变着的世界的再创造。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去蔽”,即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重新发现事物,“抵达陌生处”(兰波)、唤醒人的心灵。那么,正如荷尔德林所强调的“诗歌是语言的希望”,好诗必然具有独异的精神、有创造力和拓展力的语言,有个性化的声音,这几点质素又是息息相关彼有渗透。
兰波曾把诗人比作“窃火者”——从我们看不见的神那里偷来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景象来丰富人们的视野。为此兰波认为诗歌应该采用新的语言来写,至少他的诗歌应该成为灵魂的灵魂,包括各种声音、芬芳、颜色,把思想固定在人的思想之上,从而进行抽取。兰波诗歌的目的就是想要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打破一切的规律,打破人们一切的感官和意义。为此,我们要消灭几个世纪以来对人们所规定的规则和义务,所有的建设的落实需要从语言着手。中外诗歌史上,有影响力的诗人首先都是高度“自觉于语言”的诗人。曾经,华兹华斯将日常口语纳入诗,打破了几千年来将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隔离的偏见,拓展了诗歌的语言资源。毋庸置疑,诗歌语言的革新首先需要创造力,20世纪初,胡适明白易懂的白话诗学将中国诗歌从文言语体中解放出来,切断了文言分离的传统,自始,中国现代新诗开辟出一条围绕语言的探索之路,随后出现了语言的精致化、审美化的诉求,与此相关的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与日俱增。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建设中,伴随诗歌传统的功能的变化,不少诗人希望突出诗歌的形式及诗歌字词产生的效果,他们敢于用自己的语言方式重新定义诗歌,刷新诗歌的语言观念,积极投身于新诗建设。在众多自觉于语言探索的诗人队伍中,牛汉对诗歌语言的理解和实践极具个性,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建设颇具启发。
90年代,牛汉在与郑敏的通信中公开了他的奇特的写作方式的感受,提出并探讨了诗歌语言与诗人生命的内在联结及彼此间的互动性。[3]在牛汉看来,语言是有生命的,语言不是工具,诗人和语言之间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不是调动的关系,它不愿意被人统治和调动,被统治和调动的语言是强硬的,没有活力。作家和语言的关系、创作和语言的关系,诗和语言的关系都是互动的。在此基础上,牛汉认为诗的语言应当与诗歌一同“分娩”,没有先后,不是先想好主题再选择词语,更不是先写出诗句再构思主题,语言本身就存在着,他着重强调诗歌语言与诗歌生命融为一体的互动关系。牛汉用“母性的虔诚”、“生成”、“接生”、“充分燃烧”、“游牧”、“倾盆而下”这样的词句来形容他创作诗歌时的感受,他将诗当作从母体中分娩出来的新的生命,其富有创建的诗学观念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生成”首先意指创作中语言和诗人的互动关系——是语言和诗人之间的彼此生成,这一来自生物学的动态概念,不仅表明了他有关诗歌写作的有机整体观点,而且强调了作品于此居有的真正主体地位:一方面,一首诗的酝酿和诞生,犹如一个自在的生命;另一方面,由于作品的自在性同时牵动着语言——诗人的整体,因此,一首诗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能否既构成对这一整体的否定,又构成对它的重新肯定。绿原在给牛汉的诗集《温泉》做序时精辟的指出牛汉诗歌的想象“多半在动词,而不是名词或形容词”,正因此,他的每首诗都“构成一次完整的、不可分割而又不可重复的生活经验”。
牛汉提出和实践的“分娩”说与海德格尔对语言的看法十分相契,关于语言的“分娩”说与其自由自主的创作观念契合,它体现了牛汉思想的现代性和前驱性。牛汉反对诗人主观对诗歌语言的生硬把握,他反对“写诗”一词,更喜欢创造和生成,他在表述方式上侧重于说“一首诗如何生成的怎么诞生的”,而不是说“一首诗是怎么写成的”,他崇尚语言的独创性、反对模仿、束缚、修饰,他仅仅在呈现,让生命自我展示。牛汉之所以苦心选择和邀约语言这个神秘的接生婆,实为把心灵里即将坠地的那个独生子接生下来,尽情展示生命的律动。由是,虽然牛汉诗歌的语言大多近乎白话,但他的语言却强烈地打动人心,质朴而坚实,以坚硬的骨架,支撑起诗歌的血肉和魂魄。“然而,这似骨架的诗歌语言却拥有着极深的韵味,令人感到余味无穷,同时,其诗中质朴而不善雕琢的语言如同诗人的骨骼一般富有力量,并且时刻散发着庄严感。这可以被看做是艺术理论上的合理悖论。但是,仅仅这样解释似乎是不够的。应该看到,牛汉诗歌语言的魅力是与他的个性生命,与他的生命体验紧密地联系在—起的。”[4]早有评论家注意到虽然牛汉不刻意修辞,却往往获得一种意外的修辞效果。这一特殊的美学现象成为牛汉研究者绕不过去的研究焦点。针对类似“艺术理论上的合理悖论”,语言已经超出了诗人的理性的锻造,与他的心灵紧密连接。诚然,牛汉对诗歌语言的生命意识很值得我们深思,“透过牛汉的诗歌语言,处处体现出他对诗神的敬重,对读者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对万物的虔诚。”[5]牛汉诗歌语言的“分娩”说最大贡献在于,诗歌语言脱离了用于交流和审美的功能,突破表达的边界,成为解码生命与宇宙秘密的工具。
诗人蓝蓝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讲座“外国诗歌与我”中,谈及诗歌与语言之间的张力关系时概述为:“诗歌是语言的意外,但不超出心灵。诗歌是通过有内在节奏的文字,引起读者想象力重视并达到最大感受认同的。诗歌拥有在句子单位里迅速改变多重时空的能力,这是其它文学体裁望尘莫及的。”[6]上述观点让我想到吉尔·德勒兹所言:“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令新的语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7]诗歌的生命韵味需要富有创造力的语言去挖掘,那些没有被命名的感觉需要奇异的、陌生的或富有穿透力的语言去呈现,意料之外、突破边界和唤醒触动灵魂的语言,是好诗的创造性所在,它赋予诗歌独特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是很多诗人的志向。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1.李振声编《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2.马拉美:《谈文学运动》,《象征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牛汉:《致郑敏》,《诗探索》1994年第1辑。
4.章燕、屠岸:《牛汉诗歌中生命体验的潜质》,《艺术界》2003年第6期。
5.唐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诗刊》1996年第10期。
6.讲座题目:《存在于隐喻之中》,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11月19日),主讲人:蓝蓝;主持人:孙晓娅。
7.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