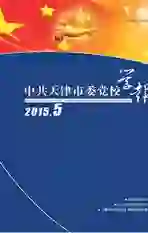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2015-10-21王天楠
王天楠
[摘要]结构型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网络作为研究的核心,通过对社会网络的历史考察、类型甄别和功能解析力图发现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的关系。从渊源来看,历史传统和制度政策相互配合共同构造了社会网络与民主制度的良性循环系统。从类型甄别看,那些具有水平结构、弱关系、包容异质成员的连接性社会网络更易于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提高制度绩效水平。从功能上而言,社会网络具有培育公民精神、制约行政权力的效用。社会网络为制度绩效的提高提供了强大动力,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了肥沃土壤。
[关键词]社会资本;制度绩效;社会网络;民主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5009507
“社会资本”首次出现于1916年汉尼芬(L.Judson Hanifan)的《社群的中心》,她观察弗吉尼亚乡村邻里和公民参与的古老传统,用社会资本解释共同体参与对于民主孕育和发展的影响[1](P4)。而对社会资本的系统研究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20世纪80年代,布迪厄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即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性的[2]。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继承并吸收了布迪厄的某些论断,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扩展。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并且彼此之间有共同之处。它们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3]罗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将社会资本的概念进一步应用到不同地区制度绩效的差异研究中,把客观维度的社会网络作为分析框架,力图使社会资本成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和解释制度绩效差异的关键要素。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超过了前者,他综合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把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定位为具有结构性的朋友、家庭、社区以及与公私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网络。他认为:“我们描述社会网络和互助的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因为像物力和人力资本(工具性和训练的)一样,社会网络创造了个人和集体的价值,因此,我们愿意投资到网络中。”[1](P8)这样,从布迪厄、科尔曼到帕特南,结构型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日益丰满起来,并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研究复兴运动①后分析政治文化与制度绩效关系的重要理论路径。
一、历史之维:社会网络之源与制度绩效的差异
历史主义是结构型社会资本理论较早采取的方法。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北方共和传统的考察,分析地区间制度绩效差异的原因。他发现:“20世纪末公民参与积极的地区,几乎都是在19世纪拥有众多合作社、文化团体和互助会的地区,在那里,12世纪时,邻里组织、宗教组织和同业公会共同促进了城市共和国的兴旺发达,但在经济表现和政府质量上(至少是出现地区政府后),却稳步地超过了那些公共精神不发达的地区。公民传统惊人的应变力,证明历史具有力量。”[4](P189)然而,历史主义并不能解释日本、韩国等儒教国家现代社会网络的成功培育和较高制度绩效的出现,学者们不得不用多元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传统、社会网络与制度绩效的关系。
(一)历史的宿命:共和经历、社群传统与制度绩效
帕特南对意大利的考察发现了一段具有宿命的历史,即在12世纪的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南方由诺曼家族统治,诺曼的统治者保留了拜占庭和穆斯林的专制传统,尤其是颁布了有效的垂直税收制度和表达君权至上的腓特烈宪法,由此,意大利南部成为欧洲众多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代表。权威的统治模式压制了南方的地方自治愿望,社会被中央专制体制锻造成纵向等级化的社会网络。而意大利北、中部的城镇与南方截然不同,一些前所未有的城市自治共和国成为散落在中世纪采邑——农奴封建制度中的绿洲,成为抗拒欧洲中世纪暴力与无政府状态的独特堡垒。这些共和国起源于邻里街坊自发组成的安全防御体系和经济互助联盟,后来这些私人性质的联盟发展为遍布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中、北部大城镇的城市共和国,共和国带来城市自治的同时也带来城市生活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达,从而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北部发达的工商业一方面培育了市民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促进了具有自治、互惠色彩的同业行会的出现。世俗组织代替了原来的等级教会,宗教权威降到谷底,市民社会开始繁荣。中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是由不同横向社会网络构成的一个个城市共和国,共和传统促进了公共精神的培养和社群的发育,为后来民主发展打下了良性的基础。19世纪末,统一后的意大利南北方的差异依旧显著,表现为南方社会垂直性依赖关系和剥削性社会联系与北方社会横向相互合作和互助社会联系的差异。国家政治上的统一并没有改变社会层面的差别,南方附庸性的社会网络和不信任的社会文化成为黑手党产生的重要因素,而北方合作社和互助会传统成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20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南北方的制度绩效差异仍然显著。
由此可见,历史具有持续性,意大利北方的社会资本是共和遗产的衍生物,它不仅是当代人再生出影响民主运转和制度绩效的社会资源,而且是历史传承下来具有持久性的政治文化财富。南方由于缺乏共和遗风的润泽,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网络,因而成为历史宿命中的“弃儿”。帕特南从历史中寻找到社会网络的源泉,从传统中寻觅到制度绩效差异的原因。
(二)历史主义的悖论:转型国家社会网络的培育
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新兴国家。对于这些共和遗产阙如、社群传统缺失的转型国家,建立起有助于提升制度绩效的社会网络是考验社会资本理论家的重大问题。罗斯坦(Rothstein)和斯道勒(Stolle)指出:“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创造、传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存量和类型。公民发展合作纽带、建立社会信任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制度和政策所影响。这种观点暗示出制度常常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酵母。”[5]马洛尼(Maloney)曾对英国伯明翰市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做过一系列调查。他发现,随着地方志愿协会更多地得到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地方机构变得更具开放性,伯明翰的志愿协会数量1998年比1970年至少增加了1/3,而且志愿者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协会生活的活跃性也明显提高。乔沃·利斯和布莱恩·多莱里经过研究认为:“地方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的网络能力之间的联系必须建立在对‘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影响特定区域社会资本的进入渠道及其形成的分析之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政治机会结构是通过地方政府修订的,这也许需要对帕特南和福山宣称政府政策很少能影响社会资本积累的自由主义结论进行重新评价。”[6](P351)他们还发现,地方政府对社会网络形成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正式的制度结构通过某种地方性的分权和相对开放的公共行政为社会协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二是地方政府通过教育和宣传手段培育出志愿者文化。鼓励人们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活动,进而培育公共精神、塑造公民意识。三是社会网络受到地方政府所处的整体政治环境影响。现代政治赋予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权利,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创造了制度环境。如果没有自由的制度环境,即使已经发展成熟的社会网络也会被专制政权废止或扼杀。因此,政治制度、政府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网络存在、发展的前提条件。endprint
制度主义的研究打破了自由主义关于结构型社会资本只能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独断结论,为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以及新兴民主国家维系和巩固民主提供了理论借鉴。从东亚一些已经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的社会发展实际也可以看出,伴随民主制度的成功确立,大量的社会网络破土而出,公民社会发育良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无法诠释这些从西方舶来民主的国家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而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开明的公共政策显然成为推进社会网络发育、公民人格成熟的直接动力。
因此,历史传统和制度政策是形成社会网络的两个来源,两者并行不悖。在拥有共和遗产和社群传统的国家,社会网络发育更早、更成熟,成为适宜于民主社会资本的发源地。而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制度的培育、政策的促进同样可以产生后发优势,进而建立起与民主运行相适应的社会网络。单一的历史决定论和制度主义虽然各执一端,但都有失偏颇,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能构造出社会网络与民主制度绩效之间的良性循环系统。
二、类型之辨:社会网络的类型与民主制度的绩效
多元的社会网络构成了复杂的社会资本体系,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起着不同的作用。纵向的时间视角和横向的特征视角是剖析社会网络类型的两种重要方法。
(一)社会网络类型的纵向剖析
从纵向的角度分析,社会网络包括传统社会网络和新型社会网络。传统社会网络主要由基于社区的团体和基于教会的团体组成,这些团体构成了传统社会网络的基本形式。伴随社会的发展,新兴的社会网络突破了传统团体的形式,增加了小型团体、社会运动等多种新形式,进而构成当代多元的社会网络系统。
早期的社会网络由传统的志愿社团构成,志愿团体是一种特别的社会设置。英国学者纽顿认为:“它不是诞生于我们的家庭,不是我们无法绕开的国家,也不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赖以谋生的工作。它是我们被卷入其中的所有完全志愿性和协作性活动中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志愿性组织被认为构成了合作性民主文化和结构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7](P431)美国历史上最积极的志愿性组织是19世纪早期的废奴团体和禁酒社团,这些团体对于推动美国社会生活进步以及民主制度发展做出了贡献。后来随着宗教的发展,教会成为影响公民参与的重要机构。从1776年到1980年,美国人中正式的宗教信徒的比例不断提高,从17%一直提高到62%[8](P16)。宗教信徒组成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团体,成为社会资本的最重要宝库。克雷格·麦克莫伦牧师甚至认为:“教会就是人民。教会不是一幢建筑,甚至不是一个机构,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9]宗教团体除了一般的宗教仪式外,直接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包括生态环保、卫生健康、体育娱乐、慈善公益等。坎贝尔指出:“美国人参加宗教活动越多,他们越可能以不同形式参加公益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志愿的社区活动、做慈善活动。经常去礼拜的人不仅投身宗教事业,而且比不经常去礼拜的人更经常献身世俗事业。”[10]帕特南则坚信:“教会是一个重要的孵化室,培训公民技巧和公民规范,培养社区利益,招募和训练社区成员。虔诚的男女在那里学习如何发表演讲,主持会议,调和分歧,担负管理责任。”[11](P63)由此,传统社会网络不但向成员教授政治技能、灌输公共价值,而且营造了一个利他、互助的社会氛围,为制度绩效的提高积累了社会资本。
伴随社会的发展,社会网络出现了新的潮流和趋势,如果说读书会、谈心治疗会、援助会等小规模、私人性、非正式团体悄然弥补着传统的公民参与组织的不足,那么一系列社会运动正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社会网络,并成为公共生活的新形式。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社会运动,从反种族歧视、反越战到2011年表达对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不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各种社会运动不但标志着公民参与政治方式的变化,而且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生产,进而对政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要从两方面分析:就消极意义而言,社会运动是人民广场式的直接参政形式,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制度运行的正常程序,扰乱了社会的日常秩序,给政府施政和民主制度造成了压力,降低了制度绩效;从积极方面来说,可控制范围的社会运动提高了可行的、合法的公民参与水平,对美国社区和公民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社会运动与社会资本相连,不但可以扩展社会网络、创造新的社会资本,而且通过集体抗议强化了参与者的共同身份感,对政府权力起到制约作用,进而提高了制度绩效。总之,社会运动不是传统政治的替代物,而是一种辅助形式,它在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爆发,不但缺乏持续性,而且具有破坏性。因此,只有把社会运动所汇集的社会资本纳入到正常的制度程序之中,才能提高制度绩效。
(二)社会网络类型的横向甄别
从横向角度分析,并非同一时代的每一种社会网络都有助于社会资本的累积和制度绩效的发挥,只有那些自身结构同政府过程的内在逻辑相吻合的社会网络,才能构成民主运转的润滑剂。因此,对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网络类型进行甄别是必要的。
第一,从网络内部的结构来看,社会网络区分为水平网络与垂直网络。水平网络把具有相同地位、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展现出“网状”(Web-like)结构,邻里组织、志愿团体、社区组织和各种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属于这种类型。在水平网络中,人们相互平等、彼此信任、互助合作,产生出有利于民主制度绩效提高的社会资本。而垂直网络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依附关系中,呈现出“柱状”(Maypole-like)形态。帕特南指出:“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太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了,也不太可能被接受。”[4](P205)由此,水平网络构造出相互合作、彼此信任的社会资本,成为提高民主制度绩效的“柔顺剂”;而垂直网络同专制等级结构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苟合,成为降低民主制度绩效的“拦路虎”。endprint
第二,从网络成员的连接强度来看,社会网络可以区分为弱关系型和强关系型。马克·格兰诺维特指出:“连带的强度(可能是线性函数),是‘认识时间的长短,‘相互的频率,‘亲密性(倾诉的内容)及‘互惠性服务内容的组合,这些都具有连带的特色。”[12]弱关系是指人们可以游离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在网络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强关系是那些处于宗教、民族、村落、血缘等传统网络之中的关系,网络成员对内保持紧密的联系,而对外持有排斥的意识。马克·格兰诺维特还指出,弱关系对于网络具有疏离感,被看作个人具有独立意识并且可以在共同体之间流动;强关系虽然产生内部的凝聚力,但最终造成整体的分裂[12]。传统社会通常是零散的,由大量完全相同或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内部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强社会联系。现代社会则由大量相互重叠、具有多重身份和资格的社会团体组成,人们可以在各个团体中自由流动,团体内部保持相对松散的联合,团体之间则相互包容、合作。因此,强关系网络滋长封闭、排外、不宽容的狭隘意识,而弱关系网络产生出相互合作、妥协、彼此平等的社会资本。
第三,从网络成员构成来看,社会网络区分为异质性与同质性。这种区分类型与连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与黏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划分相通。异质性社会网络的成员由不同身份和背景的成员组成,由此能够产生广泛的互惠合作精神。而同质性社会网络中只接纳相同背景的成员,如以宗教为基础的妇女读书会、按照种族区分的兄弟会和以地域为标准的同乡会等,这些社会网络在团体内部秉承着强烈的互惠原则和成员团结精神,对于陌生人则保持警惕。因此,以开放、包容为标志的民主体制更加需要具有广泛兼容性和庞大社会连接能力的异质性社会网络,以便把不同种族、宗教、地域背景的人们包容到网络之中,从而培养起普遍的信任、合作、互惠的公共精神,为民主制度绩效的提高培育社会土壤。
因此,多元的社会网络构造了多元的社会资本类型,而那些具有水平结构、弱关系、包容异质成员的连接性社会网络更加易于人际沟通、相互合作、彼此信任,进而使人们通过情感的凝结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和质量,最终成为提高制度绩效的润滑剂。
三、功能解析:社会网络对制度绩效的双重效应
作为结构型社会资本重要组成要素的社会网络对于培养公民互信、合作、协商的公共精神,制约国家权力,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起着重要作用,其作用方式通过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表现出来。
(一)内部效应:培育公民的学校
社会网络的内部效应首先表现为对市民社会的培育。马克·詹森(Mark Jensen)认为:“繁荣的市民社会培育和维持着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政治架构和政治文化都不能使社会上大部分成员成为好公民,而市民社会却承担着民主学校的功能。”[13](P25)社会网络是公民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在这里学会互助、合作的公共精神,克服个体原子化的倾向,从而为民主运行铺平道路。个体原子化表现为只关心私人生活和家庭利益,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缺乏相互联系的原子化个体催生了一个畸形的社会,人们面临着由文明退化到野蛮的危险境地。第一,个人囿于小圈子之中,缺乏合作和互助精神。渺小的个体淹没在庞大的国家之中,被分割为互不联系的原子化个体,面对强大国家机器的侵犯,原子化个体将束手无策。第二,在原子化的社会中,人际结构表现为单一的个体世界,既无有效联系亦无公共意识的人们无法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第三,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民主的权威需要公民共同授予,民主的运作需要公民协作参与,民主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共同推动,这些都是原子化的个体无法单独完成的。第四,原子化个体无法跨越自由放任带来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
原子化个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你争我夺,在社会网络阙如的状态下难免陷入丛林法则肆虐的动荡状态。面对现代民主所引发的个人主义过度发展趋势,美国人成功地通过“结社的艺术”(Art of Association)化解。托克维尔认为:“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没有权利和志趣为政治目的而结社,那么,他们的财富和知识虽然可以长期保全,但他们的独立却要遭到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14](P697)与美国相比,大革命时期,法国的个人主义更彻底,但由于缺乏社群传统而陷入危机之中。托克维尔写道:“在彼此一致的人群中,还竖立着无数小障碍物,将人群分割成许许多多部分,而在每个部分的小围墙内,又似乎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它只顾自身利益,不参与全体的生活。”[15](P116)由此可见,具有社群传统和完善社会网络的美国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政治的转型;而过度个人主义且缺乏结社互助精神的近代法国,陷入了旧制度的崩溃与大革命的风暴之中。历史与现实再次证明,社会网络是防止个体原子化的有效手段,是培养民主精神、塑造公民人格的学校。
(二)外部效应:对行政集权的制约
社会网络的外部效应表现为对行政集权的制约。行政集权是降低民主制度绩效的巨大威胁,它不但损害了民主的价值观念,而且带来专制主义的危险。然而,行政集权是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首先,现代民主采取代议制的形式,国家权力由公民委托代议机构履行,这就为行政集权创造了条件。当行政权力脱离人民被政治精英掌握后,权力进入“黑箱”之中,精英有机会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蒙蔽、欺骗人民甚至公然违背人民的意愿。其次,现代政治经济的复杂性对于行政权力的操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把权力集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和政治经验的职业政治家手中,以便能够做出具有远见的政治决策。再次,现代行政体制中复杂的官僚层级结构带来行政集权化倾向。因为行政系统的最高目标是效率,而自上而下的集权体系是充分发挥行政效率的最好方式。最后,行政体系内部的既得利益者凭借行政集权获得更大的利益。如米歇尔斯所言:“现代国家的自保本能使其为自身创造了最大限度的既得利益……通过设立庞大的官僚职位等级,制造大量直接依赖国家养家糊口的人,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确保人们对国家的支持。”[16](P157158)官僚体系是行政权力的直接掌握者,他们通过尽可能地把权力集中于行政内部而获得安全保证和利益回报。这样,行政集权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重大威胁。endprint
然而,社会网络为行政集权设置了一道屏障。首先,密集的社会网络是公民社会产生的原因,而公民社会是抵御行政集权、保障自由民主制度运行的必要条件。如盖尔纳所言,民主国家是“公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任何国家或宗教组织试图垄断权力或强迫信仰。在国家和家庭之间有无数的组织,从工会到集邮俱乐部,从学生组织到教堂和保龄球俱乐部,这些构成了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民主[17](P225)。公民社会培育了人们追求自由、反抗专制的精神,从而使个人抵制行政集权对个人自由的干涉,有效地维持民主的正常运行。其次,社会网络保证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培养了公民参与的习惯,进而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行政集权的成因之一在于缺乏公民的监督,而公民监督的最有力方式是参与到行政过程之中。社会网络培育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培训了公民的参与能力和技巧,进而为制约行政权力,保证行政过程公开、透明、公正进行提供条件。再次,社会网络还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制衡的舆论环境。在这里,人们阐述、传播非正式的、理性的、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制造舆论声势和民意氛围,进而影响政府运作。社会网络客观地制约了行政集权所带来的话语垄断和舆论专断,行政者必须顾及公共舆论的影响和下一届选举公民的投票倾向。最后,各种社会团体通过院外活动、发动社会运动对政治产生影响,进而制约行政权力,避免行政集权。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是渺小的,但由个人组成的分子化的社会网络的力量却是巨大的。人们之间组织起来、相互声援、协同合作,通过院外活动、示威游行、抗议活动等不时刺激由于行政集权而过度僵化和反应迟钝的政治制度,进而提高制度绩效。
参考文献:
[1]Robert D. Putnam.Democracies in Flux: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Pierre Bourdieu.Le Capital Social [J].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0,(31).
[3]James S.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Supplemen,1988,(94).
[4][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Bo Rothstein , Dietlind Stolle.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reate and Destroy Social Capital: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Generalized Trust[C].Paper Prepared for the 98th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 Boston,MA, August 29September 2,2002.
[6][英]乔沃·利斯,布莱恩·多莱里.地方政府能力与社会资本[M]//周红云.社会资本与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英]肯尼思·纽顿.政治信任与政治疏离:社会资本与民主[M]//周红云.社会资本与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Roger Finke,Rodney Stark.The Churching of America,17761990:Winners and Losers in Our Religious Economy[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2.
[9]Sara Terry.Resurrecting Hope[J].The Boston Globe Magazine,1994,(17).
[10]David E.Campbell.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3,(16).
[11][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2]Mark S.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6).
[13]Mark Jensen.Civil Society in Liberal Democracy[M].Routledg,2011.
[1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6][意]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17]Ernest Gellner.Coditions of Liberty: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M]. Penguin Books,199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