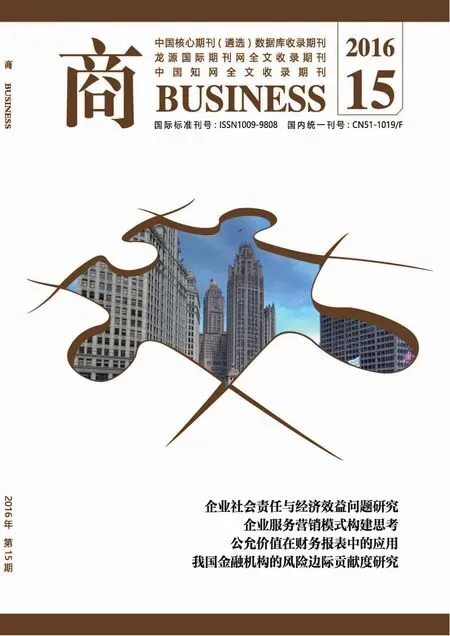边疆治理视角下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认同整合
2015-10-21袁青欢刘华夏
袁青欢 刘华夏
摘 要: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在边疆治理体系中居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由于该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际关系相交织、国家认同面临种种挑战,认同整合任重而道远,需要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跨境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强化区域主义的治理方式四个方面入手进行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认同整合路径建构。
关键词:跨境民族地区;认同整合;边疆治理
边疆是政治、文化与地理空间体(国家)的边缘地带,经常两个或多个国家的边缘、边界交接之处。边疆的“边缘性”主要来源于资源竞争与匮乏,它或因政治强权间的资源竞争与分界而成为边疆,更常因资源匮乏而成为边疆。①我国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边疆治理的成效影响着政权合法性建设。
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即调整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确保国家认同处于优先地位的过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属于政治文化范畴,认同整合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具有重要意义。云南是我国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研究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认同整合有较大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在边疆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一)地理位置敏感而重要
云南省有25个边境县(市)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有16个跨境民族。其中,中缅边界长1997 公里,境内为我国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六个州市的十九个沿边县市,境外为缅甸克钦邦和掸邦;中老边界长710 公里,境内为我国西双版纳勐腊县、普洱市江城县,境外为老挝南塔、乌多姆赛、丰沙里三省;中越边界(云南段)长1353 公里,境内为我国江城、绿春、金平、河口、马关、麻栗坡、富宁七县,境外为越南莱州、老街、河江三省。在这国境线上,跨国居住着苗、瑶、壮、傣等十六个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
跨境民族地区是边疆地域中较为特殊的组成部分,国家边缘地带的最外围,中国与邻国的连接地带,该地区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抵御国外敌对势力渗透的首要堡垒。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云南跨境民族地区重要性更加凸显,确保和维护该地区的安全是我国边疆治理的题中之义。
(二)民族构成多元、民族关系复杂
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在民族成分上极为特殊,其主要民族是跨境而居,同时在其行政辖区内同时居住和生活着我国的其他民族,民族构成多元,民族关系错综复杂,至少包括三类民族关系:跨境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跨境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跨境民族国内成员与国外成员的关系。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出现问题,将意味着国家的边疆不稳,势必影响全局。
二、云南跨境民族地区认同整合任重道远
根据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的理论,政治角色扮演者的国家认同意识是观测和衡量政治体系文化的一个核心指标,如果政治个体对于次级政治单位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出现矛盾和冲突,那么将对国家的完整和安全带来挑战,甚至会导致地方分裂主义运动。尤其当该政治个体所属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与国家主体部分存在较大差异时,离心倾向会呈上升趋势。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罕见,例如英国苏格兰地区、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离运动。
(一)民族认同与国际关系交织
民族的界定是根据语言、信仰、风俗等,“同者虽分而必趋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其同异,非一时可泯也。”②跨境民族通常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由于近现代的划界政策使一个民族一分为二,分居两国,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自然村的村民被划分为不同国籍。因此,历史渊源导致了跨境民族与境外的本民族成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境外民族中有不少人是跨境民族成员的故交、朋友、亲戚乃至家人。民族跨境而居,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指向的对象不仅仅在一国范围内,涉及到国际因素,如果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矛盾,影响与邻国关系,对边疆治理的危害更大。
(二)国家认同面临挑战
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地处边疆,民族成分多元、民族关系复杂,再加之历史因素、经济落后、基础公共服务政策差异以及境外势力影响,对该地区的国家认同形成巨大的挑战。
第一,历史遗留问题。边疆划界是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活动结果,跨境而居的民族一定程度上是被人为划定而分属不同国家,长期聚居共同生活的历史导致了部分跨境民族成员对民族的认同较为强烈,而对国家的认同较弱。
第二,经济发展滞后。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处于祖国的西南边疆,多为高原山區,交通不便,其中还有一些地区长期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与内陆地区巨大的经济落差,容易造成跨境民族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会损害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第三,基础公共服务政策的差异性。在云南边疆跨境民族地区,有一些基础公共服务政策是针对某一个民族的成员,其他民族享受不到,易加剧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民族之间差异,加深民族成员在心理上对本民族的认同,而弱化和冲击对国家的认同。
第四,境外势力影响。周边一些国家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跨境民族地区的学生到其境内接受教育,而学校是传播政治文化、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这些学生接受他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将削弱他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时还有一些敌对势力通过宗教传播等形式拉拢人心。
三、云南跨境民族地区认同整合路径建设
(一)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项战略任务。“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③一方面,建设各族共有、共享、共建精神家园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构建共有精神家园,能够让各族人民加强对国家的信任感、归属感、认同感,同时加强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稳定。
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应当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进行中华民族的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又承认各个民族的多元,是我国历史长期发展的趋势;二是进行共有精神家园内涵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对命运共同体、共同文化根基、时代精神、价值目标、建构途径等做了探讨和解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实现跨境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则带来动乱”,渴望发展、渴望改变贫穷的现状会增加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初在云南考察时指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现在距离2020年只有五年时间,民族地区必须“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应该以三个方面为抓手:
第一,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应当抓住当前的四个机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机遇、编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机遇、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第二,结合和利用自身的四大优势,后发优势、资源优势、特色文化优势和生态优势;第三,突破制约瓶颈、弥补自身短板,推进基础交通设施建设,连通西南边疆的交通网络,攻克跨境民族地区扶贫难题。
(三)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异,促进跨境民族地区民生改善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到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在教育、扶贫、交通、饮水、用电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指标。云南跨境民族地区民生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与全国落差较大,这种差距影响到该地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要改善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民生状况,首先要促进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教育事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关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工作者的权益,缩小云南跨境民族地区与全国的教育差距,在教育中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的认同整合;其次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解决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针对语言不通无法进行救治等情况,应该建设和培训精通民族语言的当地医护人员队伍,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来人才的流失难题;最后是促进当地就业,国家在加大对民族地区投资建设的同时,应当有倾向性地扩大当地劳动力的录用比例,在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帮助改善民生问题。
(四)强化区域主义的治理方式,从导向上淡化民族差异意识
西方自由主义学派进行的研究表明,出于保护和帮助的善意出发,对特殊的族群或民族群体,给与长久的政治认同或宪法地位,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人们的群体差异意识更加强烈了,对其他群体的憎恨更加突出了。人为地强化人们的族群意识,易于带来增强边疆民族地区的离心力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国家不遗余力出台了很多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民族地区取得了巨大进步。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中、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而不是民族之间的差异。任何政策都是在不断地反馈和调整之中走向完善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需要对政策进行一定的调适,因此,边疆治理政策应当由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在对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治理中,应当注意淡化民族差异,尽量减少制定针对某一民族的优惠政策,多出台促进区域发展、弥补地区间差异的公共政策。
认同整合是边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云南跨境民族地区的认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敏感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更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加强该地区的认同整合、确保国家认同居于主导地位的认同关系,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解:
① 王明珂,建“民族”易,造“國民”难——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J],文化纵横,2014,3
②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七页。
③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