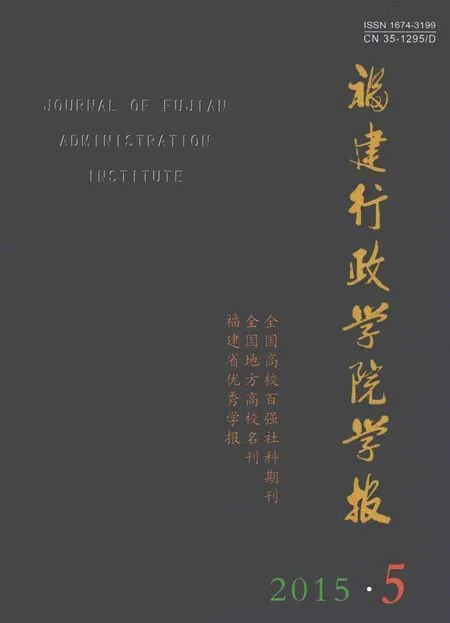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合作失灵及其矫正
2015-10-16姜庆志
姜庆志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1)
公共行政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合作失灵及其矫正
姜庆志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1)
伴随着我国社会治理中合作实践的深入,合作失灵的现象日益频发,加剧了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的难度和风险,不利于社会共治的实现。合作失灵具有复杂的生成逻辑,基于合作三要素框架诊断发现的主要诱因有:合作环境中公共事务的叠加与社会信任的缺失、合作主体有限理性的桎梏与治理能力的失衡、合作网络的规则缺失与内在价值困境。矫正社会治理中合作失灵的途径有:提高合作网络与环境的契合度,培育合作文化;明确合作主体的网络位置,增强其治理能力;提升合作网络的制度化水平,推动合作主体的共同学习。
社会治理;合作治理;合作失灵
我国社会事务复杂性和非线性的增强,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要求公共管理者与其他治理主体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1]就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而言,区域性组织的广泛增加、跨部门合作行为的增长、公民参与和公私合作范围的扩大,证明了社会治理中广泛存在着合作现象。然而,从实际绩效来看,并非所有的合作都是有效的。有学者对大量案例进行梳理和诊断后发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项目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等社会事务治理中,我国广泛存在着合作失灵的现象,不乏部门主义、“搭便车”等策略性行为。[2]合作失灵的频发易使公众认为“合作是空中楼阁”,甚至引致公众对合作理念本身的质疑,使之不自觉地“回归”传统的权威主义。鉴于此,我们要正确看待合作在社会治理变革中的作用与限度,既不将其看为“包治百病”的灵药,又不因合作实践中的困境而加以否定。同时,要探明合作失灵的生成逻辑和应对之策,以科学的态度引导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一、社会治理中合作失灵现象的考察
在社会治理的语境下,合作失灵是指由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组成的多中心行动体系在社会治理中未能带来公共价值的净增长,即合作网络中的联合行动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零效应或负面效应。合作失灵现象存在于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合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作为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逻辑的替代性方案,合作治理虽被寄予了“化解公共事务治理悲剧”的厚望,但未能充分地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福利、实现帕累托最优。二是合作达到了预期目的,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即合作网络运行所需要的公共资源大于其带来的公共价值,社会治理体制陷入低效运行的困厄之境,导致公共物品供给过剩和生产成本的增加。三是合作在关键领域作用有限。合作具有作用半径,并非任何社会治理问题都可以通过合作治理解决,在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一些“具有急迫性需要独权专断”的例外事件时,合作治理往往难以奏效。四是合作带来了负面效应。合作治理机制建立在党委、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共享权力、分担责任的基础上,这容易带来公私界限模糊、责任不清、治理主体使命感降低等问题,最终影响社会治理的能力和绩效。
合作失灵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病态”,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权力主体多元化的角度出发,合作治理的本质在于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其他社会组织与政府具有平等的治理地位[3],这也就意味着公共权力配置、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和社会运行秩序的调整,以及治理主体间自由、平等和互惠的伙伴关系与合作能力的重构。从这种意义上讲,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构建和运行的过程很难完全避开失灵的陷阱。合作失灵的常态化趋势使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陷入两种困境:一方面,合作失灵引致了资源浪费和责任缺失问题,容易诱发行政伦理缺失和政府缺位等问题,加剧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难度和风险;另一方面,合作失灵使得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冲突化解缺乏必要的网络支持,合作共识和合作能力无法得到形塑和累积,阻碍多元主体交互共治模式的构建。因而,如何规避合作失灵的风险,真正实现社会合作共治是合作治理研究中亟待探讨的一个问题。
二、社会治理中合作失灵的生成逻辑
合作失灵的诱因是复杂的,既有治理主体间理性冲突所造成的合作动机消减,又有制度缺失或权责不清带来的合作能力下降。学界从理性经济人、资源依赖、成本收益等视角对这些诱因进行了解读,但显得不够系统。为了更为系统地进行梳理,本文的诊断框架建立在合作治理三要素的基础上,即从合作环境、合作主体和合作网络三个维度审视合作失灵的生成逻辑。
(一)合作环境维:公共事务的叠加与社会信任的缺失
1.公共事务叠加的刺激。合作只是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选择,在市场和政府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合作也可能无能为力,也即合作网络无法调动充足的资源应对不断变化的合作环境。作为现代化“迟—外发”型国家,转型使得社会和政治的异质性逐渐增加,治理者需要应对社会流动加速、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交织等诸多问题的冲击,合作治理的外部约束不断增强。同时,转型催生了大量跨界性、非线性、复合性的公共问题,合作被寄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改善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消除贪污腐败、推动环境保护、平衡地区差异等各种厚望,在增加合作诉求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提出了新挑战。此外,原本固化的社会结构不断分异、多元利益主体格局基本形成、利益糅合和冲突化解的难度不断提升等情况的出现意味着合作网络的有效运行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合作不仅很难有效化解社会需求,反而有可能因不堪重负而崩溃。
2.社会信任缺失的影响。信任是合作网络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它形塑了治理主体的合作共识和合作模式,有助于化解合作者的利益冲突、规范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合作者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趋向一致。然而,转型期中的“否定性冲动”使传统价值体系和群体共有伦理失落,社会逐渐呈现出“陌生化”“利益化”“冷漠化”等特征。伴随着社会成员相互间期望和信任的下降,各种“负能量”快速凝集、传播并渗入社会治理体系。合作赖以生存的契约精神、法治精神和志愿精神的缺失,使得合作活动缺少社会响应和认同,这使其陷入到合法性危机之中,削弱了合作治理的信任基础和实际运行效果。
(二)合作主体维:有限理性的桎梏与治理能力的失衡
1.合作主体有限理性的桎梏。实现合作的过程之中,治理主体在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上必然具有一致性或相似性,且相互间有清晰的责权认定。但合作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社会利益格局复杂化和彼此之间的信任度降低的情况下,合作者即便认识到合作的价值,仍会倾向于选择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策略,这会引致合作者相互推诿、转嫁责任的风险。一是合作主体的投机风险。在特定的合作网络中,合作收益具有公共性,即网络中每个成员都能够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投入了精力。资源共享的这种性质促使合作者产生“搭便车”的投机心理,合作网络越大,“搭便车”的行为就越多。有研究者指出:合作“既有让私方利用国家资源谋求私利的危险,也有政府出于国家的或执政党的利益把手伸到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中的危险。”[4]合作主体的投机行为,不仅提高了合作网络的运行成本,也降低了每个合作者分享的份额,最终会将合作推向失败。二是合作主体的脱网风险。虽然市场和社会中组织层面对国家的依附性仍然较强,但个体的解放使微观行动世界中的“无序”行为增多。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与组织依附关系减低的个体便很容易离开合作网络,甚至与原有的网络发生冲突。当彼此间利益与目标发生持续冲突时,合作便容易转入对抗性的非均衡博弈状态,导致社会治理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无法达成合作共惠的行动策略。
2.合作主体间治理能力的失衡。合作的前提是平等,这意味着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新中国建立之后的较长时间内,党和国家一直处于公共事务管理的垄断地位,“包揽式”的管理方式拒斥了治理主体间联系日益增强的事实。受路径依赖的影响,时至今日,市场和社会力量仍表现出对国家权威的依附性和相对的脆弱性,活动空间和自主权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和拓展。我国提出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但这一过程因是传统权威的自我解构而打上“行政主导”的烙印。作为一种机制,合作超越了控制和命令,因而行政命令式的合作或许有更高的行动力,但逻辑起点的偏差却限制了合作的未来。同时,我国目前社会治理中的合作更多是政府向社会让权、赋权的过程,受到组织化程度不高、自身权威缺失、追求特殊利益、活动狭隘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治理主体化解资源约束、整合资源的能力不强,难以承接繁重的社会公共事务,这一情况的存在增加了合作治理失败的风险。
(三)合作网络维:规则缺失与内在价值困境
1.合作网络规则的缺失。网络规则缺乏的地方,合作预期的实现也缺乏保障。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释放了我国的“体制红利”,大量有关合作的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建立起来,但新旧体制之间依旧存在摩擦和能耗,在责任划分、权力保障、资源整合、行为监督等关键领域,合作网络都体现出规则数量不足和适应性不强的特点,这是合作网络难以回应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内部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已有的合作规则多由随意性较强的“土政策”构成,规定笼统、抽象、模糊,在社会治理的具体层面上缺乏操作性。同时,合作规则多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往往体现的是某一行政机关的意志与目标,这使合作活动不可避免地复制了“官本位”和“部门主义”的特质,破坏了治理主体间合作的统一性、完整性和稳定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制度的缺失加剧了社会对传统权威的依赖,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的合作也因此体现出浓厚的人治色彩,而人治又掣肘了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的进程,将合作带入“规范缺失→依赖人治→规范破坏→人治加强”的恶性循环。
2.合作网络的内在价值困境。一些研究者将主体间的冲突视为合作的内在价值困境,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合作网络并不排斥主体间的利益分歧,其真正的价值困境是随着合作活动的深入,合作网络出现了一系列的两难选择。一是主体力量均衡与网络集成之间的矛盾。许多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发现,群体成员间的不平等程度与合作效果呈现负相关。[5]伴随着合作网络的成熟,合作主体间权力的均衡程度会越来越高,但权力的多中心又容易降低合作网络资源的聚合度,增加提取公共利益和管理网络的难度。二是网络稳定性与开放性之间的矛盾。成熟的合作网络要求有一定的封闭性以保持合作关系的稳定,但这也容易导致“排斥圈外人”情况的发生,一些潜在的合作成员和资源难以进入合作网络,损失了新的合作机会。三是合作制度化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合作网络的制度化要求合作成员遵守共同的规则并形成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但制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保守并产生惰性,关系的固化更容易引发革新动力的衰减,这给合作网络的运行会带来官僚化的风险,容易出现繁文缛节、僵化低效的弊端。[6]
三、社会治理中合作失灵的矫正之策
矫正社会治理中的合作失灵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多种因素相互整合、协同发力的结果,既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又有赖于合作主体治理能力及合作网络功能的优化。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高合作网络与环境的契合度,培育合作文化
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只会伴随社会转型的深入而不断提升,因而必须提升合作网络与环境的契合度,使其所承担的职能与其作用半径相一致。一方面,合作要建立在对社会现状和发展趋势准确研判的基础上,并树立依据公共需求构建合作网络的问题意识。要厘清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动、科学技术进步、社会价值观更迭等因素对社会治理体系的作用方式和程度,通过合作网络实现物质、信息和能量的整合,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控制在可处置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明确合作网络的作用限度,构建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网络,发挥其最大边际效应。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实现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自主治理多种治理逻辑的糅合,然后根据具体社会公共事务的特质,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就目前社会治理的现状来看,合作更容易在公共需求多样化、区域化,共识程度高、需要多个行动者的领域发挥作用,譬如公共安全、大气污染治理、贫困治理等。此外,社会转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市场经济完善、生产关系调整、社会结构多样、个体意识觉醒、信息技术发展等因素释放了蕴藏已久的社会能量,为合作提供了基础、动力和可能。矫正合作失灵,必须挖掘社会变迁和结构调整中蕴含的“正能量”,将转型挑战引导为发展动力。
合作文化是合作失灵最好的修复剂,它能消除因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不信任,增强合作治理的社会认同。一方面,要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将法治、平等、公平、诚实、互信、互助等理念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消除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现代性危机”,为社会治理中合作的实现提供一个社会资本丰富的场域。在这样一个场域中,合作活动以“公民共同体”为理想标的,也即公民以团结、信任和宽容为参与原则,以互惠原则上的政治平等为基础,实现的是“有远见的”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7]另一方面,培育务实的合作文化,消除合作治理是“空中楼阁”的错误认识。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大背景下,不少地方将合作视为响应上级要求而采取的“应景”行动,综合治理变味成“挂牌”行动,许多新开展的合作有名无实,加剧了公民对合作治理的误解。因而,合作活动一定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政府官员一定要站在“目的支配结构而非结构支配目的”[8]的立场,从“创造政绩”走向“创造价值”。
(二)明确合作主体的网络位置,增强其治理能力
要想避免社会治理中的合作因利益冲突而失败这一情况的出现,就必须厘定各治理主体的“生态位”,明确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实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系统联动。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在一元单向模式转向多元交互模式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必须“还权”于市场和社会,改变社会组织“行政化”的弊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其角色定位应从公共资源的垄断者转向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者、制度环境的创造者、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会治理的协调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以及社会力量的培育者。当然,社会公共事务合作治理并非政府在“卸包袱”,在合作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政府责任市场化”“政府责任社会化”倾向,要在划定政府职能边界的基础上思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从微观层面看,在具体的合作活动中应当建立合理的有限责任机制和必要的公共伦理规范,利用规则抑制治理主体各自的内在弊端和矛盾冲突,在明晰职责权限的基础上实现党和政府领导和多元主体参与的有机互补,将不同的作用力量和治理逻辑糅合在“合作”的框架下,缓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摩擦,破除合作治理主体有限理性的桎梏。
提升治理主体的行动能力。合作失灵的矫正有赖于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散发出强而持久的能量并形成能量增殖的系统效应。其一,合作的有效运行并非以削弱国家能力为前提,党和政府作为关键治理主体依然是合作有效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党和政府应当提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掌舵”能力,增强在日益纷杂、边界模糊的公共问题中提取公共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使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能够实现制度化的整合,减少合作的能量内耗。同时,加强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综合提升组织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监督能力、学习能力和廉政水平,推进公务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增强公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其二,积极培育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释放是国家权威强力干预的产物。在市场和社会治理主体参与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国家既要为其独立活动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和制度保障,又要对治理主体的能力缺陷、相互间矛盾冲突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以锻炼其依法、有序、有效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最终实现市场和社会力量的自觉建构。此外,还应处理好实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引入工商管理技术、社会化工具、多中心网络化治理工具等创新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将“体制红利”“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转化为社会合作主体的参与能力。
(三)提升合作网络的制度化水平,推动合作主体的共同学习
矫正合作失灵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提升合作网络的制度化水平来降低和节约公共事务治理的成本,以最小的能耗使社会治理达到“善治”状态。一方面,破除阻碍合作治理开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提高制度的完备性和科学性。合作制度的修缮与创新应当覆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从“被动式”改革转向“自觉式”建构,实现“摸着石头过河”和“局部试点”的合作经验制度化、可推广化,保证各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有制度可依。需要注意的是,合作网络制度的创新应从根本上体现人民意志和人民主体地位,反映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与趋向,注重理念更新与制度改革的匹配、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改革的协调统一,避免简单复制、空泛乏力、各自为政的形式创新。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入,不少领域的合作活动已构建了基本的原则,当前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一系列细则使这些原则“落地”,让合作在运转中发挥应有的效力。具体而言,应当以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提升合作网络的沟通力,以改进公共财政体制、监督问责机制、职权配置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强化政府执行力,以健全反馈调解机制、制度评估机制提高合作网络的保障力。
破解合作网络两难困境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学习机制来保持网络的动态平衡和适度张力,原因在于:网络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动者共同学习的产物。[9]一方面,治理主体要通过权变的策略来化解合作网络的内部矛盾,学会利用协商与谈判来改善合作关系。尤其是合作网络陷入僵化状态时,政府等关键治理主体要能提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必要的时候可在共同商讨的基础上利用结构重组、制度重建等方式来改变网络运行的方式,重新配置网络管理权和塑造网络文化,保证合作网络在稳定性与开放性、制度化与灵活性间不失偏颇。另一方面,共同学习源于合作治理的实践经验。当合作成功时,治理主体的旨趣便会从狭小的利益转向对公共利益的广泛关注,主体间的信任、合作的熟练度和价值的一致性都会得到提升,从而使治理更高阶社会问题成为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行动第一”是破解合作网络两难困境的终极出路,因而,社会治理中应当大力提倡和推动合作实践,使之摆脱“经院哲学”的印象。合作治理是一个反复进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验的累积会使合作网络跳出失灵的窠臼。
四、结 语
就治理变革而言,任何一个特定的治理模式都必须考虑到与之相适应的背景。正如盖伊·彼得斯所言:政府改革的复杂性迫使我们趋向于采取情景治疗法,即使在受到一套相当有说服力的理论引导时也是如此。[10]作为社会治理体系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合作失灵是环境、主体和网络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其矫正之策也应当根植于这些特定社会背景,并回应公共事务复杂性与合作文化缺失、合作主体的策略行为与治理能力的失衡、合作网络的规则缺失及价值困境等诸多问题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合作不是万能的,社会治理也并非只有这一种政策方案选择。实践者要在理论的喧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合作能力与合作需求动态平衡的理念,用务实和权变的思维去推动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总之,合作失灵有可能会伴随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深入而不断凸显,矫正合作失灵也必然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周志忍,蒋敏娟.中国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一个叙事与诊断框架[J].公共行政评论,2013(1).
[3] 侯琦,魏子扬.合作治理——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1).
[4] [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
[5] 韦倩.影响群体合作的因素:实验和跳页调查的最新证据[J].经济学家,2009(11).
[6][9] 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6、85.
[7] [美]罗伯特·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 [美]尤金·巴达赫.跨部门合作[M].周志忍,张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 [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明,夏宏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王少泉]
Collaboration Failure and its Adjustment in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JIANG Qing-zh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Hubei, 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aboration practice in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collaboration failure takes place frequently. Such phenomenon makes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more difficult and perilous, which is not good for our social multi-governance. Collaboration failure has a complicated creation logic. With the frame of three collaboration elements, we find that superimposed public affairs and the lack of social trust in collaboration environment,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restriction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mbalance of collaborative agents, and lost rule and intrinsic value dilemma in collaboration network may result in Collaboration failure. To adjust them, we should make collaboration network fit neatly into its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e collaboration culture, clearly locate the network position of agents and enhance their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llaboration network and co-learning of collaboration agents.
social governance,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collaboration failure
2015-09-1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662015QD032)
姜庆志(1987-),男,山东泰安人,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D035
A
1674-3199(2015)05-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