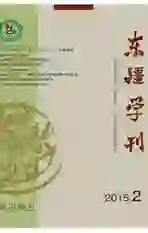古代韩民族的原始意识结构
2015-10-15潘畅和姜云
潘畅和+姜++云
[摘要] 韩民族有其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风流”。与中国文化中的“兴”立足于伦理本位、追求“大同”的精神不同,韩民族的“兴”与“风流”根植于生命本体,追求重生精神,进而使“兴”与“风流”直接与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相联系并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韩民族先民具有的自然原始性、巫术性的歌舞形式,在游戏的文化功能中,形成了“兴”与“风流”的文化特性,而其全员参与性、与“神”的沟通性和规范的游乐性则构成韩民族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 韩民族;兴;风流;原始意识结构
[中图分类号]B312.6: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2-0001-05
一
和其它民族一样,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韩民族也已经开始萌发关于超自然界的朦胧观念。韩民族特别珍视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并把它们作为崇拜对象,将女性的生殖能力看得很神奇并加以崇拜等现象就可谓是最初的、朦胧的宗教实践及其产物。据《朝鲜简史》记载,在朝鲜清津市农浦里遗址发现了飞禽、狗头等雕塑品,而且还有人像雕塑品,从其雕塑品的细腰宽臀中可以看出是女人形象;在朝鲜雄基郡西浦项遗址出土了用兽骨和鹿角雕刻的象征女人的雕塑品。这些都是在早期社会人们对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自我关联再思的产物,是在直接的、物质的实用目的之外的虚幻观念下产生的。人们在早期的生活实践中,把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朦胧地看成是“活”的而加以神秘化。这些拜物现象、女性崇拜意识是早期宗教实践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任何民族的早期宗教实践中都可以找到。而在朝鲜半岛中常见的支石、立石等巨石文化现象也可谓是韩民族原始宗教现象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据学者对古墓制的考察,大致推测韩国先史时代的葬法中最普遍的是土葬和土葬中一种的窟葬。这些土葬、窟葬中的葬法大部分是将尸体伸展开来埋葬的伸展葬和将死者的头置于东、脚朝西摆放的东枕葬。又据《朝鲜简史》记载,到了青铜器时代,墓葬法出现了与前期不同的用巨石构筑的坟墓。这些巨石墓中有支石墓、石箱坟、土矿墓等。其中支石墓尤为著名。支石墓形式上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将一人多高的宽大板石竖为两面或三面、四面,上面盖上大岩石;另一种是用扁石在地面并成箱型或砌成井型,然后在其上盖厚大岩石,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异。这种支石墓是韩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主要墓葬形式。在支石墓中,黄海北道滩郡五德里和黄海南道殷栗郡冠山里的支石墓又最为有名。那里的支石墓有的甚至在上面盖上了长八点五米、宽六米多、重三十至四十吨的大石板。那么,为什么在韩国原始社会末期的宗教文化现象中与死相关的巨石葬特别突出,且支石墓成为主要葬式呢?这可能是因为在韩民族的幽灵观念形成的比较早或对死亡的态度在早期宗教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种观念与后来的祖先崇拜发生了某种直接的联系。
约·阿·克雷维列夫认为:“人起源于动物或植物,这种想法就其本身来说,还没有任何宗教的东西。但在这里,这种想法与关于一切东西可以变来变去、关于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和超自然的联系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观念,相信这种联系的人,按照他的意见,要同自己的图腾建立友好的关系。由于意识到自己与它有联系,所以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检点自己的起居和行为(饮食和其它方面的清规戒律)。所以这一切已经使这种意识和行为具有宗教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特别突出墓葬是因为将活人与死人联系了起来,认为活人与死者有联系,而这种联系最初并不是令人愉悦的联系,反倒是令人惧怕的联系。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是古人,也能发现死尸与活人相比是可怕的存在。因为死或是老死、病死,或是意外的死,都会是尸骨冰冷,面相难看和可怕。那么古人会如何对待死人呢?肯定不希望这个令人可怕的死尸蹦来蹦去、追随自己,而是希望这个可怕的东西恒定在那里不动。所以他要用巨石做墓穴,把他关到巨石墓中。再者,古人通过做梦等现象的启发,想象到人身上除了看得见的肉体实体以外,还有看不见的幽灵,这个幽灵并不因人死而消逝,而是继续依附在死者身上或转移到一定的地方,并根据与活人的关系随时回来。所以活人要极尽诚意地安顿这个幽灵为其承担责任、做点事。因此他要用巨石做坟墓。因为在生产工具不发达的早期,最现成的也是成本最高的可能就是搬运巨石,所以他要用巨石做墓葬以尽自己的责任。通过这种责任与“死者建立友好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紧密和松散是由死者生前与活人的关系程度而决定的。如黄海道的墓葬有大到用几十吨大板石加盖的巨石墓,可能是埋葬生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人,例如年长者或氏族首领等。他们在生前所居的高位不能不影响到死后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从中也就逐渐衍化出后来的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而且对人们用巨石埋葬死者还可以解读为不只是活人对死者的责任,而且也是给死者以义务。这种关联都是“按照相互原则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真正的联盟,每方都必须本着诚意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背弃这些责任就要受到惩治,而这种惩治涉及双方”。从朝鲜古代比较完整的巨石墓葬现象,我们可以推知韩民族先民的宗教观念形成得较早且较成熟。
二
古代韩民族是具有完整和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由于与中国大陆接壤,中国又是一个具有博大精深的高势能文化的文明古国,朝鲜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具有完备理论形式的儒释道文化的传人,使韩民族可以用中国创造的现成的理性价值资源填充自己的精神世界。诸如,古代韩国至15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古代韩国的知识分子至20世纪初还用汉字而不是韩文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如此,古代韩国人并没有成为中国人,古代韩民族俨然是与中国人不同的具有自己文化个性的民族。那么,在儒释道文化几乎覆盖了古代韩国文化的情况下,到底是哪些固有的土著思想基底使古代韩民族在接受儒释道文化后不仅没有失去古代韩民族的本质特色,而且还使儒释道按照自己的文化要求发生变形,从而使古代韩民族最终仍保持韩国人的本色呢?笔者认为,在上述的宗教观念基础上发展的巫俗作为古代韩民族固有的文化风俗,为古代韩民族没有失去自我成为别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往的很多研究都以统一新罗时期崔致远(857-?)的鸾郎碑序文为例证,认为韩国的固有思想是风流道。迄今为止的不少研究也认为崔致远所说的风流道就是儒释道三教的和合。但问题是如果这样界定风流道,那么就很难解释崔致远的“国有玄妙之道,日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这一首句。可以说崔致远的“国有玄妙之道”一说是韩民族对自己民族思想进行理论概括的最初尝试。因此它必然是对以前所有意识的整体概括。也许在结果上并不一定如此,但在动机上起码应该是这样,所以崔致远所说的“国有玄妙之道,日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正是对千百年来在韩国国人中口口相传、心心相印的固有思想的总体概括。而“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以下,则是已具理论形态的儒释道覆盖着的尚不具有理论形态或理论形态还很模糊的“风流”思想,这使得固有的“风流”思想被遮蔽在界限并不鲜明的儒释道三教整体之中,最终“实乃包含三教”就成为“风流”的脚注。其实,“玄妙之道”的“风流”与“实乃包含三教”的“风流”应该是不同的“风流”。“玄妙之道”的“风流”应该是还没有包含儒释道三教的韩国固有的思想原型,而“实乃包含三教”的“风流”应该是在韩国固有的思想基础上包含界限模糊的儒释道三教整体的意识结构,统一新罗时期的花郎道的思想内核——风流道就应该属于后者,即以传统的风流思想为基础的儒释道整体和合的意识结构。
那么,作为韩国固有思想原型的“风流”应该是怎样的意识结构呢?对此,我们要从韩民族最初的生存形式去解读。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史学是最辉煌的一部分。梁启超先生就曾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所以要想了解韩国先民最初的生存样式,还必须到中国古籍中去寻找答案。因为古代中国,不仅对自己的历史,而且对周边国家也都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记录。《后汉书·东夷列传》(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记载:“王制(礼记篇名)云‘东方日夷,……盖日之所出也。……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夏朝时,夷人“献其舞乐”,“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其“俗喜饮酒鼓瑟”。
从上述对“东夷”国俗风土的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东夷”的最大特点是“喜群聚饮酒歌舞”。那么,这个特点与韩国固有思想原型的“风流”是什么关系呢?东夷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最初应是泛指中原以东的诸多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的变迁中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濊貊族是东夷的重要一支,且是韩国先民的最大根干,这已成为学界的普遍认识。而濊貊族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因此,朝鲜先民的始源应是游牧狩猎文化,农业文化到后来才逐渐占据显要地位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替代了前者。不过,虽然游猎文化完全被农业文化所取代,但游猎文化这一始源因子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必然要积淀在韩民族文化的深层中,并与自青铜器时代开始形成的农耕文化意识一起构成韩民族文化的二元结构。上述“喜群聚饮酒歌舞”的行为特征就源自这种二元结构,即半游猎半农业文化的典型表现。可以说与拥有成熟的农业文明的华夏中原民族历史意识早熟、社会伦理发达相比,有着游猎文化因子的韩民族先民的意识行为特征更接近于原始的自然性。因此,较少受到约束的生命本体的自然冲动,在还没有建立严格的社会伦理等级秩序的社会群体中,更多地与巫术结合在一起,表现在神人相通、天地神人互化合一的“醉酒歌舞”中。所以,正如有些学者所研究的那样,与歌舞在后期的中国初民的巫俗仪式不同,朝鲜的巫俗仪式一开始就伴随着歌舞。这说明,中国的巫俗仪式出现了一种仪式的阶段性分化而走出了原始性。但始终伴随歌舞的朝鲜先民的巫俗仪式却没有摆脱其原始性,巫师和众人还未实现分离,成为韩民族思想的前结构。这种前结构,在相对长久的发展中逐渐成熟并形成稳定结构,致使巫俗在以后韩国人的内心世界中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韩国固有思想原型的“风流”应该说就是基于这种意识结构的产物。
我们还可以用荷兰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赫伊津哈的“游戏”理论诠释东夷人“喜群聚饮酒歌舞”的特点。(扶余)“连日饮酒歌舞,名日迎鼓。”(《三国志》卷三十,“扶余传”)(濊)“常以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三国志》卷三十,“濊传”)(高句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三国志》卷三十,“高句丽传”)(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三国志》卷三十,“韩传”)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描述中看出,他们的群聚饮酒歌舞并非杂乱无章,在时间、节奏、舞姿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秩序。所以它是一种游戏,一种展开着的文化。赫伊津哈认为:“文化从发轫之日起就是在游戏中进行的……通过游戏的形式,向社会表达它对生活与世界的解释。”“文明是在游戏中成长的,是在游戏中进行的,文明就是游戏。”何谓游戏?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开展的活动,游戏呈现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须和物质的功利。游戏的情绪是欢天喜地、热情高涨的,随情景而定,或神圣,或喜庆。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欢声笑语、心旷神怡随之而起。这就是说,“连日饮酒歌舞”、“饮酒昼夜无休”等是不具有时势之必须和物质之功利的无我的放纵,是能使全员参与而需遵循秩序和规则的嬉戏,是来自生命本身的欢天喜地、心旷神怡的快乐的喷发,而“风流”正是这种意识结构形式。对这个意识结构的特点可以用“兴”这个概念表述。
那么,何谓“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诠释。首先,从“兴”的借用意义上解读。所谓“兴”就是生发于生命本体的生命活力的美的感受,具有较强的感性特点。它源自于原始巫俗仪式疯狂的歌舞中。而原始巫俗仪式的疯狂,都与“娱神”、“神人合一”相关联,而神是像风一样无定所、无形象的。因此,达到与神合一境界的人的“兴境”,也是游走无定所的。韩语的“sinba ram(神风)”正是这种状态的最好描述.但由于“sin ba ram(神风)”是一个词组而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在没有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这种状态之语言的情况下,就只能用“兴”来概括了。“兴”这个词是中国汉字传人之后对这种“sin ba ram”状态的最好描述。就是说,韩国人借用汉字形式表达了自己的“sin ba ram(神风)”之情境。“sinba ram(神风)”在使用时一般与动词“na da(生)”结合,成为“神风”“生”了之意。其次,从“兴”的汉语本义上去解读。“兴”的繁体字是“舆”。会意从舁(共举)、从同(同力),本义起也,起来。有学者认为,从字源学上看,“典”的本义是众人“合群举物旋游时所发出的声音”,即“共同举起一件物体而旋转”。从这种词源学的意义上解释,“兴”就是在原始的巫俗仪式上,参加者在酋长的指挥下,伴随着“乐队”的旋律,虔诚地将贡品缓缓举向上苍,请神灵受用,以此愉悦神灵进而达到与神同欢、神人共欢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已经“呈现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须和物质的功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兴”又具有赫伊津哈所说的游戏的品格。赫伊津哈认为:“游戏和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游戏不是‘平常的生活。它处在欲望和胃口的直接满足之外,实际上它中断了食欲的机制。它插足生活,成为一种暂时的活动,寻求自足,并止步于此。至少这是游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第一景观,它是生活的插曲,是日常生活的幕间表演,但是作为周期性的心旷神怡活动,他成为社会的伴奏、补充,实际上成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装点生活,放大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个人之必须,因为它是生活的一种功能;它也是社会之必须,因为它有意义且有明确的价值,有精神和社会的联想,一句话,游戏是文化的一种功能。”这就是说,韩民族先民富有自然原始性、巫术性的歌舞形式,在游戏的文化功能中,具有了“兴”或“风流”的文化特性。因此,全员参与性、与“神”的沟通性和规范的游乐性就成为韩国固有思想的基本特征,而其特征的核心精髓又是“兴”或“风流”或韩国哲学史所说的“sin ba ram”或“moeos”,这些概念可以说是韩国固有思想原型的核心范畴。因为游乐与群聚疯狂不同,它需要一种秩序、一种规则,在有序的集团疯狂中体味与神的一体感和从中生发的超乎寻常的力量和美感。作为韩国固有思想之风流的核心,应该就是这种在半游猎、半农业的二元文化结构中生成的融合了自然性(来自于肉体生命的)、巫术性(追求于神的)、游乐性(归结为族群理性的)的生命激情——兴。许辉勋在其《朝鲜民俗文化研究》中认为,“兴”作为中国与韩国的原始巫俗文化符号,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两者的根基迥然不同。韩民族文化中的“兴”根植于生命本体,追求“重生”精神,而中国文化中的“兴”则立足于伦理本位,追求“大同”精神。这种不同,又使根植于生命本体的韩民族文化中的“兴”直接与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相联系而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据学者研究,在韩国语表达审美经验的词语中,最常用而且最具民族特色的词语有“sin na da(神飞扬)”、“sin ba ram na da(神风生起)”、“moeos(风采)”、“moeos ji da(风采飘逸)”。这些词从字面上看,“神飞扬”和“神风生起”原初的意思与古代先民宗教祭礼中“神人交灵”密切关联,表达的是一种精神状态,“风采”和“风采飘逸”则是对这一状态的情感判断,后来原初之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神飞扬”、“神风生起”与原初的宗教体验多少有关联的话,那么“风采”、“风采飘逸”则已经摆脱了宗教痕迹而成了纯粹的审美体验。这种语义的变化折射出古代韩民族从单一宗教情感向审美、道德等情感方面的扩张,显示出情感的多元升华、发展。通过韩民族的审美评价,也可以看到韩民族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标准。例如,韩民族对人和事物等进行审美评价时,往往用“有风采”来形容和判断,而很少说“美”或“好看”。这说明韩民族先民最初是从“歌舞赛神”中获得了审美体验,在审美体验中感受到了生命的节奏、生命的律动,更感受到了“生命之流”(天、地、人)的交融。
三
可见,在韩民族固有思想的意识结构中,风流思想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它可谓是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风流思想源于上古,流传至今,具有曲折发展、变化多端、不断丰富的特征。它起初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始的、朴素的风流信仰(风流思想原型),后经仙道的演变以及三国时期儒、释、道的融合,形成以风流道为核心的花郎道。由原始风流到花郎道的转变,标志着风流思想真正从原始信仰升华为兼具哲学、伦理、美学及宗教特色的民族文化理念。风流思想作为韩民族的内在精神(文化价值精神),渗透到韩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于韩民族每一个成员的精神血液中,成为反复复制的文化基因。风流思想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是对人性的立体理解。风流观中的人不是单向度的伦理意义上的人,也不是单纯内心体验的遁世的人。风流观中的人是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审美、理想与现实完美结合的人。风流思想的这种人性观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准确把握,即人是自由自主的主体,人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正是有了这种自发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人性观,才有了“花郎精神”。那么,为什么风流精神成为了韩民族的独特品质呢?这也许和韩半岛的自然环境有关。韩半岛是从大陆多出来的小小的“次大陆”,因此它不像日本岛国那样有被大海淹没的危机感,也不像广阔无边的大陆那样复杂、多元,而是小巧玲珑,令人怡情于自然,在天地人三才统一中超越现实、自由神往。
中国儒学正是在韩半岛的这种固有的文化平台和价值取向中走上了自己的发展历程。换句话说,中国儒学虽然同样传播到韩半岛和日本,但韩国儒学和日本儒学截然不同,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儒学传人后根植的环境及土壤不同,所以尽管是同样的中国儒学,但在韩国和日本所结出的果实却必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