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河流
2015-09-24刘宝凤
刘宝凤
村庄·河流
刘宝凤
河流是村庄的河流,村庄是河流的村庄,在乡下,这两者的关系有点像锅和盖,或者碗和勺。就像在铧咀坪的每个人心里,河流就是我们村庄的河,滋养着村里的牲畜和庄稼,也滋润着每一个村庄的孩童。春来了,下河扑蝶或者采摘河边的野草莓、挖木蓿,夏来了游泳洗衣,秋天听蛙鸣看满池的荷花……因为有了村庄,河流则生生不息,吸呼着村庄的味道与人气,河便有了生气。有很多次天气干旱,河里只剩细细的一股水,连河底的卵石都盖不住了,但那河水还是缓缓地、缓缓地流淌着,看得人揪心不已。好在很快秋雨来了,冬雪来了,河里的水又丰盈起来,河于是又成了让村庄欢喜的河。
河是流动的水,由北向南,顺着沟沟壑壑跌跌撞撞地闯入了村庄的西边,我顺着河走过很久很久,都没有找见它的源头。只知道水是沿着人居住的村庄施施然地流淌着,它走过的地方,有庄稼,有果林,有菜地,有池塘……它紧贴着村庄缓缓流过,像老祖母抚慰孙儿的手。河里的水时大时小,水位深的地方水是温顺的,把所有的波澜都按在了水底,水把两岸的水草滋养得黑绿发亮,挺拔硬朗,蜻蜓见了就停驻下来,在水草上张望着河水流去的方向。一旦河面宽了,拉低了水位,则有着大大小小的卵石羁绊着,河水便急躁起来,发出呜呜拉拉的声响,好似在发泄自己的不满,水面也上下起伏成,像运动员长跑结束的胸膛一般怦怦跳跃。
河的边上,有一股很小的冒眼泉,跟河水汇成一股。水不断往出溢着,一旦多过水坑,便自然地流入河里,泾渭分明的两股水,便慢慢地由清和浊变成微浊、浊,最后彻底融入到河水里,任谁也看不出泉水曾流经过。冒眼泉的水清亮,小手指长短的鱼在卵石下面来回穿梭,动作快得眼睛都盯不住。还有河底的沙粒,经过长年累月的冲刷,干净得有些透明。村庄的井不出水的那几年,河水便成了我们生命的源。每天村庄都会有人挑着两个桶,晃晃悠悠地来河边打水。挑水的人见了河扔了桶,先在河里胡乱洗把脸去去汗,才会轻轻地弯腰用双手掬起泉水,滋滋滋地喝进肚子里,顿时感觉不渴也不饥了,然后再蹲下身子用勺把水一下下舀起桶里。这时候的河,成了村庄人生活的依托。
在河边相遇的村里人,总喜欢停一停,等一等,跟身边的人唠唠磕,插科打诨胡闹几句玩笑,农家人毫不做作和遮掩的笑声便会荡开河面上,在人样高的水草间来回穿梭,直到感染着后面挑水的人。挑了水上了坡才是村子,上坡的路沉重且乏味,这时候总有那喜欢张场的男人开着荤素不分的玩笑,惹得旁边的年轻媳妇们捂着嘴嗤嗤地笑。遇上半大孩子,那被愚弄的人便局促进来,骂着:“你个坏东西,把人家娃都教坏了,XX你说得是?”碰上这样的问题,常常都伴着一句“不知道”,孩子就跑开了。
不知道为何,我总感觉跟河很亲,亲近得一周里不去河边玩那么几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常常装样子拎着笼去河里洗衣服。夏天的凉风嗖嗖地吹过,河草的咸涩味道就往鼻子里钻,一下水,整个心都凉爽了,便扭头在岸上追逐着蜻蜓的身影,眼见着天快黑了,才胡乱把衣服在河里摆弄几下。再看旁边那踏实的大姐们,第一茬衣服洗得都晾干了,这时候便恨起自己的贪玩来。但到了下次,仍不悔改。
盛夏的聒噪里,蛙声一轮赛过一轮,总有那顽皮的男孩在河边挖坑建渠,美其名力曰“水利工程”。他们常常帮我们抓河里的蚂蟥,在河滩上各种折磨,或者抓笨拙得逃不掉的青蛙烤肉吃。我的视线便追着他们,渴望着身为男生的自由和胆大。更多时候他们脱得精光,在离我们洗衣服很远的地方打水仗。他们不敢去深水的地方,所以总是滚得一身泥样,皮猴似的在水里胡乱打水仗,欢快的叫场惹得我们心痒,却没有勇气照着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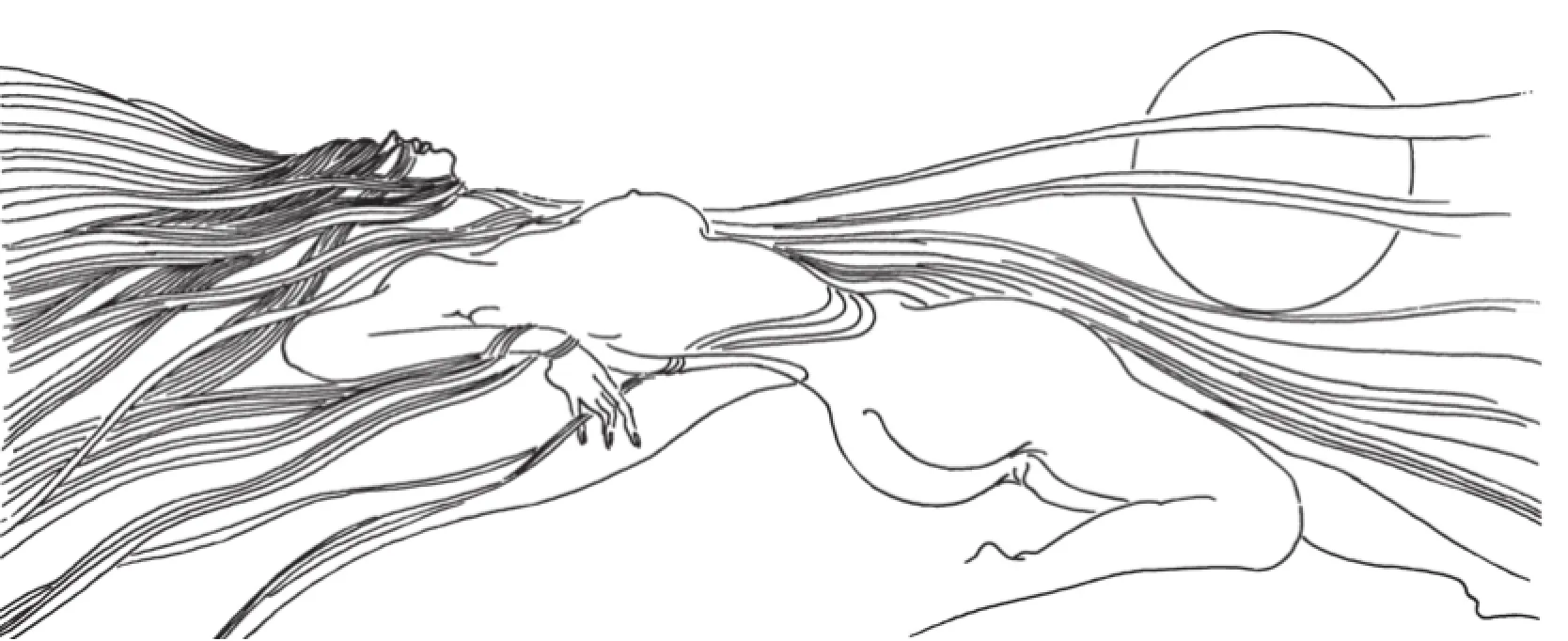
堆雪 绘画
秋天瓜果成熟,跟着看园人混熟了,便能随便摘着吃。摘了便拿去河里洗。要不然捡一些皂角在河边砸,试图制造肥皂。秋天的牛羊也是最悠闲了,没有过多的活要干,整天在山坡上慢悠悠吃草,吃饱了便拉到河边饮水。原来牛也会渴,见了水吧唧着嘴巴,舌头一卷一卷,比吃草还要有滋有味。羊到底是绵软些的动物,它喝水的时候跟脾气一样轻轻柔柔,喝一会叫几声,好像在赞叹水有多香似的。喝够了水的牛和羊,放牧者把木撅子往河床上一扎,便不用管了,尽情地玩到天黑来拉就是。
不尽心的放羊总会出差错,娟家的羊就挣脱了木撅子,把河对岸的苞谷苗啃了不少,结果被庄稼地的主人逮住了,人家硬要把羊往回拉。娟正玩得兴高采烈,听到羊咩咩的叫声吓哭了,赶紧去抓住僵绳不松手。结果就是一只羊,一个大老爷们,一个小女孩,哭声骂声叫声混成一片。等娟的母亲闻声赶来时,娟已经成功把羊从那个老爷们手里解救出来了。人的天性都是同情弱者,娟毕竟是个小孩子,来来回回路过的人便指点那个老爷们,他脸面挂不住便放了羊。其实在河流两边,时常有这样的纷争,如果是自己村子里的庄稼被羊啃了,主人顶多骂几句作罢,但碰上河对岸的人便不同了。好像潜意识里,大家都在争,争这条河流到底是你们村的还是我们村的。河把两个村庄的地和人分成了两块,于是在两岸人的心里,河都只是自己村里的河,不是对岸的。这样明争暗斗了好些年,包括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是在河的分争中长大的。
村庄的人喜欢河流,于是河流一年四季的风情便落入村庄人的眼里、心里。在我眼里,河流一直是温情脉脉的,然而这温顺得如谦谦君子样的河流,发起飙来还真是叫人后怕。上中学的时候,要穿过河去沟对岸上学,平时还好说,临时搭起的简易桥上三步两跨就过去了,一旦遇到阴雨连绵,河水暴涨,就会把桥淹掉。那时候还不知道水的凶险,便几个人拉着手挑水浅的地方过河,平时看着无害的河水混沌且凶猛,巨大的水拉力好像不把水中的人推倒不罢休似的。过了河,还晕晕乎乎没从河水的惊吓中出来。那次对门的卫卫玩大胆,非不跟我们从浅水区过,渡到了稍微深一些的地方,结果一脚刚踩下去,就被浪打得翻了个跟头,幸好手上拿着弯把的长柄伞,勾住了边上被洪水冲刷成一团的水草,在水里几经翻腾才慢慢站起来,再扒拉草连爬带滚上了岸,随后的几天都没有去上学。听说是吓着了,打了几天针都不见效。随后的一个傍晚,我看见村子里的珍珠大妈给他叫魂,她让卫卫坐在门槛上,用盛饭的勺一下下勾着叫着。那个傍晚于我而言记忆深刻,我再也不敢轻易到发水的河边去了,生怕那里蹿出一个红毛怪物,把我进起肚子里。
有一年交公粮时节,河里遭遇了我记忆中最大的一次洪涝。而且那天傍晚的雨下得毫无征兆,不然也不会挑那样的时间去交公粮。去河对岸交公粮的大都是年轻壮汉,归家的时候河里发大水,大家都焦急地在等在河对面,没有人敢冒然下河。后来听他们说那天的洪水真大,几乎到了人脖子的位置,幸好雨不大,几个年轻人没处躲,便挤在拖拉机的下面,风一阵雨一阵,幸好是夏天暑气浓,不然还真得生病。河流道是有情却也无情,最是无情也最是有情。
听说那次洪水主要是上流下来的,因为我们这里雨并不大,顺着洪水溢入河流的,除了混沌不堪的泥水,看瓜人临时搭建的瓜棚也被水冲散,檩木便顺着水胡乱磕碰着往下赤溜,带着瓜蔓的西瓜和梨瓜,在水里起起伏伏,看得人眼馋不已。溢了水的鱼塘就在不远处,鱼一见下雨天便缺氧,不得不浮到水面上大口呼吸,有一些鱼被雨打蒙了便跟着水溢出了鱼塘,往河流的方向流窜。河水退去后,挂在河两岸的树杈上、草丛间什么东西都有,频死的鱼,半烂的瓜,运气好的还能捡几根檩木。
现在河里的水越来越细,已经几近干枯,但好像又有那么一丝精气神在支撑着,让河流不要彻底断掉。我在猜,那一丝精气神会不会是村庄赋予的力量,毕竟村庄和河流,上百年的相伴,已经深入彼此的骨髓。
麦陇黄,五月忙
头一天看着还半绿的麦子,一晌的工夫就全黄了,金灿灿地摇着小脑袋。对庄稼人来说,再也没有比看见小麦成熟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尤其是北方城市,秋只是辅种,麦子才是正茬,一年的辛劳勤苦,全都在这料庄稼上。眼望北陇上金黄的麦浪涌动着、撺掇着,浩荡蓬勃、滚滚如潮涌般散发出迷人的麦香,让人不由想起诗句: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北岭上的麦子黄了一片又一片,母亲的心也跟着焦了一寸又一寸。她是个急性子,再加上麦子黄了不等人,要不及时收进仓里,不知哪里来的一阵邪风就会把麦粒摇到地里,捡都捡不起来。所以一到这时候,父母常常是身不挨床,天不亮就磨镰去了地里。中午吃饭也是凑和着,把早早压好的挂面往锅一扔,锅底下再烧油炒一点葱花,一顿饭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吃了饭,也不敢休息,身上稍微缓过了乏劲,又得赶紧去地里。晚上依然是这般凑和吃,吃了饭上床躺上十来分钟,身体舒展开了便背着月光再次去地里。
晚上的麦地明显没有白天人多,所以总有人家的麦子顾不上收就被风或者雨糟踏许多,也就是母亲常说的好日子都是一镰一镰割出来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困极了,便偎在捆好的麦子堆上休息,谁知道一坐下就给睡着了,大概近一小时才醒来。母亲看看天色便埋怨父亲也不叫醒她,父亲嘿嘿地笑了笑没有说话,继续把腰弯到半身高的麦地里,这时便只能看到两顶草帽,一前一后在金黄色鹅缎上露出个尖,忽高忽低地移动着。
麦子拉回场院,父母才踏实许多。我总觉得这种踏实是一种农民与生俱来的本能,在我父母身上尤为明显。自从搭镰开割起,父母的心便都挂在地里,听天气预报,夜里几次去院子看天气。要是哪天没跟上看天气预报,父亲还会拿起平时都不舍得用的电话拔气象台咨询,生恐哪里不周道田里遭损失。
麦子先是堆在场院里竖着脑袋晒,把那湿湿的麦杆晒得干崩脆,各个都垂下饱满的“大脑袋”,才能摊开麦子碾场。遇到下雨天,便要赶紧把麦子寄成麦垛盖起来,沾了雨的麦子就会长芽,就算是磨成面也难吃得不行。所以天气稍变,就得全家总动员,麦子垒得高了,便由一人在下面往上扔,一人在上面压垛子,稍微不留意,麦垛可能就溜了,这样又得重新弄。所以寄麦垛特别费心。其他人也别想闲着,全场上的麦个子都得运到麦垛跟前。每天雨前便跟打仗似的,全都蚂蚁样在场院里跑来跑去,别说空闲,连去茅房撒尿的时间都没有。直到麦垛垒好,盖上雨布,用木头石头压得严严实实,才能松一口气。还不等气喘匀,豆大的雨点拍了下来,跑得快了赶紧钻到屋檐下,场院离家远了,就一步一个由那雨疙瘩把脑袋打得生疼。
碾场要翻,把麦杆翻上来,把麦粒抖下去,一场下来翻个三五次便成了,麦是麦,杆是杆了。接着就要借个大风扇扬场了,大风一吹,扬起一掀掀麦子,直到风把糠吹走,把麦沉下来。细心的母亲还要用簸箕簸皮,用筛子筛,直到把麦子归整得一颗颗一粒粒,这样交公粮的时候才能够上一级,按最高的价格算。
现在,麦子收得越来越快速简单,简单到大型收割机往地里一开,拉回来的就是麦粒,麦杆往地里一扔,省事的人就一把火点了。不再需要帮忙的麦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对于久居城市我已经慢慢忽略麦子是几月熟的。直到有一天电话打回家,问母亲在干嘛,她说收麦子,急着去找收割机呢。我这才想起来,哦,原来又到一年麦黄时了。
◎刘宝凤,女,80后,曾在《延河》《秦岭文学》《工人日报》等发表散文小说。获上海市作协、《西安日报》等举办的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