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啸:美的极致是自由
2015-09-18
曾经的韩啸,作为整形美容界的翘楚,怀着精湛的美容技艺,以其胸怀天下的人文关怀做着医疗整形事业;如今的韩啸,与艺术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2012年5月举办了《手术:韩啸行为艺术展》后他的创作便引发了广泛争议,如同一颗石子打入湖水,荡起了艺术圈对于艺术的可能性表达的涟漪,当批评家们在思考和议论中将其作品归入艺术的范畴时,韩啸却道出了让人不解且颇具争议的一句话:我不是艺术家,我做的不是艺术,是生活。如果一定让我为艺术、为美、为生活做一个注释,那便是freedom(自由)。

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韩啸以其潇洒不羁、特立独行的个性追求着一种美到极致的生活,他将艺术的态度溶于血液中,融入他生活的点滴中,举手投足、穿衣谈吐之间极尽美感。韩啸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爱茶成痴,钻研周易玄学,颇有魏晋之风,然衣着服饰的品位上又有着西方贵族般的低调奢华。生活中的他对自己的爱好投以最大的精力和热情,专注于每一个细节以求达到完美,不在乎曲高和寡,只执着于追求自己心中自由的向标。纵观韩啸的前四十年,也就不难理解他将手术台移至美术馆的行为了,一个将他的生活品位做到极度艺术化的人,他的生活本身便是艺术,作为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手术亦是艺术。
既对别人要求苛刻,也对自己要求苛刻是韩啸的信条,对别人要求苛刻体现在整形美容上,对自己要求苛刻体现在极致的生活上。艺术不是一个门类,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韩啸便是这艺术化生活的标杆人物。
他的手术消除了性别差异、文化的成见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艺术与美的标准,在他看来,对于一切标准的否定只是为了呈现最极致的生活,从而获得最大的精神自由。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它既不解释什么,也不推演什么。因为一切都已公开地摆在那里了,没有什么需要解释。摘除了传统意义上艺术的光晕,将现成品纳入了艺术系统的杜尚也曾说:在传统意义上讲,现今存在的几乎每一件现成物体都不是原物,因为艺术家使用的一管管颜料都是机器制造的,都是现成的产品,所以我们必须断定,世界上所有的绘画作品都是现成物体的辅助,它们都缺乏原创性。这一切都指向一点:艺术本来没有法则,法规愚弄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韩啸的作品,他只是将一个整形美容手术呈现在了公众面前,无须解释,也不需要任何人对这手术做一个是不是艺术的判定,如同杜尚一般,他的创作不属于任何流派,不属于任何艺术形式,所有既定价值、规则或者美感标准都是无意义的,当代艺术原本便是消除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韩啸从未将自己定义为艺术家,社会给予他多重的身份,但韩啸一个都不要,他将自己定义为生活家,因为他的一生是追求美的一生,追求自由的一生。在韩啸的整形手术面前,艺术的概念看上去是毫无疑问的苍白和空洞,生活这个词标志着艺术的死亡。事实上我们怀疑生活这个概念成为艺术的中心,是寻找到了替代,而不是合法地理论化这一概念。在一台变性手术面前,艺术甚至承载不了乌托邦期待的可选的一点微光。
如今当代艺术走在了一个误区,过于把艺术当回事儿,艺术家们在形式上、内容上抑或是观念上竭力呈现出与众不同、高深莫测,将艺术缩小至多数人无法看懂的小众范围,以当代艺术的名义将自己束缚在了高墙之内,使艺术实际上俨然成了少数人的精英文化,而这种精英文化的呈现实则与公众有一种割裂式的距离感,违背了当代艺术的本意,在民主、平等、自由的当代社会,精英文化是应当被摧毁的。如果说杜尚推倒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那堵墙,在理论与实践上拉近了艺术与公众的距离,那么韩啸的手术则是一个深层次的实践与开拓,以极致主义的生活方式做出了表率,他将医学领域的手术台移至美术馆,是通过艺术和美对生活的再提炼,对自由的再定义。他的手术消除了性别差异、文化的成见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艺术与美的标准,在他看来,对于一切标准的否定只是为了呈现最极致的生活,从而获得最大的精神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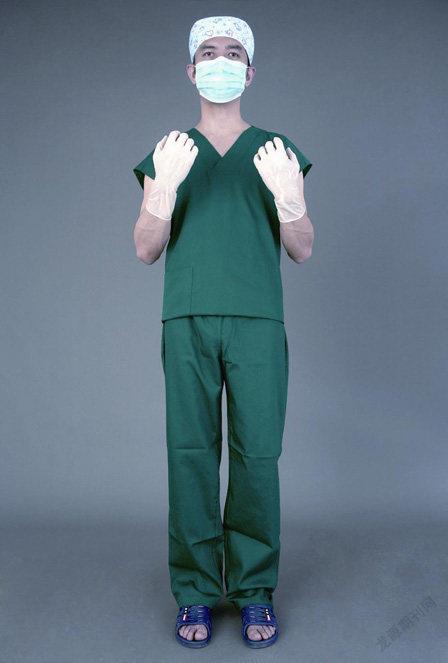
彭锋:韩啸的行为,可以在众多的当代艺术理论中找到支持。但是,韩啸的行为是不是艺术,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韩啸的行为被宣称为艺术时,它所引起的关注、质疑、讨论以及有可能进一步触及的问题:当医术离开治病救人之后,它还是医术吗?值得为了美而去实施手术吗?手术能够真正造就美女或者美男吗?用手术的形式改变一个人的外貌是合法的吗?用手术改变一个人的性别是符合伦理的吗?韩啸通过宣称自己的手术是艺术,无疑会加深人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思考,它比韩啸的手术是不是艺术更重要。(《可塑的身体——评韩啸的行为艺术》)

王春辰:事实上,这是韩啸以手术的行为在确证艺术的可能性表达,而又以艺术的名义来强化对生命之肉身的反思。手术作为人类救治自身肉体的方式,源远流长,复杂而精细,迄今更加完备高明,生命的病变顽疾在手术之下得以救治修复,肉体得以康复,生命得以延续。这是手术的本质,但手术也进入另一个人类的审美化追求中,即它不再以肉体病变为对象,而是以形体缺憾的完善为目的。后者的手术功能为人类带来形体的革命,即通过整形而成为人工之人。人者,在手术中实现的不再是疾病的消除与根治,而是自身肉体意义的重构。人以手术求肉身的改变,非为肉身的灵魂超越,而是肉身的世界化,即以人类的自我审视为观照坐标,一指向表象的审美欲求,以获得肉体向生命联通的那一瞬间心理感应;二是指向外部世界的满足,以他者为参照,受控于人类的自我形象的异化体制,使形象成为被消费的核心价值之一,绵延至肉身的异化改变。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古训,肉身、心灵与美化并非对等之关系,但一部人类史中,美艳倾国不绝于史书,以形象为武器,实乃是人类自我视觉化之后的文明之殇。(《手术成为艺术》)
约瑟夫谈克: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再属于我们自身,而相反地被社会、文化和历史彻底渗透,难道我们还看不到艺术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吗?我认为,这就是韩啸的工作所抓住的关键。现在,艺术在我们身后进行着,在无人实际掌控的匿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中进行着。在这方面,韩啸与他的志愿者/被试者/对象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所以他即使暴露出不完美也无可厚非,这是欧洲美学黄金时代和后现代理论家们都共同存在的问题。创作一个作品时如果缺少应有的程序,艺术家、客体、自然和文化就会变得极其混乱,但是不能因此就把结果简单地归因为一个接一个的事物。
然而韩啸的艺术大都是将美再一次引入现代艺术,这是在艺术家工作室或是当代博物馆之外创造的美。这是广告商、女性杂志、男性幻想以及对年轻、完美和永恒的渴望所构想的美。但也许,最核心的内容是:韩啸的作品表明了在丧失自我的过程中发现的美,或者更彻底地说,意识到我们从未拥有可以丧失的自我。(《实现你的潜能:韩啸的易逝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