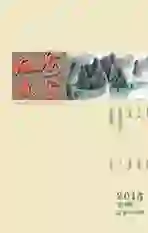小说三题
2015-09-17罗俊士
罗俊士
归来
张强从一家国营企业下岗后,三个多月没找到工作。也怪他,力气活不想干,又没有一技之长,哪家私企也不养吃闲饭的,当然会屡屡被人拒之门外。没奈何,他干起了蔬菜批发。
这天早晨,大雾弥漫,张强开着一辆长风三马车去乡下贩大头白菜,回到县城想占个好摊位,三马车开得莽撞了些,后右轮轧了一位扫马路的大叔。那位大叔瘫坐在地,表情痛苦地说,别傻愣着啦!快送我去医院啊!张强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招手拦出租车。
到县医院急诊室后,张强给老婆吴莉打电话,让她立马来医院。吴莉刚来到医院,那位大叔的老婆季芳和他们十六岁的儿子李涛也来了。季芳气急败坏地问,老李,你不是穿着黄马甲吗?咋会被轧了呢?老李说雾大呗。季芳火了,快没命了,还替肇事人遮掩,憨呀你?老李煞白着脸苦笑。
医生开了个单子,催他们去住院处缴费。张强说您行行好,先安排老李住院用药中不?我这就回去筹钱。医生说恰好我院刚出台一项为民举措,对于危重特殊病人,可以先住院治疗,你赶紧筹钱去吧,我马上请示院长。
张强走出医院后,发现李涛跟在后面,你走哪儿他跟哪儿,像条不声不响的影子。来到一位朋友家,张强说想借点钱,有急用。朋友问这个孩子是谁?张强不得不实话实说。朋友听了摇摇头,说自己手头紧,你去别处借吧。一连去了几家,都是这种情况。张强说,李涛,你跟这么紧,我想扯个幌子都不成,不如你回医院,我老婆不是在那儿吗?你盯好她就成。李涛还是不吱声,却点点头,转身走了。
又转几家,张强只借到几百块。去年二月里,张强因为老爸身患肝癌住院,取出全部存款,又借了三万多块,才筹齐手术费。现在他下岗了,旧债还不了,谁肯再把钱往穷坑里扔呀?
张强有个高中同学叫刘洋,在市里一家公司当副总,去年借给张强一万,还说有困难尽管张口,你这人实在,我上大学那会儿你曾借给我几千块,现在,我得涌泉相报。刘洋的手机停机了,张强只得去市里,找房东打听,房东说那家公司倒闭了,刘洋去了石河子。
张强也去了石河子。没想到那地方那么大,缺少联系方式,蒙头蒙脑找一个人,等于大海捞针,没有指望。张强赶紧找工作,不然就没钱吃饭了。
有个建筑工地要招看大门的,张强嫌工资低,不干。对方说每天五十元,不少了。除非当力工,一天能开你一百。技工更高,可你干得了吗?张强一横心干起了力工,搬砖,提泥,扛东西,每天累得够呛。
跟着鸭子上架,张强慢慢学会了砌墙、抹墙、刷漆、刮白、粘地板砖。当技工后,收入翻番,可他仍然捡旧衣服穿,鞋袜和帽子也是捡来的。他经常在工地附近那家餐馆吃饭,进门就抹桌子拖地洗碗刷盘子,还抢着帮女老板干杂活,就为一日三餐,免费。
再说老李,也是下岗工,儿子李涛患白闭症,常年需要治疗,家里人不敷出。主治医生说老李两条小腿骨头碎裂,膝关节以下必须截肢,需要好大一笔手术费,因张强不辞而别,无奈之下,老李想放弃治疗。可放弃治疗就有生命危险。于是,李涛写了个求助牌子,跪在医院门口,逢人就喊,救救我爸!救救我爸!
六年后,初夏的一天上午,老李家来了一位大胡子男人,两口子看他很面生,异口同声问,你找谁呀?大胡子男人把几样礼品放下,搓搓手,瓮声瓮气地说,是我,不认识了?是我呀!老李把轮椅往前摇了摇,仔细端量大胡子一番,点点头,张强你可算回来了!坐,坐呀!季芳也认出了他,面色顿时阴冷下来。老李指使季芳,把冰箱里那盘猪头肉端来,我陪张强兄弟吹瓶酒。季芳白了老李一眼,你个憨种,就知道喝酒!话是那样说,她还是拿来了酒菜。
老李边斟酒边问,在外边不好混吧?是,挺难的。张强喝下一盅酒,呛得直咳嗽,说话也有些磕绊,这几年,我、我戒酒了,烟也不抽了。你、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咳!咳!老李淡然一笑,说不上好,也说不上惨。那年,多亏几位爱心人士捐助,手术出院后,我用余钱把临街那两间小房朝外开门,弄了个小超市。李涛前年去交警队上班,谈着个对象,就快成家了。季芳没好气地说,成家?没钱成个屁家!张强你这人太差劲了,心比石头还硬,就那么一甩手走了,要不是有人捐助,我家老李指不定早没命了。张强又喝下一盅酒,低头不语。
这时,有人喊买东西,季芳忙去小超市应付顾客。
老李问,回家看过你老婆女儿吗?张强摇摇头,没呢。话音刚落地,吴莉就进了屋,她放下一小捆韭菜,抓起笤帚想扫地,被老李制止了。老李把张强指给她看。吴莉注视着大胡子男人,突然痛哭流涕,随之戳指着张强的鼻尖吼叫道,死鬼!你还知道回来呀!一走就杏无音讯,以为你死在外边了呐!你咋不死呢?张强颤抖着声音说,老婆,对不起。
吴莉在西关口摆着个菜摊,她经常抽闲过来端屎倒尿,伺候老李。有时夜里也带女儿过来陪老李两口子聊天。她是在替张强赎罪。
张强在外边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不敢逛大街,不敢往老家打电话,甚至学当地人蓄起了胡子,可心里那团阴影越来越大,常常夜半惊醒,虚汗淋漓。
附近音像店里传出费翔的歌声: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
张强和吴莉走后不一会儿,警车就停在了门外。几位干警从车上下来,如临大敌,却不见大胡子男人。领队的是城关镇派出所林所长,他声色俱厉地问,人呢?人呢?季芳说刚走,跟他老婆回家了。走!我带你们抓他去!
老李一把捉住季芳手腕,谁让你报警的?看在吴莉几年来给我端屎端尿的份上,你也不能报警呀!季芳说不是我,是李涛报的警,他是在汽车站附近交叉口看到张强的,随之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报案了。老李,再不能让张强开溜了!吴莉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我才不相信鳄鱼的眼泪呢!再说,我一个人照顾你就够了,她那是六指挠痒,多一道子,每天来这儿做做样子,目的就是为了稳住咱们,不去报案抓他男人。季芳说罢,甩开老李的手,一头钻进了警车。
就快到张强家了,林所长接到一个电话。合上手机,他让司机停车,掉头回所里。季芳不解,怎么,不去张强家了?刘所长说不去了,张强自己投案,在所里等着我们录口供呢。
季芳回家后,翻看张强留下的几样礼品,发现那箱营养快线没有用胶带封口,打开一瞧,里面是整沓整沓的百元钞。
自首
齐宝良大学毕业后,在县政府当公务员十年窜头了,仍然没有头衔。他老婆薛静在一家私企打拼,不到三十岁就被升职为购销处处长了。打那时起,两口子在家里的地位就显出了高下,薛静像齐宝良的科长,颐指气使,吆五喝六。齐宝良只有唯唯诺诺,服从的份。
齐宝良有个大学同学叫张章,和他一起进政府办的,前年冬被提为副科,今年开春又升半格,成为正科,走路都有些飘飘然起来,齐宝良羡慕不已,嫉妒有加,直恨自己窝囊、无能。
这天傍晚,齐宝良给张章打电话,说想请他喝酒。其实他是想跟张章讨教。张章说你来天外天酒家好了,正好我要宴请一位美女。
齐宝良到那儿时,美女已经在了。张章介绍道,这是我表妹史小莉,前几年曾在多家私企打工,年初才托关系进了县电视台,做导演。史小莉笑笑说,齐科长,甭听我表哥瞎讲哟!我进台不到半年,哪儿配称导演,充其量是个不人流的编导。
齐宝良那张白脸顿时飞红,结结巴巴道,我、我只是个科、科员。史小莉不信,不会吧,你和我表哥不是大学同学吗?当公务员有年头了吧?怎么会纹丝未动呢?张章说,真的!他这个人吧,优点是老实,缺点也是老实,换个说法就是,死眼皮子,半死蛮子。齐宝良的脸更红了。
吃喝完了,张章去柜台结账,史小莉趁机开导齐宝良道,齐哥,你得活泛些,向我表哥学。又说,要不要我给你搭个桥?见齐宝良疑惑不解,她不得不把话往明里撂,知道吗?政府办安主任是我老乡。齐宝良点头如鸡啄米,那敢情好,拜托您了。
隔几天,周六晚上,齐宝良坐史小莉的面包车,去了市里。真如史小莉所说,只有安夫人在家。齐宝良按照史小莉编导好的话,说自己姓齐名宝良,在政府办某某科当秘书,这次来市里办事,顺便看看安主任,没想到安主任不在家。说罢,他将两盒普洱茶搁台柜上,转身便走了。
从安主任家出来,齐宝良瞥见史小莉正在楼道那边摆弄手机。安夫人出门道谢那一瞬,史小莉闪身躲进了楼道口。
回来的路上,齐宝良仍有些忐忑,小莉,这事靠谱吗?史小莉大咧咧地说,当然靠谱啦!不信你去问我表哥。
齐宝良真就去问张章了。张章说这还不够,你得学会和安主任套近乎。其实也简单,比如见到安主任,老远就打招呼,喊声好。近距离时,递支烟,送个笑脸什么的,安主任心里一热乎,你的事指不定立马就会提到议程上来。齐宝良拨拉一把后脑勺,说,这么麻烦呀!我、我怕是做不来。
正说话间,安主任大摇大摆走过来。张章果真喊了声好,快步迎过去,又陪着安主任往这边走。齐宝良也换副面孔,嘻笑相迎。安主任拍一把他的肩膀,小齐,好好干啊!齐宝良一激动,打了个立正,是!我一定好好干!
晚上回到家,薛静说她看好了公司附近一套房子,想买下来,问他有多少钱?齐宝良说我原先有些钱,现下一个也没了。
薛静听说他把钱全送出去了,顿时火冒三丈,戳指着他的额头说,你个糊涂蛋,这么大的事情居然瞒着我?这不是拿钱打水漂吗?
刚睡熟,电话响了,齐宝良一听是安主任的声音,心跳顿时加快。安主任说你那事已经报组织部了,过段时间就会批下来。齐宝良忙说,谢谢,谢谢您!不过,我能问问,过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吗?安主任说快则两个月,慢则三四个月。
嘿嘿嘿!齐宝良高兴得直拍巴掌,把薛静拍醒了。薛静嘟囔道,神经病,还让不让人睡了?齐宝良乐滋滋地说,刚才接到安主任电话,说我那事报上去了。薛静说,你是在做梦吧?黑着灯,你是咋接电话的?电话在客厅,我也没听见你下床开卧室门呀!齐宝良呆了,大睁着两眼等天亮。
到单位后,听人议论说,安主任要调往市里。齐宝良顿时像掉了魂儿,立马给史小莉打电话。史小莉说我也听说了,安主任真的要调走,不是去市里,是去外县当副县长。齐宝良问,那,我的事还有指望吗?史小莉没好气地说,有球指望,一朝君子一朝臣,人走茶凉,吃亏的都是那些想攀高枝的憨种。
两天后,市里公示几位调升官员名单,其中就有安主任。
这天下午,齐宝良正坐立不安之际,电话响了。史小莉竟然劝他去自首。齐宝良说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啊?我去安主任家又没人看见。再说,行贿也会被定罪的呀!史小莉说关键是,已经有人揭发安主任在前了,如果从安主任嘴里吐出你的名字,一切都晚了。虽然行贿也会被定罪,但主动自首是会从轻判处的,哪头轻哪头重你好好掂量掂量。
齐宝良有个疑问,小莉,你跟安主任不是老乡吗?为啥撺掇我揭发他呢?史小莉诙谐地说,包括你和我表哥张章,咱们不都是本县老乡吗?
不一会儿,张章来了,也是劝他去自首的。张章说行贿这类事吧,泼水难收,可人家另有收获。你这瓢水泼得太窝囊,只能收获一个冤大头的名号。不捅他一下,这口气你咽得下吗?
张章刚走,电话又响了,是薛静打来的,事办不成,想昧钱轻松走人,太便宜姓安的那个王八蛋了!你只管放心大胆去揭发他!我会照顾好儿子,守好这个家的!
齐宝良嗫嚅道,我担心进去后会被单位除名。薛静更火了,十几年你都白干了,有什么可留恋的!良禽择木而柄,凭你的聪明与诚实,去私企打拼,准保能混出个人样儿来。
哪家私企愿意用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呢?齐宝良心里虽然没底儿,可薛静的话他还是听的。去县纪检委的路上他还在想,别人的意图不知道,老婆能不向着自己男人吗?
服刑期满这天,齐宝良刚回到家,张章和史小莉就上门了。他俩是专程从北京赶回来的。
前年夏初,安主任那个案子没有把张章牵扯进去,但谁知姓安的会不会再往外供人呢?只要他在里面,张章的心就无时无刻不悬在半空。那段日子,张章说话明显少了,一副老气横秋模样,做事丢三落四,加之屡屡被新主任排挤,一气之下递交了辞呈。史小莉觉得在县电视台当编导没意思,像个打杂的小跑,再晃荡下去,大好青春就溜光了,干脆,她也辞职不干了。之后不久,两人合伙在北京开了个文化传播公司。
史小莉说话还是那么爽快,齐哥,鄙公司宣传总监一职,就等你来做了。然后,她递给齐宝良一张银联卡,这是公司开办两年多来你的那份分红。齐宝良推拒道,无功不受禄,你们打拼挣来的钱,我怎么能要呢?史小莉说你进去是我考虑不周导致的,所以这钱你必须收下。张章附和道,这样,我俩心里会轻松些。
原来,那次齐宝良进安主任家门时,躲在楼道里的史小莉用手机给他录了像,录像里还有安夫人和她的说话声。之前史小莉曾多次陪人趁安主任不在家时去他家,还陪张章去送过一次钱。她做这些事有个目的,想进县政府机关当公务员,没想到,安主任把她搪塞到了县电视台。她搞录像是为抓住把柄,以便日后要挟安主任。却不料,计划撵不上变化,安主任要调往外县。
更料不到的是,当史小莉给安夫人打电话,追问齐宝良送去的那笔钱时,安夫人却打起了马虎眼儿,什么钱?我没见到啊!史小莉说那两盒普洱茶你打开看了吗?安夫人说看了呀!不就两块茶吗?
史小莉气不打一处来,当即给市纪检委写了封匿名信,塞进了邮政局门前的绿邮筒。
次日上午十点多,史小莉突然觉得不妥,赶紧去邮政局,想找回那封信,营业员告诉她,已经投递走了。她后悔不该在信中夹寄照片,这不是把齐宝良给露出来了吗?信找不回来,只有将错就错,劝齐宝良去自首了。为此,她还给张章和薛静分别打了电话,让他俩说服齐宝良,立即自首。
就这样,安主任在公示期满那天,被隔离审查了。
都是短信惹得事
谢方走进总经理室时,廖汪正在压低着声音打电话,丽丽,这几天没去看你,是我实在脱不开身,刘梅盯得太紧。谢方想退出去,廖汪招手示意他坐下,继续讲他的电话,丽丽,我人不能去,脑子里其实一直在盘算,把你安顿到一个清净地方。这样,你把随身衣服用品准备好,待会儿我去接你。去哪儿?去邺城我老家。放心,刘梅轻易不去邺城,以前她一般都是春节去一次,这几年公司忙,春节也顾不上去了。你赶紧拾掇,待会儿见!
宋丽丽快生产了吧?谢方问。噢。廖汪说,你千万别给刘梅透口风哟!谢方说,我是那样人吗?廖汪说,跟你老婆也不能说,女人的嘴,没把门儿。谢方忍不住发笑,这话你叮嘱我十多遍了,我会保密的。廖汪说,小心不出大差,等到宋丽丽给我把儿子生出来,刘梅知道也迟了。唉!都怪我那姑娘智商低,初中读四年,高中读六年,跟她小学同过窗的有几个大学毕业都读研了,她还没拿到高中文凭。刘梅不能生了,你说我咋办?
谢方没法回答他的话,咋办?你不是已经办妥了吗?其实那句话无须回答,因为内中蕴含着只得如此,这是万全之策的意思。 廖汪喊谢方过来是有件事必须马上办,陪他把宋丽丽送走。
欣欣制衣有限公司是刘梅官居高位的老爸扶持他们鼓捣起来的。刘梅长相平淡无奇,嘴头子特棒,多年跑外,并未出过风流韵事。她曾约法老公:不准偷嘴吃,否则……廖汪从未想到过离婚,家庭与事业这两样他都要,第三样也要,但不好明说,只能暗中行事。廖家三代单传,许是受传宗接代陈腐观念影响,又或许和事业的蒸蒸日上有关,廖汪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动起了借腹生子的念头,并付之于行动。
宋丽丽的住处挺隐蔽,在向阳旅馆四楼最里头一处居室,带小卫生间和小厨房,各种摆设现代,超薄电视、笔记本电脑、冰箱、电饭锅、电磁炉、电动吸尘器等,一应俱全。宋丽丽白皙,个头高挑,是个万里挑一的大美女,由于十月怀胎,即将分娩,肚子膨大得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嘀嘀!嘀嘀!是廖汪的手机在响。他用左手打开手机,翻出一条短信:你在哪儿呢?廖汪给对方打了过去,不耐烦地说,刘梅,有事直接说不好吗?发什么短信?我去乡下招几个熟练T。谁在车上?不是跟你说了吗?谢方谢主任。啥?让他说话?好好好!谢方接过手机,说董事长您好,噢,噢噢,好咧,好咧!我一定那啥,有我在,您尽管放心!
廖汪开这辆宝马车已经六年了,他的技术日臻娴熟,车的性能及外观均属优良。都说人要衣配,马要鞍配,廖汪和这辆车,就是绝配。他作为成功人士,虽然年过半百,配一个年轻貌美的缝纫女工也算时髦,可他有老婆,这就成了乱配。廖汪曾对谢方说,他和宋丽丽能走到这一步,全得益于短信,宋丽丽外表腼腆,与男人说话时常常脸红,短信里的她却热情似火。她说你才是个真男人;她说女人都想倚靠一个硬实的肩膀;她说真爱就是全身心的付出,不图任何回报。
几天后的傍晚,廖汪约谢方去凤凰酒家喝酒,刚坐下,他就唉了一声,说,我和宋丽丽的事被刘梅发现了。都是短信惹得事,宋丽丽吃饭时间也发短信,短信里老公老公的,这不是自我暴露吗?刘梅身为董事长,手下能没几个心腹?纸里包不住火,但也暴露得太快了些,她居然顺藤摸瓜追寻到了向阳旅馆420房间。好险!不是我提前把宋丽丽转移到邺城,可就坏事了!
临分手时,廖汪让谢方去省城参加一个订货会。谢方说,我一个办公室主任,去参加订货会不合适吧?廖汪说,最近我老牙疼,吃不好睡不稳。换句话说,就是寝食不安,你忍心让我带病上阵吗?谢方说,订货会应该刘董事长去,她不一向负责销售跑外吗?我就是个做现成活儿的料,好多事情没法拍板。廖汪说,她也走不开,你只管去,遇到难事及时跟我俩联系。廖汪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再推三阻四,就有不服从领导的嫌疑了,谢方只好答应下来。
廖汪其实没害牙疼病,寝食不宁倒是真的,因为宋丽丽的预产期就是这几天。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刘梅也走不开,她要把廖汪盯死在眼睛里。为这,两人不得不撵鸭子上架,把谢方推到省城订货会上。好在有手机,可以随时发短信请示汇报,收短信读取指令,谢方等于是颗棋子,总经理廖汪尤其董事长刘梅在二百公里之外动动手,他在省城就挪一挪。
谢方从省城回来才知晓,宋丽丽生了,是个儿子。刘梅做了让步,条件是,廖汪必须快刀斩乱麻,和宋丽丽彻底绝交,附带勒令把孩子给老家公婆,眼不见,心不烦,她不想身边多根针。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廖汪刚睡着,听到了开门声。刘梅进屋后,双手叉腰站在卧室门口,阴森着脸问,廖汪,一整天你去哪儿啦?回来也不开机,我给你发六条短信,看见没?廖汪说我手机没电了,那不,正充电呐。接着解释道,上午我去了康德大厦,那不,买了双皮靴。中午和朋友喝酒,后来打了几圈麻将,天就黑了。刘梅说,不!你去了邺城二姐家。宋丽丽想看儿子,当然也去那儿了。那双皮靴是你在邺城鞋帽店买的,你是天大黑才回来的!廖汪慌了,你、你居然派人跟踪我?刘梅说,跟踪你咋啦?我还让人拍照了呐!对你这种言而无信的人,就得这样让事实说话!
第二天上午,刘梅逼迫廖汪跟她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那个一百八十平米的房子是老岳父出钱买的,房产证上的名字也是老岳父的,当然没有廖汪的份儿。公司里的股份有老岳父三分之一,刘梅三分之一,廖汪只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全抽走,也就三十来万。这些年,廖汪收入不少,大都扔老家了,他爹患脑瘤住院做手术花费几十万;两个弟弟修房盖屋娶媳妇啥的,也没少贴补;还有,前后几次给宋丽丽也有十几二十来万。那辆宝马车归他了,可也该大修了,不值多少钱。
这天下午,公司班子成员进行了重新调整。谢方接到一条短信,是廖汪发来的,说有要事,要他去老地方面谈。
那个老地方就是他俩经常去的凤凰酒家,却不是雅间,而是大厅。
宋丽丽把孩子偷走了。四个小时前,她给廖汪发了条短信,威胁他说不准备够二十万就把孩子送人。廖汪手头钱不够,股份到年底才能抽出来,他找过几位朋友,知道他不当总经理了,都对他横眉冷对起来。
而如今,谢方被提升为总经理了,人的地位一抬高,筹借几个钱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廖汪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说他想借些钱,把儿子赎回来。谢方说,我凑凑看。他其实不想借,不是他做事短,是手头真没钱,他把积攒的钱全入股到岳父经营的那个轴承厂了。
转个念,谢方说我想提醒一句,你应该做个DNA鉴定。廖汪一怔,怎么,你怀疑那孩子不是我的种?谢方说你不是说有个从山里来的打工仔,跟宋丽丽过从甚密吗?廖汪又是一怔。
两人刚走出凤凰酒家,廖汪的手机响起短信提示声。他翻出那条短信,看了足有几分钟,才说,钱不用凑了。怎么啦?谢方问。廖汪铁青着面色说,方才我给宋丽丽发了条短信,说必须先做DNA鉴定。这不,她给我回了条短信,只有五个字:不必了,拜拜!我算是倒八辈子瞎霉,这些怪事怎么全让我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