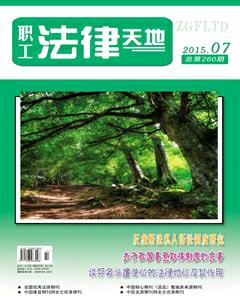关于合同解除的异议权法律规定探析
2015-09-15张秀梅
张秀梅
摘 要: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依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享有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它的行使直接导致合同权利义务消灭。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便告解除。为了限制解除权人滥用解除权,避免给无过错当事人造成损失,法律在保障一方行使解除权的同时,赋予另一方即相对方异议权。本文阐述了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立法规定、法律困惑,并对合同解除异议权的具体适用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合同解除;异议权;法律困惑;路径
一、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立法规定
合同解除权在解除权人的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即告成立,无需征得对方同意,这对于及时保护合同解除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合同法》也规定了合同解除的异议权。有关合同解除的异议权主要规定在《合同法》第96条及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
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这就赋予了非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权,即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是本条文没有就异议权的行使期限、行使方式和法律后果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如果相对方没有及时行使异议权,会使合同效力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
有鉴于此,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对合同解除的异议期做出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是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的异议期间及其法律后果的解释,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是对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权行使方式及后果的规定,但是,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又明确规定,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之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三个月之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就涉及如果发出解除通知一方并无合同解除权,相对方未在异议期内提出起诉,人民法院该如何处理,合同的效力状态该如何界定的问题。
二、合同解除异议权存在的法律疑惑
合同解除异议权存在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异议期间的合同效力;异议权的行使方式;异议权的主体及行使对象,异议权性质的界定等。
(1)合同解除异议权的性质关于合同解除异议权的性质认定主要有形成权和请求权的分歧,这种争议焦点的存在直接导致异议期间的适用差异,异议期间始终处在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夹缝与矛盾中无所适从。
有学者认为,合同解除异议权是与解除权相对的,是作为一种形成权而存在的,应适用除斥期间的相关法律规定,是一种不变期间,不适用于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这样,虽然有利于及时解决合同的不稳定状态,可是对合同解除异议权人的权益保护却是不利的。
与之相反,把合同解除异议权界定为一种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是一种可变期间,可以中断、中止、延长,这种观点侧重于保护合同解除异议权的合法权益,却不利于交易的高效稳定。
(2)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的针对对象合同解除异议权的异议期间的针对对象是否包含无解除权的当事人,是否包含违约方,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也得出不同的结论。无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对方在异议期满后提出起诉的,法院是否需要进行实体审理?无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对方在异议期满后提出起诉的,合同是否发生解除的效果?司法实践中有如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从广义的视角来分析,包括无解除权的当事人与违约方,这样容易导致异议权人的权益受损;
从狭义的视角来说,也根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合同解除异议期间的针对对象不包含无解除权的当事人与违约方,这样可以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进而实现当事人利益的平衡。
三、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相关路径探析
我国法律有关合同解除异议权规定的缺憾与争议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第一,增加违法解除合同的信用风险;一些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较重,而违约责任较轻的合同,意图不再履行合同一方,极有可能利用约定解除或是法定解除的条件,违法解除合同,意图摆脱合同束缚。第二,可能导致司法资源浪费;法院类似诉讼案件明显增多,而异议人准备时问仓促,导致司法处理的社会效果不佳。该司法解释确定的三个月内提起诉讼的时问,显然过于仓促,不利于异议人准备充分提起诉讼,不仅使得该司法解释原本消除合同不确定状态的初衷无法实现,而且,造成诉讼程序的拖沓、繁琐,加重当事人的讼累及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第三,法律规范的指引不足;由于合同当事人不甚理解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稳定合同状态的立法原意与规制,加之法律经验与意识的缺乏,很难起到实际的规制作用。
而这一系列不利影响迫切需要对合同解除异议权加以规制,以发挥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应从立法,司法,法制宣传教育等角度进行探析。
(1)立法方面:进一步细化与规范合同解除异议权的相关疑惑所在,尽可能准确合理地对异议权的主体、行使对象、行使方式、异议期间的合同效力作出相应的解释,从而对司法的适用提供合理的指引作用。这样做到了有法可依,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健康发展。
(2)司法方面: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审查合同是否应当解除时,不应只是停留在表面进行形式审查,而更应从制定合同的目的出发,衡量当事人的权益,进行相关的实质性的审查,从而维护交易的稳定,尽可能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发挥指引作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当事人深入了解合同解除与异议权的立法原意,知晓双方的权利保障,通过自身的途径解救纠纷,而不过多依赖于公权机关与机构。